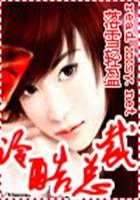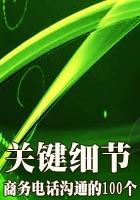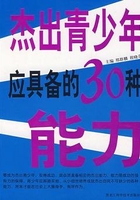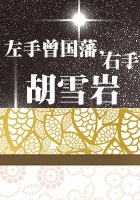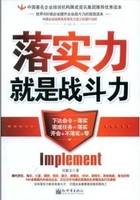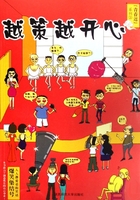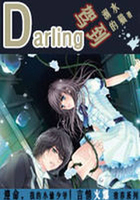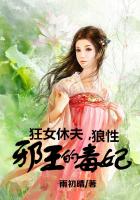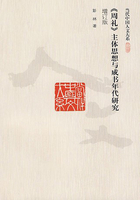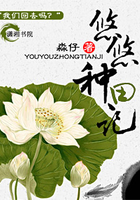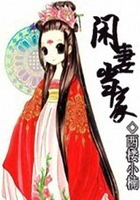金岳霖不是没有机会成为林徽因的伴侣,只是为了梁林这段美好姻缘,他选择做她一生的蓝颜知己,至死不渝。
老金对林徽因情深意切、一往情深,不多言不多语,始终以最高理智驾驭着感情,着实令人动容。对感情,不问前尘过往,不问今生以后,只为现在他所能够献给她的幸福。
迟暮之年的金岳霖,对她的评价,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词。"
这是怎样的一片痴心啊!是她的坦诚相待,诉诸真心,保住了这段友情。不论对错,可以做到毫无保留,是一种境界。
每个人都有拥有秘密的权利,有些想法和心情,不愿透露给他人,宁愿烂在肚子里,独自消化。这很正常,秘密之所以为秘密,就在于它的私密性。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埋在心里,躲藏在见不得光的阴暗处。
人们对内心的真实想法闭口不谈,甚至口是心非,遮遮掩掩。说的次数多了,当我们自己也快信以为真了的时候,掩盖不住的愧疚往往就会不请自来,夜夜侵扰着心灵,提醒着不坦诚的人们。
不要昧着真心,将事实隐瞒。坦诚,是对他人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直率之人学不来对自己虚伪,对他人虚伪,就像是揣着微笑,暗地里却握着匕首。
敞开胸怀,吐纳真心。只有以真心,才能换来真心。拥有坦诚之心,是林徽因的福分,是梁思成的福分,也是金岳霖的福分。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东西在起变化,比如天气,比如饭量,比如人心。
可是,林徽因与梁思成清楚,不管怎么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他们依旧是彼此的臂膀,岁月带给他们不可避免的阵痛,也带给他们笃信的爱情和婚姻。
时间揭穿了谎言与虚伪,也见证了真情可贵。
做人就要坦坦荡荡,若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吐为快吧,试着对他人坦诚吧,去收获我们的福分。
真爱是无我
两情相悦又可以白头偕老的爱情,是女人心中绮丽的梦。甜蜜又安稳,是女人对爱情的憧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也许女人就是为爱而生的吧,爱情和婚姻占据着人生的主导地位。寻得一份真爱,觅得一段良缘,携手走过彼此的朝朝暮暮,是女人从小到大的心愿。
不能将心比心的爱情是无法长久的,想要永恒就需要坦诚,谁不渴望被疼爱,谁不愿被捧在手掌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爱情除了享受,还有付出。
女人皆艳羡林徽因,她无与伦比的才情和风华令多少世人倾倒,追随着她,仰望着她。浪漫诗人徐志摩对她的迷恋至死方休,哲学大家金岳霖终身不娶"只待徽因"。
也许这对于普通女人来说,太过于缥缈,她与梁思成实实在在的婚姻,才是女人梦寐以求的人生,那是从平淡生活里渗透出来的浓情蜜意。
林徽因与梁思成尚在宾大求学时,学校要求每位学生自己设计作品,梁思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给林徽因设计了一面仿古铜镜。
那是用一个现代的圆玻璃镜面,镶嵌在仿古铜镜里合成的。铜镜正中刻着两个飞天浮雕,飞天的外围是一圈卷草花纹,花纹与飞天组合成完美的圆形图案,图案中间刻着: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纯手工精心打造的物件带着他对她的一片情深。恋爱时的点滴,都是那么晶莹剔透,令人着迷。世间最能滋润女人的不是别的,正是爱情,受宠的女人有着格外柔软舒心的笑容。
爱情有甜就有苦,浓重的苦滋味也不全是坏事,愈是举步维艰的时候,愈是考验爱情。
积劳成疾的林徽因,早早惹上了肺病,加上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养调理,演变成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没有治愈的可能。看着瘦骨嶙峋的妻子,梁思成也满脸憔悴。
如果世间的苦痛可以转移,那么他宁愿代替她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煎熬。
凡人为七情六欲所喜,也为其所扰。林徽因也是凡人,大病在身,疼痛难忍,脾气愈发暴躁,似乎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个时候,最亲近的丈夫便成了出气筒。
她不是有意去刁难梁思成,也不是没事找事,只是脾气说来就来,根本不受控制。面对妻子毫无征兆的脾气,梁思成只有默默低头的份儿。
她在吵、在闹,他在忍、在让,曾经的温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顺心、不如意。可即便是这样,没有人说要放弃彼此,没人打算用逃离的方式挣脱总是阴郁的心情。
在艰苦的条件下,肺病反复发作的林徽因,经常连续几周高烧不退,梁思成远途奔波去将医生请来为她诊治,久而久之,他竟也学会了打针。
日子拮据到无钱无粮的时候,梁思成只得硬着头皮去典卖衣物,他自是看不惯账房先生嘲弄的目光,却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
为了凑足妻子昂贵的医药费,他忍痛割爱,将日夜伴随他20年的金笔和手表拿去典当,这些都是他心爱的东西,可与妻子比起来,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他爱她,毋庸置疑。因为爱,他永远是她的支持和守护者。他甘愿将锋芒收敛,让她的光芒绽放,还会在一旁为她鼓掌,为她骄傲。
"太太的客厅"里每每都是林徽因高谈阔论,梁思成和金岳霖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沈从文托着下巴,不住地点头赞赏。
说到兴致高昂的林徽因,忽然停下来,看向默不作声的来客,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笑了,满脸宠爱地看着她,打趣道:"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得上嘴?"
在座的各位都笑起来,林徽因笑得最爽朗:"我们家是妇唱夫随嘛,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
笑声满堂的时光总是过于短暂,当林徽因的肺病进入晚期时,梁思成仍在国外。接到妻子病重的消息后,他匆匆结束了讲学,提前回国,回到妻子身边。
结核已经转移到肾脏,她一直发着低烧,她在病中煎熬着,挣扎着。刚刚回国的梁思成,顾不上旅途劳顿,又担起了护士的角色,除了必要的讲演外,他尽可能地陪伴在林徽因身边。
中国人讲究以小见大,这些细碎的小事足以证明梁思成对林徽因最真挚的爱。讲到这里,女人们对林徽因的羡慕、嫉妒恐怕又要开始泛滥了:
苦苦追问苍天,为什么自己遇不到这样的如意郎君,为什么桃花朵朵却都是烂桃花?难道是生不逢时,还是因为生得不如林徽因美丽动人?
如果这样去想,令人生羡的爱情永远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理想的爱情没有如期到来,何不先好好自我反省一下。
爱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梁思成爱林徽因,林徽因又何尝不是全身心地爱着梁思成呢。
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在昆明恢复工作以后,林徽因放下手头的工作,抽出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来操持家务。她是专注于事业的人,并不喜欢被家务活所打扰,在她看来,这是在浪费大好的时光。
可爱情就是这样,走进婚姻之后,女人理应承担起部分家务,为爱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林徽因曾经给沈从文写信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
不喜欢归不喜欢,林徽因做起家事来却有模有样,正如她对事业专注,无可挑剔。既然因为相爱走入婚姻的殿堂,生活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就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适当的让步,也是有必要的。
林徽因是梁家的长嫂,是林家的长姐,与两家的亲戚时常会有来往,想要把来客的衣食住行安排好,自然是要费一番工夫的。据说她画过一张床铺图,共计安排了17张床铺,每张床铺都标了姓名。
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棘手的家庭琐事圆满地解决掉了,免去了梁思成的后顾之忧,这样知书达理又贤惠温柔的妻子,叫他如何不爱。
她对家庭的付出,丝毫也不会逊色于丈夫。她是被宠爱的那个,同时,她也勇敢地肩负起了生活的担子,爱着他,为他操劳。
在生活上,她是他的贤内助,精心打理着两个人的生活;在工作上,她则是他的左膀右臂,燃烧着自己,为他助力。
当林徽因的病情稍有好转时,她便躺在小小的帆布床上,为丈夫写作《中国建筑史》做准备。她提起精神,支撑起病弱的身体,将资料分门别类,详细认真地做好读书笔记,以便他日后查阅。
当医生宣布她患有绝症后,本该悉心静养的她却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收拾行囊陪伴丈夫在穷乡僻壤间奔波劳累,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
她不怕自己病情的恶化,不惧死亡,她唯一担心的是没有她的陪伴,丈夫的考察工作会有所耽搁。
这样的女子,叫人如何不爱她。
林徽因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梁思成也因肺结核住进了医院,病房就在她的隔壁。昔日曾一起翻山越岭的两个人,如今静静地躺在各自的病房里,不免叫人看着心酸。
大山大水都未曾将他二人阻绝,现在的一道墙壁,却隔开了千山万水。
梁思成还没有住院的时候,还可以常常来医院探望妻子,现在也住进了医院,即使是隔壁,不到数米的距离,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他们每天只能靠着送药的护士传一张薄薄的纸条,将对彼此的关心落在纸上,传递给彼此。
梁思成在建筑史上的成就,也有林徽因的一半功劳。他坦然地承认:"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
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痛哭了24个小时的林徽因,对沈从文说:"在夫妇之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她认为夫妻争吵,是因为彼此在乎,"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消灭怒气的最好武器,是爱。
她与他都深谙这个道理,几十年风风雨雨,都在彼此的眼眸里。
爱情是两个人心甘情愿地守护,上天赐了姻缘,能否相伴到老,能否幸福愉快,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多少人艳羡她的好福气,能有这样体贴的丈夫相伴左右、不离不弃。殊不知,福气是靠个人修来的,不是从天而降的。女人幻想幸福没有错,错就错在只懂得坐享其成,却忘了爱情同样需要付出,才会有回报。
想要被人爱,首先要让自己值得被人爱。一味只顾自己,自私又任性的女人,一定得不到他人的贴心守护,也一定不会懂得真爱是无我的乐趣。
婚姻需要经营
两情相悦的男女,拜过天地、父母,并在父母的见证下,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从此,两个人凑成一个我们,荣辱与共,甘苦与共。
婚姻,是爱到情深时,心甘情愿地将彼此捆绑在一起,缔结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不论疾病还是健康,不论年轻还是衰老,都愿意永远爱护彼此,安慰彼此,陪伴彼此。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它的稳固,仅凭一腔热血和三分热度是无法维持的。朝夕相处中,岁月会将恋爱时如胶似漆的激情褪去,当激情不再,只剩琐碎单调的生活时,爱情开始变了模样。
当刻骨铭心的爱情转变成血浓于水的亲情,聪明的女人懂得去经营婚姻,打理生活,让爱情在平淡中永放光彩,让婚姻经得住流年。
林徽因是聪明的女人,她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她懂得作为女人,何时该温柔,何时该凌厉。她用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
外人常谈起的是她与徐志摩、金岳霖剪不断的情缘,却忽略她与梁思成相濡以沫、坚如磐石的婚姻。不管时间怎么变,她的丈夫不是徐志摩,不是金岳霖,而始终是她的恋人梁思成。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可谓是新旧相兼,门第相当。由于两位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政见相投,关系十分密切,友情笃深,对于两个孩子的终身大事,作为长辈都有结为儿女亲家的愿望,便私下为梁思成和林徽因订下了婚约。
作为近代的开明人士,梁启超和林长民虽然订下了婚约,却并没有按照旧式的惯例,将婚约强加给两个孩子,而是将选择权交还给儿子和女儿,让他们自由相处。
他们的首次相识是在林长民的书房中。
当时,林徽因年仅14岁,正在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梁思成17岁,是清华学堂的学生。梁再冰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说起过这段往事:"爹爹后来说,特别令他动心的是,这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
这种飘洒一直扎根在梁思成的心中,成了他朝思暮想的靓影。待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后,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并于1924年共同到美国留学,1928年毕业后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
他们的爱情始于父母的撮合,比一般情侣有着更亲厚的感情基础。他们崇尚西方式的恋爱自由,相信爱情是两个人心心相知后形成的特殊感情。同时,他们也愿意遵从父辈所结下的秦晋之好,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林徽因喜欢和梁思成在一起,他们有着相似的出身教养和文化构成,他们交流默契,相处愉快。很多年后,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学界的权威专家,当他谈起最初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建筑事业的时候,他的答案很简单,是为了林徽因。
《林徽因传》里则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