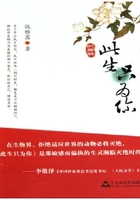那么,达尔杜弗用什么手段蒙住了奥尔贡的眼睛呢?那就是他的假虔诚。他看准了奥尔贡的弱点,抓住不放,大肆进攻。他的假虔诚是三分做作,七分奉承,而这一些正是奥尔贡最欣赏的东西。奥尔贡并不是一个糊涂人,道丽娜说过,他象当时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那样,在内乱时期,辅佐国王,英勇有为。一旦得势,当了新贵,他就仿效上流社会的习尚,以宗教虔诚为时髦,而且喜欢别人的谄媚。
这正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贵人迷》等剧中都揭露过资产阶级的这种虚荣心,达尔杜弗在教堂里的种种表演,全是投其所好,做给他看的。达尔杜弗并不急于求成,做得颇有心计,而且以谦卑为主要特色。奥尔贡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更由于虚荣心得到满足,便陶醉在对方的阿谀声中,把一个骗子接进家来还自鸣得意。所以奥尔贡的轻信和形式主义宗教热都与上层资产阶级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于达尔杜弗,莫里哀并不限于从道德上揭露他表里不一的卑劣品质,而是在撕破他伪善画皮的时候,着重暴露他恶棍的本相,揭发他的罪恶用心以及这种伪善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样就使剧本对于伪善的揭露更深入了一步。
达尔杜弗不仅是个酒肉之徒,而且是个淫棍。他一上场就暴露了好色的劣根性:一见道丽娜穿着裸胸的裙子,心里就热烘烘地冒上一股淫乱的念头。为了掩饰这种感情,装出绅士的假象,他故意耍弄一块手帕,要人家把胸脯盖上,不料被道丽娜用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心理。好色是他的致命伤,莫里哀就从这里开刀,让他显出了原形。不过达尔杜弗并非无能之辈。当他色相毕露,向奥尔贡的续弦夫人艾耳密尔求欢,做出这种与绅士身份绝不相容的罪恶勾当的时候,他竟能把自己卑鄙无耻的情欲说成是敬爱上帝的一种表现:“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的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哦!秀色可餐的奇迹,我将永远供奉您,虔心礼拜,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这简直是一首宗教赞美诗,可是,它表达的却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兽欲。一当恶行败露,面临险境的时候,达尔杜弗仍能毫不慌乱,冷静而熟练地装出一副无辜受诬、忍辱含冤的样子,说什么:“上天有意惩罚我,才借这个机会,考验我一番。别人加我以罪,罪名即使再大,我也不敢高傲自大,有所声辩”。甚至还跪下来请求饶恕揭发者。
这样一来,他把圣人的模样就装得更象了,奥尔贡对他更是无限地信任了。他也就自然地达到了化险为夷、嫁祸于人的目的。奥尔贡赶走了揭发奸情的儿子,把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都赠送给他。这个家伙居然有脸在“愿上天的旨意行于一切”的名义下,把这一切统统都承受了下来。克莱昂特指出:他的这些举动,未免不合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达尔杜弗仍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巧言作为答对:“因为我怕这份财产落在歹人手中,他们分到这笔家私,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不象我存心善良,用在上天的荣誉和世人的福利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既好色又贪财,掠夺别人财产、勾引别人的妻子,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人毫无道德信念,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宗教在他手里就象一块胶泥,他可以随机应变,熟练地玩弄教义来对付各种情况。
到了第4幕,他再次向艾耳密尔求欢。这一次却是别人设下的巧计,达尔杜弗尽管老练,然而他欲火中烧,色迷心窍,急于求得实惠,以至抛弃了上天的名义,剥下了绅士的伪装,奥尔贡终于认清了这是个大坏蛋,狂怒地叫道:“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没有比他再坏的了。”当即要把他赶走。达尔杜弗再次陷入险境。
但是达尔杜弗并不示弱。当伪善再也骗不了人的时候,他索性抛弃假面具,露出了凶恶的真相。
因为这时他早已掌握了奥尔贡的财产和命运,假面具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他干脆就撕破脸皮恩将仇报,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利用法律,串通法院,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他到宫廷告发奥尔贡违犯国法,亲自带领侍卫官前来拘人。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他同样能找到借口,说什么“我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圣上的利益,在这种神圣责任心的正当威力下,任何感恩的心思也不存在”,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道丽娜说得好:“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有鬼招儿给自己改成一件漂亮斗篷披在身上。”对于这样的恶棍来讲,不论在什么样不利的情况下,他都能厚颜无耻、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神圣的名义。
莫里哀通过达尔杜弗的行动告诉我们,这种伪善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与官府衙门,甚至和宫廷势力都有联系,法律和制度也对他有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奥尔贡一家不可避免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伪善的恶习包藏着祸心,它必将造成严重的危害。莫里哀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达尔杜弗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教会以伪善为其特征,推而广之,伪善也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恶习。
在专制君主的朝廷里,虚伪是一种求得宠爱和晋升的手段,在贵族阶级内部,虚伪又是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拿手好戏。达尔杜弗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作为教会的代表,作为以法院、宫廷为背景的流氓恶棍的代表,集伪善恶习于一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因此,在当时就不断有人指出它与某个真人相似,实际上,达尔杜弗绝不是个别人的写照,而是17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典型。在欧洲,达尔杜弗几乎成了伪善者的同义语。
喜剧的结尾出人意外,国王明察秋毫,认出了达尔杜弗是个大骗子,把他拘捕入狱。对于奥尔贡则记起他勤王有功,宽恕了他的罪行,一场灾难就这样烟消云散。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结局圆满,莫里哀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使奥尔贡一家得到喜剧结局的根据,他只能借助国王的权力来主持正义,这当然反映了莫里哀的政治态度——他是拥护国王的,同时,它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并不具备惩罚达尔杜弗的客观条件,莫里哀的设计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而已。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的喜剧大师,这出喜剧也是按照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
古典主义是适应17世纪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在当时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并且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古典主义要求创作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古典主义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把它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法则,要求当代的作家严格遵守,以便把文艺统一在专制政体的控制之下。
莫里哀是从学习民间戏剧开始自己的戏剧活动的,后来进入宫廷,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有时还有所突破。古典主义要求戏剧遵守“三一律”,《达尔杜弗》也符合这个要求,不过莫里哀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法则,使它们有利于推动剧情、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例如,按照“三一律”的要求,剧中地点不变,始终安排在奥尔贡家。莫里哀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来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如第3幕达米斯藏在套间,第4幕奥尔贡躲在桌下,都造成了关键性的情节,另外一些戏剧动作,如达尔杜弗求爱、艾耳密尔的巧计也只有在室内才能发生,离开了这个环境,那些都成了不可信的了。
莫里哀的喜剧很注意塑造人物典型,因而被称为性格喜剧。《伪君子》一剧的全部艺术构思都为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在塑造这个形象时,莫里哀一方面从剧本的主题思想出发,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揭露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这一点上。
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如何掌握好分寸,把伪君子与真正有德之士区别开来,让观众自始至终看清这个恶棍的真面目,还可以减少演出的阻力。他在剧本的序言里明确地交代了这一点:“材料需要慎重行事,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绅士这种人物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立面,也衬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
全剧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1、第2幕是侧面交代达尔杜弗的虚伪性,为他的上场作准备;第3、第4幕,正面揭发达尔杜弗的伪善;第5幕进一步揭露他的凶恶面目和危害性。
莫里哀把达尔杜弗以外的剧中人,分成两派,奥尔贡和他的母亲是达尔杜弗的崇拜者,其余的人物都是达尔杜弗的反对者,在前两幕,达尔杜弗没有登场,但是这两派之间围绕着对于达尔杜弗的不同看法,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达尔杜弗的出身,达尔杜弗如何混进了奥尔贡家,以及他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这些都是刻画人物所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
莫里哀在人物出场之前就把它们一一作了介绍,等到人物上场,他就可以集中笔墨来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实质,而不至于为了交代往事而分散笔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