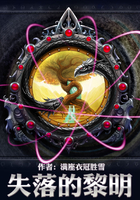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
两本“半部书”
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此时,胡适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鼓吹白话文学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挟此气势,他又抛出这部观念、写法与先前研究全然迥异的著作,引起震动自然不言而喻。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序文中对这部著作大加赞誉,认为该书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对于此书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元培说作者“有截断众流的手段”;认为此书讲时代、辨真伪、考方法的研究,足以“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
顾颉刚后来回忆起,当他们在课堂上,听到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的震动情形:“这一段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冯友兰当时也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回忆说:“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胡适后来总结此书,认为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子)、孔(子)讲起;二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都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可惜,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只有上卷,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大憾事。
1921年,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请胡适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2个月,编成了15篇讲义。讲义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开始于“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大约与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
1922年,胡适到南开大学讲这门课,该讲义印成油印本。1927年,北京一家文化学社以油印本为底本,印成一本《国语文学史》。印本虽然是胡适的朋友钱玄同题签,又有黎锦熙的长序,可胡适并不知情,是黎锦熙学生以此名义印了1000本,为同学作查考用的,不牟利。
当时,梁实秋、徐志摩等一干胡适的朋友办起了“新月书店”。胡适入了100元,成了股东。见有人翻印胡适著作,同仁们不满意了,便大力催促,让胡适将著作修改出来出版,甚至早早就在报刊上打出广告。广告中说到“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了一千部”,并无其事。钱玄同不过题一签而已。胡适于是便托朋友借书,又据自己游历巴黎、伦敦时搜集的资料,更借重当时的研究成果,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胡适在该书自序中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对这部旧讲义进行大规模修订。
这次修订,原稿几乎全推翻了。原讲义15讲,除第一讲、第二讲稍有删改,三、四讲得以留一部分外,后面几讲完全重写。胡适本打算将书写到唐末五代,作为上卷;不料愈写愈长,收不了尾,只得在白居易处打住。胡适后来说:“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70万字至100万字。”何时完工,自然难料。
这部以《白话文学史》为名的著作,就这样以上册面貌问世。之所以称“白话”,胡适说了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1928年6月19日,胡适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又出了半部著作。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月书店的第一本书,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
丘吉尔式的演讲作风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有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和钱穆都是北大教授,而且都研究《老子》。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两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胡适的研究论著先出,钱穆著书批评他,他却按兵不动。钱穆很气愤。有一次,两人在一个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张中行回忆胡适先生时说:“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
胡适信奉的格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他既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又潇洒儒雅,从容优游。1949年7月10日,他在美国西雅图进行“中美文化使用会议”演讲,一位美国学者称赞他具有“丘吉尔作风”。他语言浅显易懂,振聋发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一句“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出了醒狮般的怒吼。
1960年6月18日,胡适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防身的三味药》。他以一位长辈的殷殷之心,在同学们即将毕业之际,热诚真挚、推心置腹地勉励大家怎样走向社会,提出以“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当作“防身药方”;将读书、做学问、树立起追求理想的信心和勇气,出神入化、行云流水似的宣示出来,且跌宕得方、起伏有致、张弛有度、文白相间、警语迭出,如“努力不会白费”,“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胡适主张,“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什么是文学———钱玄同》),要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胡先生无论写作,无论演讲,通过严肃而认真的实践,算是比较完美地做到了。
【大师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1929年6月,被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赵元任留学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讲授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是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把语言当成自己一生的最爱,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38年,赵元任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
他早年致力于国语运动,在音位学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他创立的音位标音法,在国际语言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人曾问赵元任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他只说了两个字——“好玩”。
美国语言学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语言上,赵元任没有错过”。赵元任有“录音机”一样的耳朵,他一生会讲33种汉语方言,会说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等多种语言,是方言调查工作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为汉语拉丁化字母的制定做了很大贡献。
在清华任教期间,赵元任由于受过万国音标(IPA)听音、记音、发音的训练,入选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致力于研究国语罗马字注音。他与刘半农、黎锦熙、林语堂等人组成“数人会”,提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本,开展了3个月密集的吴语方言田野调查工作,深入实际,对汉语方言进行了分区研究,创制了调查表格。
赵元任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以便能够记录生动的口语材料。在研究汉语语法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借鉴了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另一方面,他善于结合语义进行分析,弥补了结构主义重形式、轻内容的缺陷。
赵元任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他曾用“中华好大国,偷尝两块肉”这两句话,来向同学们讲授“阴阳上去入”五声,使同学们在寓教于乐的气氛中学习了语言知识。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1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的大体意思是:从前,有一个爱作诗的施姓文人,住在石头造的屋子里。他喜欢吃狮子肉,发誓要吃十头狮子,所以他经常到市场上去找狮子。那天早晨十点,恰好有十头狮子上市。这时,碰巧姓施的也来到了市场。他确实看到十头狮子,于是拉弓射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然后拖着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回到了他的石屋。但石屋很潮湿,他叫仆人把石屋揩干,然后再饱尝这十头狮子的肉。吃时,才发现这十头狮子其实是石头的,不能吃。
这篇短文,原作不过百字,却能用一个同音字将姓施的这个书呆子吃“石狮”的故事描绘得淋漓尽致。非语言天才何能有此奇想、出此妙笔?虽属“文字游戏”,但充分表现出了单音节汉字视听分离的特色。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有记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后继队伍。
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