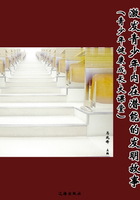当然,胞儿子也可以在成家后若干年,再找理由动员妻子带着子女回到原来的宗族去,从而解除与妻家的宗族关系,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女家父母已经过世,作为儿子已经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还有,就是妻子作为老大,其他兄弟、姊妹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或兄弟、姊妹多,分家矛盾大,胞儿子愿意放弃财产继承,也可以选择离开。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当初避难至此的几十号人,和本地土著人,以及后来的移民,世代交往,几经融合,便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族系。一般山贼,小股土匪,多不敢睨视洪氏一族任何一家的财物,即使有点势力的恶人也不敢轻易冒犯。
但是人多了,大天井里自然容不下了,就陆陆续续有人搬出了大天井。先或是一家两户,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搬出去的人多了,新建的房屋,新生的院子也就多了起来,先是称新房子,小院子,与大天井相对应,后来新修的院落就随地形、景物取名,不外乎井边上、河坝里、向阳坡、梁梁上、柿树坪、大松树、斑竹林一路取下去,不一而足。单门独户的人家,大大小小的院落绵延七沟八梁,四坝五坡。
人口多了人才辈出。从文的,练武的,耕田的,种地的,打铁的,倒铧的,做小手意的,贩山货的,跑马帮的,什么都有。不过,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送子女读书才是正道。
11
天祥家道并不富裕,但母亲幼兰还是愿意送他到私塾里去读书识字,希望他将来会有出息。在他六岁的一天下午,私塾的王先生登门来访。
王先生身材瘦长,一双小眼睛眯眯着,留一绺山羊胡子,一袭长衫经常显得又脏又破。他是常客,进了楼门,就大声问,大嫂,幼兰,在家吗。
四新爹,看秀秀啦,坐噢。幼兰和她妈妈同时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邀请王先生进屋里去说话。
有洪氏一族以来,族人起根发苗,支支繁盛,唯独幼兰这一脉一直人丁不旺,几乎代代单传,若干代人都住在老房子里,尽管她爹为了延续香火,娶了四房妻子,唯独她妈妈年近四十才开怀,只生养了她一个。幼兰爹死以后,四姨太才三十多岁,年纪尚轻,就招了多年一直在井田坝教私塾的王先生做了上门汉。幼兰的母亲是大房,所以她称王先生叫四新爹。
在清水河,称谓前加新,不是与旧相区别,而是专指新来的。一位男子娶了几房太太,平辈儿的称大房就叫姐,或大姐,晚辈儿的就叫她大妈,或婶婶。二房就不一样了,前面就得加新,叫新姐,或新妈。三房又不一样,还要加上序数,叫三新姐,或三新妈。以后的都是这样,序数加新一路叫下去。如果一家养了几个儿子,大儿子娶了媳妇,就叫大儿媳妇,二儿子的就叫新儿媳妇,三儿子的又要加序数加新了。
王先生婚后,他们的女儿与天祥几乎是同时出生的。按辈分四房的女儿,应该与幼兰同辈,是天祥的高辈儿,天祥应该管她叫姑。四房为高龄生产,风险大,产后得了月间病,缺奶。秀秀饿得嗷嗷叫,没办法,王先生就送她到幼兰处,同天祥一起哺育。幼兰拿她这个小妹子当女儿看,啥事都依着让着。秀秀对幼兰嘴上喊姐,但自幼没了母亲,与天祥同吃一对奶长大,骨子里早把她当母亲,把这个家当自己的家了,进进出出,随便得很。再加上自幼同天祥同吃一对奶,同睡一个被窝,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天祥的一举一动,她都特别在意,天祥的一言一行,她都特别关心,天祥高兴,她高兴,天祥委屈,她憋气,天祥挨了打,她就暗自掉泪,浑身都难受。
王先生虽然没了妻子,但女儿有幼兰和她妈妈照管,他就放心教他的私塾。他对幼兰一家心存感激,就实话实说,秀秀在你们这儿好好的,看她做啥子,我放心得很哩。
幼兰晓得他说的是心里话,就当面夸秀秀听话,乖得很,你坐哈,四新爹。她一面夸秀秀,一面张罗着去打了一小罐酒,顺手煨在火塘里。
不说秀秀啦。王先生在火塘边坐下来,直接说出了他的来意,我今天来就是要和大嫂幼兰你们商量商量,是不是该让天祥去学堂里念书了。
幼兰担心天祥才六岁,年龄小,不好教,问他能行吗。她把一只黑陶杯子递给王先生,为他满上了酒。
王先生咂了口酒,语气很肯定,行啊,咋不行哩,天祥那家伙脑瓜子精灵得很,保证念得走的。
幼兰见王先生那么肯定,也就应许了,四新爹,你老说行就行吧,只是要叫你费心了。
哪儿话哩,秀秀给你们那么多的麻烦了,我都没客气过。王先生告诉幼兰,天祥只管来念书,份子就不那个了。
四新爹,我得把话说到前头,天祥来念书,份子我们还是要照给哈。私塾先生的薪金来源于学生的份子钱,一个月给一次,半年给一次也可以,学生多了,关系又到了位的,一年结算一回也是允许的。天祥去念书,理该出份子钱,至于多长时间结算一次都不很重要,幼兰坚持的有道理。
王先生要天祥去他那儿念书,本来就是为了回报幼兰这么多年对秀秀的悉心照顾,听她这么一说,他自然有理由拒绝。天祥妈,那就太见外啦,秀秀在你们这儿吃的用的不算少了,多少年我都没给你们客气过,天祥这会儿念书若要你们出份子,我这褡老脸倒真没处搁啦。
幼兰妈妈也劝王先生不要客气,他新爹呀,你也是靠这吃饭喃,该出的,该出的,你就不要客气啦。
王先生态度很坚决,不容商量地对她们母女说,大嫂哩,你们啦,对我和秀秀的大恩大德,我就不晓得咋个来报答了。现在一个学生是教,两个也是教,说啥也不能要你们再给天祥出啥份子了,再说我可真气啦。
幼兰觉得这样就要欠王先生一份人情了,要是该出的份子都不出,那咋好意思哟,四新爹。
王先生站起身来,摆了摆手,边说话边往外走,再莫说见外的话了,明天就来噢。
幼兰知道王先生是诚意的,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得行嘛,得行嘛,秀秀的事你老就放心哈。
王先生已经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他一时像骑在门坎上,无法回头和幼兰答话,放心,放心,在你们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走啦,明天一定来哈。
天祥念书了,秀秀少了一个玩伴,偷偷地哭了好几回,一时也跑到学堂里去做了旁听生。教书先生是她爹,来去都自由,里里莲花落,她也在学堂里混了好些年,认了不少的字。由于整个井田坝没一个女娃娃进学堂读过书,稍大了些,她就主动辍了学,回到幼兰那里,开始学做女红,先从扎鞋垫子做起,缝衣缝被,扎花绣朵,这些活计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慢慢地做得很精道了,稍大了些,好多同龄的女娃娃都赶不上她。
学堂设在大天井外一处小天井的大堂屋里,常年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学童。小娃娃都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增广贤文》等识字课本,大些的娃娃就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般上午背书,下午临摹毛笔字,或对对子,或学写一些半文半白的短文。
天祥好像还是块念书的料,小小年纪,记忆力却特别好,书本上一页的内容,王先生教他一两遍,他就能认,而且很快就能背下来。只是好动,实在坐不住。特别是下午习字,先生稍不留神,就不见了他的影子。
12
旧时教书,先生主要是教儿童背书。儿童每天到学堂的第一件事就是当着先生通背前一天教过的内容,有时还要抽背以前背过的内容,然后老师再教新课。这样,同一天进来的学生,由于记忆力注意力等个体差异和用功程度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教的课文就有可能不会一样,后进来的学生说不一定有一天还会超过先进来的,先生当然更偏爱那些记忆力好背书快的学生。对于那些注意力和自控能力差,老背不下来书的学生,先生就让他天天重背,几天都过不了背书的关,先生就可能要对他进行惩戒,这个学生就要准备挨竹板子了。
竹板子都是用斑竹块做成的,一般有一尺多长,一寸来宽,有厚有薄。先生打学生,有抽手心的,也有打屁股的。抽手心算是一般性的惩罚,打屁股就是很重的责罚了。
抽手心时,先生让学生到讲桌前站直了身子,将一只手反背在背后,另一只手则要伸直手掌伸到先生面前,让先生抽,一下,两下,三下,抽多少,抽得重不重,就要看先生当时的心情了。心情好时,先生就只会象征性地抽几下,吓唬吓唬就达到了目的,心情不好时,就会抽得多一些,抽得重一些。
有意思的是打屁股。学生老背不下来书,该让长长记性了,或者犯了错,理应得到惩罚了,再加上先生心情不太好,屁股就得小心要挨板子了。
打屁股时,先生拉长了脸,命学生把长板凳抬到讲桌前,自己脱了裤子,骑在板凳上,将两个肥墩墩圆滚滚的屁股蛋完全暴露在先生面前。
先生本来显长的脸拉得更长,眯缝着双眼,似乎很不情愿正视那对略带粉红的肉蛋蛋,握着的竹板子先在自己的手心上啪啪地试了试,从心理上给受罚的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举起的竹板子还没有落下,那两团粉红的肉蛋蛋就抖开了。
先生之所以乜斜着那两团粉红的肉蛋蛋,实际上是在确定竹板子的落点。竹板子既不能直着去,也不便横着去,最好选择斜着去。直着去要不得,伸长了会伤着大腿,如果失手,误伤了两个藏在那两团粉红的肉蛋蛋下面的两个小蛋蛋,就不得了了,那可是受罚者长大成人后的快乐之本,打坏了不但家长不答应,先生也会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横着去当然保险,绝对不会误伤无辜,但很费劲,先生不得不略微弯一弯腰,拉开架势才施展得开来。斜着去成了先生的最佳选择,做起来更是得心应手。
先生一旦找准了落点,手起手落,一下一道血印子,道道刻在两团粉红的肉蛋蛋上,分分明明。一般情况下,三五下惩戒就到位了,先生实在生了气,就难说了。
竹板子与两团粉红的肉蛋蛋相亲,可想而知该是怎样的一种疼痛,那是真正钻心的痛啊。而学生挨板子只能咬紧牙关,任凭泪水长流,也不能哭出声来。不过,虽然先生经常拉长了脸,扬起竹板子在自己手掌上拍得啪啪直响,真正用它来惩戒学生的时候却是少之又少。
背书时,学生背向先生,面朝其它学生。学生叽里呱啦地背,先生摇头晃脑地听。如果稍有错漏,先生会提醒一两次,错漏多了,先生就会责令停下来。如果背的是多次都没有背下来的篇目,就准备挨板子了。话又说回来,先生赏的板子不是人人都可得到,何时赏,赏给谁,他心中自有一杆秤把握着。
天祥背书快,记得牢,很会背书,也很愿意背书,似乎背书有瘾,屁股蛋蛋自然讨不到与竹板子相亲的犒赏。只是经常会得了意,就忘了形,他一边叽里呱啦地背着前一天先生教过的内容,一边摇头晃脑挤眉弄眼做怪相,逗引其他学生发笑。先生不便过多地迁就他了,就会遭到训斥,甚至也会赏给他一两下板子,做给其他学生看看,免得说他偏心眼儿,总是护着他。
天祥书背完了,先生又不想再教他新课了,他觉得无事可做,就更难控制了。要么猫到桌子下面去摸前排同学的屁股,要么就搞恶作剧,把已经一张够脏的脸再涂些墨,画成小花猫,把一双已经够脏的手再弄些墨,染成黑打手,把自己装扮成黑猫警长吓唬同学,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先生拿他没得办法了,找理由说他书背得好,就奖励他到学堂外去放风,目的是避免他妨碍其它学生背书。可这一放出去,往往就成了他的天下,再难收得回来。任他去掏鸟窝,钻狗洞,追野猫,撵兔子,什么都干,全然不像个正读圣贤书的学生,个性张扬无余,十足一个野孩子。而且越大越难管,有时先生真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一个春日的下午,太阳暖暖的,林中的鸟儿都懒得开口鸣叫了。先生吃过午饭就多睡了一会儿,学堂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娃娃没一个闲着,你追我逐大闹学堂。天祥这家伙不晓得哪根筋出了毛病,他竟然喊拢几个平常耍得好的同学商量着,成心要出一回先生的洋相。那些读起书来呆头呆脑的家伙们,搞起恶作剧来,一点儿都不笨拙。他们估摸着先生快要进学堂了,就七手八脚地把半撮箕垃圾放在半掩的门扇上方,等着先生来着套。
先生像平常一样款款而来,推门进来时并不曾注意半空中,半撮箕垃圾哗啦啦下来,全都扣在了他的身上,头发上,脖子里,长衫上,甚至那绺山羊胡子上都是垃圾和尘土,弄得他一时斯文扫地,灰头土脸,样子十分狼狈。
本来大家看先生出了洋相,是要好好笑一回的,一见先生满头是圾垃,并不干净的长衫上又沾满了脏东西,都惊得目瞪口呆,再没一个笑得出声来了。
先生这回可是真正地气急了。他顾不得整理整理尊容,拉长的脸似乎变得非常的威严,学堂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感觉到了他那张威严的面孔给人的震慑力量,大家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显然,这是一出集体共同上演的恶作剧。尽管法不治众,但首恶分子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天祥已经认识到这次的祸真正闯大了,一定难逃责罚,不待先生点名,就抬着板凳走到了讲桌前,撩开长衫,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脱掉裤子,趴在了板凳上,其他参与者也学着天祥的样子,先先后后撅着屁股蛋等待竹板子来亲吻。
先生这次再没手软,噼里啪啦,好一顿痛快发泄。竹板子在那些粉红的屁股蛋蛋上欢快地跳着舞步,旧的血印子很快被新的血印子覆盖了。他那块本来只是用来吓唬学生的竹板子第一次沾上了学生屁股蛋蛋上的血点子。没挨板子的其他学生,也感觉到肉皮子一阵阵地发紧。
天祥挨了打,王先生心疼,幼兰更可气,反应最强烈的要数秀秀。她不依不饶,和她爹大吵大闹大哭了一场,非要她爹赔天祥一个好好儿的屁股蛋子。感动得天祥摸着火辣辣的屁股蛋子,咧着嘴傻傻地笑,感觉多一个人疼,自己就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不禁在心里喊,小姑,你真真是好啊。
傍晚,王先生换了衣服洗了头,气也消了,回想当时的确是气急了,对那些粉红的屁股蛋蛋下手也确实太重了些,就心里歉疚疚地前去探访天祥的伤情。
天祥屁股蛋蛋好了又开始上学,天天背书,对对子,临帖习字。功课做完了,照样掏鸟窝,钻狗洞,追野猫,撵兔子,同学间的恶作剧照搞,花样儿层出不穷,但再没敢针对先生。他淘气归淘气,门门功课却始终做得都不错,自然挨不了先生的板子。随着岁月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阅读的能力也增强了,几年间,他把王先生准备的课本都相继念完了,实际上也都背完了。
王先生藏书不多,就给他找些古诗词或史书以及传奇之类的书看,还把一些医书药书和一些杂书也拿给天祥读,那部蜀中杂记更让他十分着迷。不强迫背书了,他则从亲朋好友那里搜罗了好些书来看,阅读范围扩大了,自然增长了许多的活知识。
天天和一群大小不一样的同学混在一起,天祥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面对自己说话的声音不再尖细,而且觉得声音是从喉管里发出的,又粗又沉这种变化,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搞不清楚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