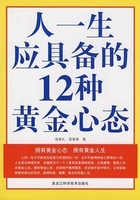爷爷自然晓得路径。他朗朗地笑着,这不太简单了吗。从井田坝,或者从两河口到古城,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水路只有一条,陆路就有若干条。清水河左岸的路不说,右岸他就走过三条不同的道。一条沿清水河河岸,上梁下沟弯路多,坡路多,陡路多,龙背山上的路几乎全是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还找不到路。这条路有三四天的路程,是距离古城最近的一条路。这条路从两河口出发,坡坡坎坎往前走,到了干龙洞和水龙洞,如不想再走山路了,就穿过干龙洞,到清水河岸去等下行的船。只是下去比较麻烦,要事前有所准备,十来丈高的一道陡坎,要下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水龙洞没人走过,传说里面水很深,还有大莽蛇,是真是假,不得而知。龙洞以下的路有易有难。难的是必须翻过龙背山,很陡,全是羊肠小道,路特别难走。翻过了山,下了河坝,沿河谷走,当然容易得多了。
第二条路,也就是中间一条,距离也近些,走的人很多,是条大路。从这里出发,翻过龙池坪那座山,就沿着一条几乎与清水河相平行的小河一直往下走。从两河口出发,方向也大体一致,就是现在走的这条路,也要翻龙池坪,只是从下垭口过去,再到那条小河。走出了河口,距离古城就不太远了。这条路上人家多,路边也有不少歇脚的幺店子。实在走不动了,找家幺店子住下来,第二天又走。实际上,这条路是古城到两河口的陆上大通道,常有骆马队来往。做货郎生意的应该知道这条路的。
第三条路是弓背,路稍远。从清水河上游翻过分水岭,顺小清河而下,直达嘉陵江岸,再沿江而上,也可到达古城。小清河河谷地势平坦,人口比较稠密。做货郎倒不在乎路远路近,只要卖得脱货,走远点也值。只是分水岭一带人家很少,比较荒凉,只有白天赶路过去。
除此而外,三条大路中间也有一些叉道,与大路时分时合,不如走大路便捷。
爷爷告诉天祥,这几条路都是自己年轻时收山货,做铲铲生意时用脚板儿量过的,都走过若干次。沿江的路荒凉,路小,路陡,沿途难得遇到人家,渴了,找不到喝的,饿了,找不到吃的,天晚了,更找不到往的。不时还有野兽出没,很不安全。第二条路和第三条路都不存在这些间题。年轻的时候收山货,做铲铲生意。从这里出门,一路铲过去,到古城卖掉了,多从沿江的这条路返回,这条路近些。出去时则多是走那两条大路,一边赶路,一边还可以收些东西,赶路也在挣钱。沿途都是熟店子,哪家都可以住下来,歇歇脚。路上发生的风流事儿,当着孙女的面,自然说不出口。实际上,这才是老人家最精彩的生活经历。
爷爷对三条路确实太熟悉不过了。哪里有一道坎,哪里有一条弯,哪里路窄,哪里路宽,如数家珍。不时还用柴棍在地上画一画,指一指,生怕天祥听不明白。
天祥专注地听着,不时还要问一问,让爷爷重新讲一讲。
桃桃干陪着,也不插话,抱着黑蛮子的脑壳,轻轻拍着,抚摸着,不时拿眼睛瞟一瞟天祥,想她自己的心事。
柴火燃得很旺,火光把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每个人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都显得特别有精神。桃桃的脸形饱满,脸颊绯红,焕发出青春的美。
爷爷额头的沟渠明显,棱角分明,留一把大胡子,朗朗一笑,自然掩饰了自有的威严。一罐酒煨烫好了,爷爷把盏,先是同天祥对饮,喝到后来,天祥感到已经有了些醉意,不再接了,爷爷就自斟自饮。
天祥在酒精的作用下,满脸通红,耳朵都是红红的,他那别致的眉毛更引人注目。
桃桃不喝酒,先是看他们爷孙喝,又劝爷爷少喝点,最后怕爷爷喝醉,干脆就不让爷爷再喝了。
爷爷嘴里嗔怪着孙女,干脆让桃桃收拾了酒罐和杯子。
夜已经深了,大家都还没有睡意。天祥还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爷爷难得遇到一个愿意听他讲故事的人,谈兴正浓,桃桃只是陪他们干坐,不时瞟一眼天祥。
天祥对通往古城的道路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只待自己以后去实地踏探,掌握更多实际的东西。从爷爷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总想回避收山货、当铲铲匠后来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原因。于是他再次把话题引到了做山货生意上来,以探究竟。
爷爷确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十多岁开始做铲铲匠收山货。那时山货多,价格也便宜,收一背兜背出去也落不了几个钱。做铲铲匠生活无定着,经常一个人漂着,浪着,就图落得自在。往往出去一背货,回来一身轻。哪个幺店子老板娘好,就投那里去。幺店子老板娘都是为个钱,只要愿意掏钱,一百个好都有。跑跑跳跳,一年下来,除了嘴巴快乐,肚子饱外,最多只能剩下收山货的钱。后来,接了婆娘有了儿,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漂了,浪了。跑一趟货回来,称点盐,买点油,带点糖,看看婆娘,亲亲儿,小日子过得还滋润。以前的婆娘生不得,生了一个就不再生了。一混就是一二十年。儿子长大了,给他接了婆娘安了家。跑了几十年,也跑不啥动了,就让儿子跑。儿子又勤快,又节俭,有心机,会把家,跑一趟下来,总要落几个子儿,远比老子强。
桃桃两岁多,就快要过年了,儿子想再跑一趟下来顺便买些年货回来,好安安稳稳过个年。儿媳妇也想出去见见世面,就相跟着,想走水路,快点儿回家。
哪曾想,他们夫妇俩到了两河口就没有再回来。那天真他妈遇缘,该有事出。他们夫妇到两河口就要上船,碰上一伙滥杆子正好上岸。那伙滥杆子见儿媳妇人长得标致,姿色好,一个家伙就在她脸上摸了一把,另一个家伙则拿倒拐子撞她的前胸。儿子见那伙人不怀好意,就上前拉着儿媳妇赶快往船上走。不曾想那伙畜牲趁儿子不留神,硬生生将他掀进了冰冷刺骨的清水河里。儿媳妇见男人落水,不顾一切地挣脱纠缠,也扑进了江里。儿子还背着山货,儿媳妇又不会水,双双落水,哪还有个活哇。桃桃她婆婆听到恶耗,一病不起三两个月没熬过去,也去了哇。可怜桃桃一下子就没了三个亲人。好造孽的娃娃哟。后来打听,那伙作恶的家伙,就是龙头大爷张啸虎的兄弟伙。老汉本想去拼命,但一想可怜的桃桃再不能没了爷爷。这才按下这心头的怒火,记下那齐天的大仇,一个人带桃桃一天天长大。
总有一天,老汉我要烧了他狗日的房子,砍翻他狗日的几个人,报了仇才咽得下这口气。
爷爷说到最后已是咬牙切齿,桃桃则泣不成声,天祥也仇恨满腔。他趁机将所知道的红军如何帮穷苦人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惩治恶人的事讲述给祖孙俩听。
祖孙俩听得入迷,两眼放亮。他们也听人说过红军,但都是些传闻,夹杂着许多神话的成份。听天祥讲了,他们心目中的红军才真正从神话中走出来。他们好像真正看到了红军的样子,听到了红军的声音。他们向往红区,希望红军早点打过来,杀了张啸虎一伙恶人,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为所有受欺凌,受侮辱的人报仇。爷爷担心着,红军杀得了张啸虎吗,当年的田颂尧不是也拿他没办法吗。他想田颂尧是正规军,正规军对付不了的人,红军能对付吗。
天祥告诉爷爷和桃桃,田颂尧才算老几,只算得了一只癞哈蟆,又脏又丑又没用,只会胀了气,吓唬人。老牛不信那个邪,蹄子给踩上了,放了臭气,它就只剩下一褡皮了。田颂尧组织了几万人去打红军,结果被红军打得鸡飞狗跳墙,从阆中逃到古城躲起来,抱着小老婆直喊脑壳痛。
张啸虎早在红军那儿挂了号儿的,罪状就给他列了几十条。他躲得了初五,躲不过十五,红军迟早要找他算总账的,一定把他打回姥姥家,给大老婆洗脚去。
红军中的能人多的是。他们那里有个指导员,也就二十来岁,真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美国有多大,日本有多小全都晓得。更神的是,他还晓得清水河源自哪里,流经了哪些地方。红军个个都是大能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凶得很。那里的女红军有背长枪的,也有挂盒子炮的,个个神气,还有穿白大褂当医生的,敲竹板子打莲花闹搞宣传的。女红军给伤员喂奶奶的事,只听木匠师傅说过,他没有亲眼看到,自然不好说了。
桃桃对女红军特别感兴趣,问她们长啥样儿,像她这样儿的女娃子可不可以当红军,等红军真打过来了,她也去当红军。
天祥很肯定,告诉她得行,当然得行啦。指导员说了,天下穷苦人都去当红军,打倒了地主军阀,打败了日本,就自己当家作主,过太平的日子了,安逸得很。
金鸡啼鸣,时近拂晓,他们还无睡意。爷爷喊天祥这就去睡,先美美地睡一觉,好好休息一天,再说赶路的话。天祥年轻,说瞌睡来了就撑不住,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爷爷已煮滥了猪腿子,炖粑了鸡,又好好地款待了天祥一番。
天祥把背篮里剩余的货全部存放在爷爷家,说好以后来取,就按照爷爷的指点,抄道走沿清水河河岸的山路向古城方向急进。到了龙洞口,他很想进去看看,但已时近中午,不敢稍作耽搁,万一翻不过龙背山天就黑下来了,那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麻烦大了。爷爷告诉天祥,走这条路,人要年轻,灵活,有力气,脚板儿翻得快,一步不停地往前走,才能翻过山,找到人家投宿。爷爷专门找来一幅绑腿,帮他把裤脚和小腿扎了个结结实实,告诉他走这种荆棘小道一定不能把裤脚子敞起,不然进了林,到处都是巾巾绊绊的,一会儿扯住了,一会儿绊住了,不洒脱不说,还会把裤子扯得没片片,划不来的。
出门时,天还没亮,桃桃已早早地起来为他煮好了早饭。酸菜豆花儿珍珍稀饭,地道的家乡小吃,很可口,天祥吃了三大碗。桃桃像秀秀一样盯着他一个人吃,吃完一碗,马上又给满上,吃好了,给递上揩嘴的帕子。临出门时,还特地给他装上了一个烧得黄稣稣的麦面大锅盔作为干粮,带在路上吃。他走过了一个垭,翻过了一道梁,已经走得很远了,还分明感觉那双明明亮亮的眼睛还在望着他的背影,望着东南,他就要去的地方。他一时心血来潮,回首望着来路的方向,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唱了一首山歌子,只是里面的词儿他即兴作了一些改动。
太阳出来哩照白岩啊喝,
哥爱妹妹好人才哟。
秀发飘飘风摆柳哩嘿,
双目幽幽深似海啊。
最是那对酒窝窝啰喂,
又美又甜惹人爱哟。
亭亭玉立身段好啰喂,
哥想妹妹乐开了怀哟喝,乐开了怀。
歌声由近及远,在山山岭岭之间久久回荡。
桃桃虽是山里长大,但并不怕生。天祥瞌睡重,那天一觉醒来就已是下半天了,爷爷吃了饭便独自一人到山坡上去收牛晚归,家里只有桃桃陪着天祥。天祥一身轻松,这里走走,那里瞧瞧。桃桃就一直跟着他,找他说话,问他家住哪里,家里还有些啥人。当听说他姓洪,是井田坝的人后,桃桃显得特别激动,拉着天祥的双手,又是摇,又是晃,脸上光彩照人,眼睛里似乎还噙着泪花,明显流露出突然遇到亲人的那种欣喜之情。如果不是男女有别,如果不是处在情窦初开之时,如果不是还有种种说不清的东西阻挠着挡着绊着,她会扑进他的怀里纵情地大哭一场,尽情地发泄一场。多少年来,她是那么孤独,那么无助,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她渴望亲情,渴望爱抚,渴望得到来自亲人的温暖。她告诉他,妈妈也是清水河洪家的人,他们应该是亲戚,天祥就是她最亲的亲人。她对他由衷地感到亲切,一见面就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亲近感。
桃桃的情绪也深深地感染了天祥,他也感觉浑身发热,热血直冲脑门。他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尽量躲开桃桃热辣辣的眼神,回避桃桃满腔的热情,尽量不与桃桃拉手,更不与桃桃的眼睛对光。有亲近又保持着距离,是亲切又很有分寸。他家有秀秀等着盼着,最重要的是他此时身负重任。
桃桃本是一个热情外向的女子,性格开朗,心地纯真,长时期生活在山里,跟爷爷长大,自幼缺少玩伴,遇到了同龄人自然感到亲切。同天祥一天的相处,既有相通的语言,也有相通的情感。在她看来,天祥见多识广,待人诚挚,人也长得帅气,形貌俊朗,而且又存在亲戚关系,当然感到亲切,值得亲近。从内心深处萌动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情愫,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法用其它形式表示,只觉得与天祥在一起,不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动作,就感到满意,就是一种满足,挨得越近越有安全感,越有认同感,越有归属感。
龙背山怪石峥嵘,一尊尊龙骨石有的像猴子,有的像怪兽,面目狰狞。山上并没有路,怪石之间,齐胸的丝茅草丛中,脚下时隐时现被人或其它动物踩过的痕迹就是路。天祥把爷爷送他出门留给他的一把长把砍柴刀紧紧握在手里,顺手删开挡在前面的藤蔓,最讨厌的要数那种带刺的藤蔓,随时都有可能扎破手,钩住衣服,扯了裤子。
龙背山很高,天祥不停地在怪石间穿行,徒步攀登。手背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他顾不上手痛,更顾不了衣服裤子,一直撵着太阳往山顶上爬。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终于登上了山顶。他不敢稍事休息,回首望了一下来的方向,走过的路又被丛草掩没,龙骨石周围草青草黄,在落日的余辉中显得迷迷茫茫。他不敢更多逗留,转身又急速向山下赶去。
16
田颂尧吃了败仗后,红军的力量更强了,红区的地盘更大了。总指挥徐向前曾率兵对利州进行了围攻,虽然最终没有打下来,但对田颂尧的残部却给予了毁灭性地打击,从此再也不敢对红军有任何军事行动了,这些残部对红区采取一种望风式的警戒,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望风而逃。士兵对出入红区人的盘查也放松了许多。天祥到了古城,坐上水船到了利州,再向东行,只一天多的路程,就进入了红区,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指导员。
指导员正在给一群红军战士上识字课。他站在一张大黑板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战士们就跟着念。一个字教三遍,或者五遍,战士们念会了,就用树棍儿在地上一遍遍写。教的字大多数都与红军和红区有一定的关系,讲解时都是举红军和红区的例子,很容易记住。
天祥把他近段时间所做的一切都向指导员进行了汇报,仔细地介绍了他这次出来时翻龙背山的情况,并按爷爷的描述,介绍了另外两条通往两河口的道路。
指导员表扬天祥工作做得好,有成效,特别是几条路对红军西进很有帮助。告诉天祥,现在红区正在大练兵,学识字也是一种练兵的方式。红区能识字的人很少,他这次来了,就在这里多呆一些时间,学习学习,也可以去教红军战士识字。
天祥当然愿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跟随在指导员左右,听指导员讲那些他从内心十分向往,但又似懂非懂的东西,讲红军的事,讲革命的事,讲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讲如何去打日本。在他看来,在指导员那里学到的东西,在学堂里学不到,在两河口也是学不到的。跟着指导员,他就会长大,就会成熟。
报告。这天,来到一座老房子的门前,天祥的声音有点儿发涩,生评第一次喊报告,难免显得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