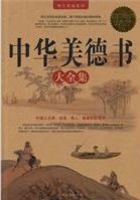清定都北京后,八旗主力驻扎在城内外,称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八个城门都有旗兵驻防。清朝统治者认为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皇帝亲自指挥正黄、镶黄两旗驻防。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正因为如此,北京北面以“旗”、“营”为名的地名特别多,而其他三个方向类似的地名就比较少。
清初八旗驻防分布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简单来说,就是两黄旗守北,两白旗守东,两红旗守西,两蓝旗守南。
康熙年间开始,八旗逐渐移居城外,因为当时在西郊营造圆明园,便从北京城内抽调八旗官兵前往保护安全。圆明园落成后,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住上几个月,并设朝理政,圆明园事实上已成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八旗护军营,规划为:镶黄旗驻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驻树村东,镶白旗驻长春园东北,正黄旗驻萧家河村北,正红旗驻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驻玉泉山东北,正蓝旗驻海淀东,镶蓝旗驻颐和园南蓝靛厂。八旗兵驻扎城外,在地名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厢红旗”、“蓝旗营”等。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在香山成立了“健锐云梯营”,是一种为攻城而单独训练的特种兵,以后这里也出现了正白旗、镶白旗等地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与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是明代的地名,明代军队中“旗”是最基础的单位,每“旗”10人,5个“旗”上有“总旗”。这些地名都是明代牧马的军队驻地。
今天的北京地图上,会找到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之类的地名,这里都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西城区还有“校场胡同”,过去北京各类“校场”非常多,今东安市场原来就是“校场”,因长期废弃不用,后来被小商小贩占据。
有趣的是,德胜门外西北,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这是当时八旗最精锐的部队,被认为是太平之地,所以此地被人们称为太平营。
明代天坛已“开放”
1918年1月1日,天坛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这是它成为人们游玩之所的开始吗?其实,从明代起,许多人已经开始拿它当公园了。
据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唯天坛游人最盛。”每年端午节,这些“游人”在此地举办骑马射柳比赛,不少太监也参与其中。
堂堂皇家祭天之所,怎敢如此践踏?因为,天坛内有神乐署,大祭时负责配乐,平时授徒,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就在天坛内办公,为增加收入,他们先在坛内开茶棚,渐次把天坛当公园,坐收门票。
明朝初期实行天地合祭,天坛活动不断,如此沿袭了多年,到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大礼议”,改为四郊分祀,又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坛的地位相对下降,祭祀活动也不那么频繁了,后来明世宗在宫内几乎被宫女勒死,搬到西苑居住,长年不参加祭祀,天坛大祀只派官员替代,管理日渐粗疏。
明亡清兴,天坛制度依旧,只要有钱,照样可以进进出出,连《顺天府志》都记载道:“挈酒游高粱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祯还写诗记载了自己在天坛品茶的感受。可见大家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祭坛本是圣洁之地,为何管理如此模糊?因为它是皇帝的财产,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没人爱惜它。
作为农耕国家,敬天法祖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意识深处,大家也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天坛属于公共财产,应该保护好它,可围上墙,大家平时看都不能看,那么,谁还会觉得那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部分北京人哄抢皇家财物,甚至主动帮助侵略者,他们平时看上去温和、谦恭,谁也没想到,他们内心的不满已压抑到如此程度。
那么,加强管理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雍正皇帝知道天坛成了公园后,曾经震怒,严加惩治,在他的努力下,短期内确实起到明显效果,可他死后不久,天坛再度沦为游乐场,到嘉庆时,神乐署内店铺林立,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要求清理。
加大管理力度,皇帝就要面面俱到,也就没时间去考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即已油尽灯枯,也难免人亡政息,清代关于天坛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条文历历在目,表面上看,权力很强大,对于违反者的惩治也很严,可就这点小事,居然管不好。
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公园,但相关制度并未落实,加上战争等因素,使它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局面才发生根本改观。
老北京的路没人修
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所有城市,莫不以修路为要务,可让人奇怪的是,作为明清两代首都的北京城,道路条件却长期得不到改善,堪称惨不忍睹。
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城市道路的规划,以唐代长安为例,主干道均宽达100多米,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只能是土路,那时连长安城的城墙都基本是土坯,只有城门的外表才用砖砌。如此宽的土路,一旦下雨,则行人举步维艰,故唐代有规定,如赶上雨天,大臣可以不上朝,不是大家想偷懒,实在是路太难走。
宋代煤炭应用逐渐普及,燃料成本大大下降,烧砖已相对便宜,但普通人依然难以承担,穷人经常沿城墙建房,以省下一面墙的材料费,但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道路自然难有改观。
老北京的道路最早也以土路为主,初期规划很完整,即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清代一步为五尺,故大街的宽度在40米左右,较唐代距离大大减少。在大街两边设有明沟,以通污水等。道路基本用黄土铺垫,因为它比较干,吸水性强,可应对普通降雨,而北京较少大雨,如此设计,堪称实用。可为什么到后来会惨不忍睹呢?
首先,京城多风,而黄土很轻,动辄漫天黄土,污染极大,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路两边本有明沟直通护城河,可常年无人疏通,导致淤死,加之护城河水源不足,清末时已到处是垃圾岛。污水无法排出,只能沿街泼洒,更要命的是穷人家没有厕所,干脆在路边明沟中解决,长年累月,淤积成堆,臭不可闻。
第三,由于土路颠簸,为了图舒适,贵族与商家多用重型马车,往往要五六匹骡子才能拉动,对道路破坏极大,许多路面上的车辙经年不去。
第四,黄土是建筑材料,此外可以用来做煤球辅料,—些贫困人家直接上街挖土,完全不顾行人利益。
几方面都在破坏,情况自然越来越差。清末民初,老北京逐步引入了西洋式马路,每个路口设警察,防止人们丢弃污物、破坏道路,并阻拦重型马车,但西洋马路成本极高,政府投入能力不足,只修了很少的几条路。
按当时国际惯例,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以路养路”的举措,即征收路捐、马车税、车辆通过费等,可王公大臣们率先反对,普通市民也不认同,大家一片喧哗,结果民意战胜了理性,只能不了了之。
于是,人人都知道现代公路好,但人人都只想搭便车,不想付出,结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真正像样的路也没几条,而当年修出的几条新路,也因无钱养护,负载过大,成了旧路。其实,即使是在古代中国经济、文化领先的一些时代,我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也往往落后于其他文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老北京皇家的“冬运会”
北京的冬天,寒风彻骨,留下了“猫冬”的说法,意思是要少运动、多保养。其实,这是特指在平日劳动时,寒冷会导致热量消耗增大,所以要“猫”。而闲暇时,则不仅不应该“猫”,反而应增加运动,故老北京冬季运动精彩纷呈。
北京冬天是按“九”来计数的,过去普通人家没挂历,只能“画梅花”,就是在墙上贴张纸,上面有九个格子,每个格子有一朵九瓣梅花,过一天用颜色填上一瓣,晴天填红色,阴天填黑色,下雪不填色。81瓣全填完了,冬天也就过去了,这叫《九九消寒图》。到清代,嫌太麻烦,改成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繁体为風)”,每个字都是九画,过一天描一笔,据说这还是乾隆发明的。
有了土日历,人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了。按老规矩,每到三九,冰嬉就开始了。冰嬉又叫冰戏,宋代就有,清代极盛,乾隆还将其定为“国技”。因努尔哈赤举兵时,专门组建了一支冰上部队,入关后,御林军的健锐营有一支编制为1600人的“冰鞋营”。为保证其战斗力,皇帝每年都要亲自校阅八旗溜冰。
校阅项目分走冰鞋、抢等、抢球、转龙射球、打滑挞等十几种,此外还要请民间艺人在冰上舞龙、舞狮子、跑旱船等。
走冰鞋即花样滑冰,穿传统满式冰鞋,将两个底部有铁片的长木板捆在脚上,一边滑冰,一边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包括托举、哪吒探海、朝天蹬、果老骑驴等。
抢等是速度滑冰,一声礼炮,众人争先,先到者有赏。
抢球则是将皮球远远踢出去,看谁先抢到,参与者需穿特制的冰鞋,这种冰鞋下有铁齿,便于急刹车。
打滑挞是从冰山上往下滑,看谁动作潇洒。
转龙射球和走冰鞋很相似,但要边走边射箭,需过两个旗门,门上有球,一为“天球”,一为“地球”,每个旗门可射三箭,必须中一,否则挨罚。
与今天不同,清代八旗都是终身军人,他们的孩子也入军籍,因此阅兵时不仅大人上阵,小孩也要参加表演,以示明日军备一片光明。此时皇帝也会乘坐专门的“冰辇”,由冰鞋营牵引,绕场巡视。传统“冰辇”很重,行动慢,为此,奥地利皇帝还赠送给光绪皇帝一乘西式“冰辇”,造型很像马车,只需八人牵引。
老北京冬天,富裕人家常模仿“冰辇”制作所谓冰床,可乘3—5人,一边观景,一边饮酒作乐。冬季太冷,牵引的绳子勒手,易冻伤,所以要用骆驼毛做,柔软且保暖。
至于普通的老北京人,最经常的运动还是滑冰和抢冰球,后者尤其普及,但一般不扔球,而是一人将碎冰踢远,众人争抢,由于挤在一起,往往一摔倒一片,用老北京话说,这叫“抢冰球,看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