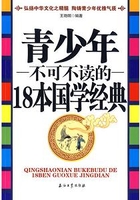缺乏统一的语言标准,给沟通带来了巨大麻烦,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湘乡人,可湘乡话却是全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再比如康有为被召见时,光绪皇帝怎么也听不懂他说的南海方言。为避免难堪,清末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不得不破坏历来的规矩,允许召见时带一名随从,充当“翻译”,而此前清代的召见,除军机大臣,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室内不得有闲杂人等。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地位。
崇祯究竟死在哪儿
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遗址至今犹存,且有石碑为证,许多人以为这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约12公里,外城墙约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
3月18日夜,农民军攻破外城,崇祯带十几名太监逃离皇宫,到齐化门,守军不认识他,以为有诈,将其射回,转安定门,没想到门闩沉重,太监们无法抬起,正是这根沉重的门闩,彻底改变了明朝历史。
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
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
1931年,故宫博物院始立“明思宗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抗战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
从档案照片上看,1931年时“罪槐”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而照片上的槐树胸径不过一尺,生长得也过于缓慢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冒名成了“罪槐”。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当年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
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信以为真,未免贻笑大方。
死者覆面源于崇祯吗
逝者以白布覆面,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丧葬习俗,有说法认为它来自老北京。据说,明崇祯皇帝上吊前,特意嘱咐太监以布覆其尸体的面部,因为他丢了江山,无颜见列祖列宗。
北京是首善之区,礼仪最为正规,全国各地取法都城,也属正常,但此说有两个疑点:首先,崇祯自杀前,身边只剩老太监王承恩一人相随,王同时上吊自杀,以布覆面之嘱怎么传给后人?其次,据史籍记载,崇祯是以发覆面,并非覆布。
考察此俗来源,可根据考古发现来研判。事实是,早在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便已发现覆面,多用玉,由于好玉难得,故生活用玉不小心碰伤或摔碎后,往往改造成覆面的材料。这一习惯不仅中原有,西域、内蒙古、契丹都有,可见流行之广。
覆玉为什么变成覆布了呢?因为覆玉并不是直接放在脸上,而是先覆布,再在布上放玉,而普通人无玉,就只能覆盖一层布了。覆布易腐烂,故出土时多见覆玉,少见覆布。
既然覆布之俗已有2000多年,那么它是何时产生的呢?传说有二:
一说是源自吴王夫差,他在战胜越国后,不听伍子胥苦谏,放松警惕,后来甚至逼迫伍子胥自杀,伍死前说要把眼睛悬挂在城门上,亲眼看到吴国的灭亡。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灭掉了吴国,夫差死前嘱咐尸体覆面,因为无颜见伍子胥。
二说是源自春秋时的齐桓公,他晚年不思进取,不顾管仲、鲍叔牙的劝谏,亲近易牙、竖刁等奸臣,结果被他们窃取权柄,关押在宫内,活活饿死,奸臣们秘不发丧,以追杀齐桓公的亲信和子女,尸体在宫中放了多日,身上的蛆虫甚至爬到了宫门之外。齐桓公临终时托付宫女,以绫罗覆面,以示无颜见管仲、鲍叔牙。
两种说法大同小异,虽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显然是后人穿凿附会,不值一驳。
那么,人死后为什么要覆面呢?学界至今也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有三种说法:首先,人死后面目狰狞,既然丧礼规模盛大,则覆其面既尊重逝者,也尊重来宾;第二,古代医学不发达,认为停止呼吸是死亡的标志,但有的人休克很久,气若游丝,却又能苏醒过来,为鉴定逝者确实死掉了,一般会以绸布或纸覆其面,等候半日,如果有轻微起伏,表示这个人并没死;第三,古人并不把死亡看成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即进入阴界,阴界畏阳光,故覆面以遮挡,让死者更舒适。第三种说法有考古发现佐证,新时期时代,部分先民已经用打碎的大陶罐为逝者覆面了。
由上可知,覆面之俗与崇祯无关。
老北京的衙门不好混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是过去老北京人对各官府机构的准确评价。从理论上说,古代官员非世袭,多是平民出身,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上官员,却为何不愿给老百姓办事呢?
因为科举考试严重脱离实际,比的是谁能背死书,官员们满腹经纶,却无办事能力,只会讲大道理、争道德制高点,靠价值观来断事,具体操作全赖小吏。在老北京,各级政府少不了书吏,他们熟悉法律规章,却没有正式身份。
当好书吏并不容易,先要拜老书吏为师,并在其帮衬下进机关,第一年叫“事务”,只能打杂,没任何收入,连午饭都得自己准备。第二年叫“写字”,官方给午餐费。第三年叫“贴写”,依然抄抄写写。两三年后,可升为“注销”,负责来往文档。以后升为“说堂”,可与长官接触,再升为“值宿”,在领导下班时独当一面。再往上是“办稿”,替领导写稿。稿写多了,就成了“看稿”,最终为“经承”,是书吏的头目。
书吏升迁艰难,其间备尝人情冷暖,可清廷却规定,“经承”最多任职5年。清廷担心,老吏业务过于烂熟,将操纵官员,可如此刻薄,不仅执行不下去,还会产生副作用。
事实上,各衙门都是应付了事,“经承”一到5年,便让其更名改姓,糊弄上级,因为官员们确实已离不开这些老吏,上级对下属的小动作了然于心,但想到自己部门也要靠老吏,故视而不见。
清廷用老吏,却又防老吏,且在制度上克扣老吏。清代各部门经费中,虽有“饭银”支出,但远远不够书吏们养家糊口之需。为维持团队稳定,“经承”只能自掏腰包,可这么大的亏空,总不能自己出,这就逼着老吏们贪污腐败,到后期,成为公开的“陋规”。甚至连发给曾国藩的军饷,也需向相关部门缴纳“陋规”,否则就拖欠不给,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吏治败坏如此,为何不加整肃呢?首先,到清末时,问题已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成本太大,所谓“官帮官,吏帮吏”,动一个老吏,各部门老吏或请托,或找门路,甚至集体罢工,部门工作立刻瘫痪;第二,老吏虽是蠹虫,却是封建皇权所需要的,皇帝希望官员无能,这样才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而老吏虽能干,却名不正言不顺,名誉又差,且多有贪污腐败的案底,故更容易操纵。
“治官不治吏”,结果清末屡次整肃官场,皆流于形式,“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始终未能打破,对老吏来说,他们手握大权,却得不到尊重,升迁无望,连正式工资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廉洁奉公,更不会为百姓办事了,老北京对衙门评价颇低,不是没来由的。
老北京曾经鸣炮报时
“晨钟暮鼓”,老北京报时都依靠它,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还有另外一种报时法,即每到中午在德胜门、宣武门鸣炮,俗称“宣武午炮”。
炮在古代战争中作用巨大,明末为对抗清军进攻,大量进口“红衣大炮”。一说红衣为红夷之讹,因当时红头发的荷兰人在亚洲影响甚大,明朝常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采买火炮,另一说是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故名之。两说皆有道理,明朝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交恶,贸易往来极少,基本没从他们手中买过炮,大多数炮是在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多是英国造。
“红衣大炮”一度改变了战争格局,造就了袁崇焕的威名,但由于制度腐败,大量明朝军队降清,清军也掌握了制炮技术,并成为其鹰扬天下的法宝。
1653年,明亡后第九年,为加强京城防备,济尔哈朗提议,顺治皇帝批准,在北海公园琼岛和内城九门上各设信炮五门,并立五根旗杆,遇到紧急情况,白天挂旗,晚上挂灯,并立刻鸣放信炮,以提醒警戒。当然,炮不能乱放,需持金牌传令才行,各门信炮需同时鸣放。
这些古炮体现了当时造炮的最高技术,重约800公斤,安放在木制的炮车上,进退自如,并可左右调整方向,和现代炮车设计非常近似,与电视剧中的笨重之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以后清代长期和平,武备松弛,造炮技术一落千丈,到清末时,水平甚至不如明末,故城楼上的古炮一直没被淘汰。1924年,溥仪离开故宫,北京钟鼓楼不再报时,为服务市民,每到中午,便在宣武门城楼上鸣炮报时。
为什么选择在宣武门?因民谚称:“崇文、宣武各西东,左亡明,右亡清。”明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崇祯,而清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宣统,分别是崇文门、宣武门的第一个字,所以民间将宣武门看成是清朝灭亡之门。
没想到,宣武门首次鸣炮便发生了意外,震塌了周边的民房,只好减少炮的数量,为避免声音变小,北城听不到,便在德胜门同时鸣放。由于鸣炮报时始于宣武门,加上当时宣武人口更密集,故人们习惯上仍称为“宣武午炮”。
然而,“宣武午炮”用的真是古炮吗?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古炮已陈设数百年,太危险,操作也比较复杂。因此,今人多认为是当时北洋军阀调了两门退役的克虏伯野战炮当“午炮”,只是当时古炮仍在城楼上,留有照片,遂让后人产生误解。
1927年,为方便交通,宣武门、朝阳门城楼被拆,城上文物、建筑材料都被变卖,以弥补政府官员的欠薪,但保留了部分瓮城。
到上世纪30年代,因放炮报时花销太大,被迫停止。1933年,宣武门瓮城亦被拆除。
老北京为何会馆多
在老北京文化中,会馆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老北京俗语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多集中正阳门外),士子出入宣武门(文人会馆集中在宣外),商人出入崇文门(这里是税关,商人多居住在附近)。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仅宣南一带就有数百家会馆,在这些会馆中,上演过热血沸腾的“公车上书”,鲁迅先生完成了《狂人日记》,在京剧发展史上,会馆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有了这些会馆,各地优秀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让北京文化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会馆多,是老北京独有的一景。
北京会馆的兴旺,始于明代,清代达到极盛,原因有三:
首先,明清农业高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开土地,从事商业。据估计,明代粮食平均亩产245斤,较宋代多80斤;清代粮食平均亩产达310斤,较明代又提高了65斤。明代耕地面积为9亿亩,清代为13.8亿亩。明清农业高速增长与引进美洲作物有关,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政府鼓励商业,明张居正执政后,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农民纳税不能再缴纳农产品,必须到市场上折合成银铜,这个举措带有鲜明的前现代的特征,鼓励农民与市场主动结合,促进了货币的崛起,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观念转型,中国历代重农抑商,但明代主流学者大多对商人抱同情态度,因为这些学者、官员多来自南方,地稀人稠,人民不得不经商,王阳明、李贽、黄宗羲等都曾在著作中为商人抱不平。清入关前,依靠商人贩运中原军火、铜铁料、盐等,明政府三令五申,却始终无法禁绝,入关后清廷对商人抱有好感,管理措施相对宽松。
明清商业发展迅速,这为会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成祖迁都后,北京成了科举的中央考场,大量学子来京,生活无着,刺激了会馆迅速繁荣。
商人们在京建设会馆,为乡党提供住宿条件,一方面是出于乡里情谊,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投资,如果学子科举成功,成为官员,所带来的回报巨大。在封建社会,皇权缺乏足够的能力,无法对乡村社会直接治理,因此也非常注意利用同乡的认同感,将其转化为管理工具,明知会馆可能滋生腐败,依然变相鼓励它的发展。
以芜湖商会为例,1905年成立时,会长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杰,有二品衔,其他负责人汤善福、翟寿芳都是四品,官商一体,明目张胆。
传统会馆多是同乡捐建而成,除特别贫寒的举子外,落榜者不得久住,需回乡复习,除了大考之年外,平时非常宁静。会馆的管理完全依赖乡土观念、血缘关系,宗法色彩浓厚,但一般情况下,会馆馆长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
清代皇帝会养生
明清皇帝都以故宫为家,在这里生活与办公,有趣的是,清朝皇帝寿命更长,平均达53岁,而明朝皇帝只有42岁。康、乾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长寿皇帝,令人好奇:难道清朝皇帝的基因更有优势?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在抗生素发明前,人类平均寿命一般在40岁左右,因为婴儿死亡率高、出生风险高。中国历史上共产生了335个皇帝,虽然有被暗杀、夺权的风险,但整体保健水平较高、日常风险低,可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1岁。
古人平均寿命和现代人无法相提并论,考虑到这个因素,清代皇帝应属长寿,究其原因,不外有四。
首先,清朝皇帝生活比较规律,明代皇帝经常不早朝,而清代皇帝则兢兢业业,有时凌晨4点便起床,因朝会经常安排在五六点,坚持早起早睡,契合“养生之道,常欲小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