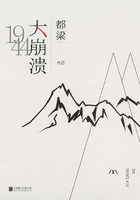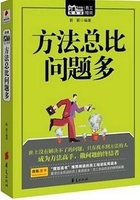1
叶子头很痛,一直痛。
这痛苦就像是噩梦后遗症那样,随风而至,即使在睡眠中也不放过她。身体忽冷忽热。前面有一棵树,一半枯萎,一半生长。
她从梦中惊醒,赤着脚走过一段木楼道,来到母亲身边,告诉母亲她的梦。
母亲笑着抱起她,告诉她,冬天和夏季不会重逢。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叶子,我相信你是坚强的。”
有一双温暖厚实有力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从轻轻喘息的声音,从咔咔的脚步声,她知道那是谁。她转了个身,把脸埋进他的手掌心里。
“许多个夜晚,母亲总是安详地坐在那里,手里织着给我的毛衣。只有一个夜里,那天是父亲的忌日,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我光着脚,循着声音走去,发现那是母亲房间里传出来的,一声声压抑的哭泣。我想走近那扇门,却像魔怔了,怎么也走不过去,犹豫着,徘徊着,最终只能蹲在墙脚捂住自己的耳朵。可是睡了一觉之后,我什么都忘了,我不记得母亲哭泣,因为在我眼前,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的笑容掩盖了她的痛苦,这让我在成长的岁月里淡化失去父亲的悲伤。父亲走后,母亲从未带男人回来。那时,我还小,还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可现在当我明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心真痛!那时她才三十多岁,她的身边应该有爱她的男人!可是她没有,她只有我。只有我……”
她在说,她一直在说。他强忍着泪,轻轻地安慰。
“叶子,你母亲有你,是很幸福的!”
她慢慢睁开眼,光线很刺眼,像一根根针。看到他心疼关切的脸,她微微地笑了笑。安德烈扶她起来。她攀着他的臂膀,脑袋无力地倒在他的肩上。
“是么?”
“是的。你要相信。”
“安德烈,我现在才知道,这些年母亲心里有多痛!我记得,有一次家里漏雨在收拾屋里时,我们翻出了父亲的衣物,父亲的东西母亲一件也没丢掉。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默默地整理父亲的遗物。突然,母亲很大声地对我说:你爸爸是我选的!我有点惊异地看着母亲,她说话向来是柔声细语的。母亲并没有察觉我的惊异,她手里拿着父亲的一件旧外套,抚摸着,脸上带着笑,像在跟自己说话似的,我这个人呀,说挑不挑,但是有一条很固执的原则,那就是找的对象不能比我大!一个女人要找比自己小的男人做丈夫,这是多么奇怪的念头啊。在旁人眼里,我简直就是个怪物。我也因此错过了几个在你外公外婆眼里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男人,却仍固执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那时候我已经不小了,找个比自己老的男人都有可能找不到,更不用说找个比自己小的啦,你外婆愁得常常背地里抹眼泪。可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想,我要的那个男人就在来找我的路上,说不定明天他就来了。呵呵,没多久,你爸爸真的就来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我问母亲,为什么一定要找比自己小的男人。母亲说,女人总是比男人寿命长,男人走了,留下女人孤零零的,多痛苦,我就是不想死在自己男人后头,找个年纪小的,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走在黄泉路上。母亲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你爸爸还是走在我前头。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我无法改变这个命,好在,他把你留给了我。母亲,她为了我付出了一切,而我又做什么呢?除了傻事,什么也没有做!”
“叶子,你母亲是幸运的,因为她装着所有的爱,所以她做每件事情都会感到幸福!”
“但是这种幸福是残酷的!”
“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已,我相信对于你母亲来说,那是一种甜蜜和温暖。即使是对你父亲的回忆,那也是一种幸福。叶子,你要振作起来,没有一位母亲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你母亲会想,她的叶子是坚强快乐,美丽和幸福的。因为你拥有她的爱。不管她在哪里,她的爱是不变的。”安德烈抚摸着叶子的头发,“叶子,生活使我懂得,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为什么会绝望,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驱赶心中的恶魔。这恶魔使我们不会理智地克制自己,做出悔恨的蠢事。它使我们意志薄弱,会不时掉进深潭。可是我们又时常会鬼迷心窍,就会让愚蠢蒙蔽双眼,进入错误的岔道还不知道。记得在狱中那段日子,我整日整夜睡不着,感觉这个世界令人窒息。我疯狂撞墙,绝食,有一天夜里,我晕死过去,我的灵魂看见了卡琳娜,她对我说,你必须活下去,因为你还有伊凡。是的,我还有伊凡,为了伊凡我没有理由逃避一切。叶子,那一刻,我感到力量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对于任何一个父亲和母亲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生命和希望。有了孩子,父母亲所经历的哪怕是痛苦也是一种幸福。叶子,没有人能让时光停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今日的事和现在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你无法退缩。当然,过去的经验要总结,未来的风险要预防,这才是智慧的。”
她一动不动地俯在他怀里。他的嘴唇贴在她的头发上。
“我们会找回幸福的,”安德烈说:“叶子,我感觉到了。”
就像是闪电划过天空一样,他的话烧灼了叶子内心的迷茫和疼痛,反而使她豁然开朗。她点了点头。她愿意相信他!虽然母亲的爱有时候在折磨着她,但她明白,那是一种强烈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拿不走的爱。她们共有的血缘,已把彼此的身心连在一起。此时此刻,她更确信安德烈是爱她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进入对方的心间。叶子从中得到了安慰和力量。
好半天,她才从他的肩上抬起头,看到桌上的药和针筒,她有些恍惚:“我病了么?”
“没什么,只是睡得久了点。”
“哦,我好像只做了个梦……”
“是哦,只做了个梦。” 他吻了吻她的额,笑着站起来,“你还太虚弱,得好好吃点东西。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有一种久违却又有点陌生的香味在屋子里飘散。她坐着没动。安德烈关了火,端来热腾腾的一碗粥。
“白米粥?”叶子诧异。在法国,这种在中国最平常不过的食物根本绝迹,老外是不吃这种东西的。安德烈怎么会煮中国人吃的粥?
“在市场问一个中国女人,她说中国人都喜欢喝粥,而且热乎乎的粥喝下去,有助于恢复体力。这是按她教的方法煮的,快尝尝,我煮的中国不中国?”
叶子心头一热。自己真的睡了好久,久到现在还像在做梦。
接着安德烈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包榨菜,打开放在粥里,对叶子说:“那中国女人还说,中国人吃粥喜欢就着泡菜。对不对?”
“你呀,现在都快成半个中国通了。”
他笑着点了点她的鼻子,“为了你,我愿意变成整个中国通。”
叶子抬起头来看着他,漂亮的大眼睛里透着欣喜。正准备张口时,门被推开了。
“啊,叶子,你醒了!”伊凡惊喜地冲过来。
“嗯,我醒了。”
伊凡扑到叶子怀里,像个大人似的说:“这下,我总算放心了,你不知道吧,你都睡了……”
“伊凡,叶子需要休息,你不要吵她。”安德烈向伊凡眨眨眼睛。
伊凡咧嘴一笑,冲着叶子吐了吐舌头。突然长吸了口气,“啊,好香啊!”
“伊凡,想吃吗?” 叶子把碗在伊凡面前一晃。
就在这时,安德烈伸手一捞,把伊凡捞到怀里。“你这个小馋猫,那是给叶子的,你的晚餐在餐桌上。”安德烈把儿子甩过肩头,伊凡挥舞着双手,乐得哈哈大笑。
吃过饭,叶子要下床洗碗,被安德烈拦住,“下床太猛你会头晕,快躺下,这里一切有我。”他又回头对伊凡说,“好好守着叶子。”
“是!爸爸。”
听到厨房那边传来哗哗水声,叶子小声问伊凡:“伊凡,我睡了多久?”
“你睡两天了,都不醒,我都快急死了。爸爸请来医生,开了药,还给你打了针。今天我都不想去学校,可爸爸说有他守着你不会出事,我在学校一直想着呢,一放学就跑来了。”
叶子“哦”了一声,记忆里有一段空白。她怎样从阿芰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她一点想不起来。
“是你和爸爸在照顾我?”
“嗯,我和爸爸这两天都没回家,嘘,爸爸不让我告诉你。”伊凡小声说。
“哦哦,我想我是丢了魂吧!”叶子恍然。
“没事儿,有人会帮你捡回来的。”伊凡脆生生地说。
“谁帮我捡回来呢?”
“我爸爸呀!我丢的东西全都是他找回来的。”
叶子不觉抬起头望向安德烈,他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她,眼里是晶莹的光。突然间,她心底涌起一股乐音,似乎是什么遥远朦胧的地方的一把小提琴,美妙的乐音在山林里围绕。
2
通往真相的门打开,迈进门去仍需要足够的勇气。有时候,叶子仍感觉自己像被绑在一根绳索中央,两端都有人在用力拉她。前行还是退缩,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拉走她,可当那两人势均力敌时,她就会被绳索勒得喘不过气,最后被拦腰截断。害怕犹豫,她会有。但是,她仍是坚强和勇敢的,不会永远害怕犹豫。既然真相已经存在,知道它,比起逃避它,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坏。
晚上,伊凡要回家看小男孩。叶子坚持让安德烈和伊凡一起回家。
“你身体刚好,一个人能行吗?”安德烈不放心。
“我全好啦!”叶子说着,做了个伸展运动,“看,我多有劲。明天就可以去上学。”
安德烈笑了笑,没有再坚持,又叮咛了几句,和她吻别。望着父子俩走远,叶子提起外套,冲出门,向地铁站跑去。她必须去找阿芰。
几天不见,阿芰像大病了一场,明显苍老了许多,头发里的灰色也开始泛白。回忆使她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灵魂,正视自己的痛苦。这令叶子于心不忍。但也许真如安德烈所说,痛苦即幸福,无人能拒绝。她一见到叶子,精神立即振奋起来。
叶子最终还是沿着阿芰的讲述,走进母亲曾经真实的生活。阿芰说,她和叶子母亲的幸福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
2003年6月的一天上午,阿芰和母亲像往常一样在餐馆厨房收拾碗碟,准备马上开门营业。老板发现当天的生菜不够,那段时间餐馆做的春卷卖得不错,法国人吃春卷,习惯用生菜菜叶包裹着吃,称那才是正宗的吃法。老板临时叫母亲去附近的市场买几棵生菜回来。母亲刚出门,十几辆大小警车呼啸而至,阵势惊人。
那段时间巴黎很不太平。巴黎郊区阿拉伯、黑人因抗议政府的不公平待遇,大肆焚烧车辆,仅两三天的时间,巴黎郊区就有五百多辆私车及公交车被烧毁。骚乱刚刚平息,阴影还未从人们的心里完全散去,大家看到那阵势都感到十分恐慌,以为又发生了什么大事。餐馆老板和几个工友好奇地站在门口观望。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全部控制起来,要他们一个个出示证件。一个警察还拿枪指着老板,要他拿出餐馆账本报税单。看到那阵势,一向见多识广、随机应变的老板都吓傻了,他说他开店十几年来,这么多荷枪实弹的警察闯进来,拿枪指着他,还是头一遭。
躲在厨房的阿芰听到警车呼啸声就已吓得直哆嗦,又听见楼上人声嘈动,更是吓得不知往哪里躲。就在那时,有个工友拖着个大垃圾筒从她身边走过,她急中生智,打开盖子就跳了进去,工友见状,又往里面倒了两袋子垃圾把她严严实实地埋住。当时她只有恐惧,只求不被抓走,什么恶臭肮脏全都顾不上。不一会儿,她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和人声。是警察冲进厨房来了,她在垃圾筒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听老板和工友说,除了警察还有劳工税务部门的人,他们在店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巴黎治安不好,中国人又往往是街头混混打劫的对象,许多人害怕身份证件丢失,一般没有随身带证件的习惯。警察不由分说把店里几个没有证件的工友全都拷走。事后,老板收齐了他们的证件送到警察局,人才被放出来。但有一个没有身份的洗碗工却再也没有回来。老板说他已由警察局送交到移民局,可能被返遣。阿芰在那臭气熏天的垃圾筒里闷了一个多小时,被人拉出来时,她几乎失去意识。
自那次惊吓后,差不多一个月,阿芰不敢出门,不敢上街,更不用说打工了。母亲默默地维持着她的生活。虽然母亲也逃过了那场劫难,但随后的处境却很糟糕,餐馆老板经历了被枪指着的经历后,也不敢再雇佣没有身份的黑工。失去工作,母亲只能去找点临时工干干,今天在这个餐馆洗碗,明天去那家看孩子。她一天天消瘦下去。阿芰不忍心拖累母亲,做了暗娼。
阿芰说她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做的第一笔生意。
那天夜里,母亲很晚没有回家。阿芰很担心,就到楼下去等。她不知怎的走出了小巷,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过马路的时候,一个男人紧挨在她身边。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继续往前走。那男人跟了她许久,突然伸出手紧紧抓住她的手臂。你要去哪儿?男人问她。她茫然地望着他,摇了摇头。好奇怪,那一刻她一点也没有害怕。放开我。阿芰勉强动了动嘴皮。他慢慢松开她的手臂,好奇地说,夜里,一个单身女人,在这个时辰的巴黎,你到底想去哪儿呢?阿芰还是没有回答他,不过她也没有再往前走。男人撤回身,看了她一会,一把拉住她说,那么跟我走吧。就这样,她像个失魂人,跟着那男人。男人拦了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一个小旅馆。她做了第一笔生意,甚至连那男人的脸都没看清。第二天醒来时,男人已经走了。床头放着两张百元大钞。阿芰呆呆地望着那两张百元大钞,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连后怕也没有。她去浴室痛快淋漓地洗了个澡,然后就离开了旅馆。
阿芰揣着那两百欧元,拖着母亲去了一家好馆子,美美地撮了一顿,她还要了一瓶好酒,一个劲地与母亲干杯。阿芰说她永远也忘不了母亲看她的眼神,是心疼是痛苦是无奈是悯惜,没有一点点瞧不起。她心里很清楚,母亲知道那钱是怎样来的。母亲什么也没说,仍旧像往常一样陪她吃陪她喝。就凭母亲这一点,阿芰记得她一辈子。
那时阿芰风韵犹存,生意渐多,赚的钱比打餐馆工要多得多。有一段时间,一个法国男人常来找她。那男人出手大方,而且不像其他客人变态动粗,他对阿芰很温柔,与阿芰过完夜,还会送阿芰回来。阿芰无法拒绝这样一个男人,终于有一天在住处接待了那个男人。没想到却被同屋的上海女人撞上。从此她们就对阿芰指桑骂槐、冷嘲热讽,她们不愿与鸡住在一起,发誓要将阿芰赶出去。阿芰说要不是舍不得与母亲分开,她是一天都不愿在那个屋檐下住下去。可是那地方房租实在是便宜,如果叫母亲和她一起搬走,那就得加重母亲的负担。她不愿也不能。她想只要她不搬,那两女人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于是她与两个上海女人明争暗斗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她们做得绝,告到房东那里,房东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她只好与母亲分开了。临走时,母亲把那件红风衣送给了她。
阿芰受够了与人搭铺的苦,想方设法租个房子单独住。她是干那个的,自己也觉得无脸见人。因此,与母亲分开后,她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找母亲。有一天晚上她遭到打劫,手机被抢,丢了与往日朋友熟人的联系方式,她也彻底告别了过去的一切。阿芰说她其实还是忘不了母亲,她从不到母亲住的那条街去做生意,也是害怕母亲遇上难堪。有一次她路过那里,望着那幢楼好久,终于下决心上去了,却被告之,母亲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