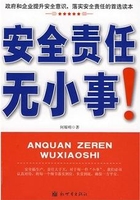一句心动,让云兰也沉默了。
那时候,云兰心底恍惚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只觉有些人,生来就注定是要相遇的,可是相遇或者别离,早在相识的最初也已注定,无法逃避,亦无法抽离。
她至今也想不出,甚至也不敢想这注定相遇的两个人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有一点她可以肯定,老天既然笃定了要捉弄人,就不会轻易罢手。
然而这一点,或许灵歌比谁都清楚。
由于心情的影响,灵歌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好转。
曹嬷嬷见灵歌一直郁郁寡欢,心道她可能是思念家人,遂将其母苏氏也唤入府内一同照料。灵歌见了母亲,未免其担心,只得强颜欢笑,云兰看在眼里,委实是说不出的心疼。
这一日傍晚,用过晚膳,灵歌靠在床头,怔怔地望着窗外的花海出神,四个嬷嬷退下用膳,皆不在屋内,只有苏氏坐在灯下,一边绣花一边与云兰聊着刺绣。
屋内燃着熏香,是早先灵歌装病之时,太子送来的贡品之一,沉静的香气不仅可以安神,还可以驱赶蚊虫,云兰本欲带往行宫,没想在这里就先用上了。
想起太子,云兰不由有些闪神,平心而论,她对太子的好感,或多或少是多于英亲王的,虽然她也开始喜欢英亲王,但相对来说,太子总是比较务实。当然,不管怎样,两个人对于自家主子来说,都是万万不可沾惹的人物。
“主子,夫人绣得鸳鸯可真是一绝,您为何就没学一手呢?”
见灵歌又开始发呆,云兰忍不住故意取笑了一句,只想让她开怀些。
灵歌转过神,理了理空茫的思绪,这才笑了笑,“我娘自幼就心灵手巧,少年时在十里八乡可是出了名的,我一生下来就笨手笨脚,自然学不了这好手艺。”
“你是偷懒!”四个嬷嬷不在,苏氏说话也随便了些,“当初让你学女红,你都能跑到树上躲一天,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教训你的了?”
灵歌低眉一笑,却没言语。那段皮肉受苦的日子,她怎么可能会忘?想来灵家祠堂的列祖列宗都已厌烦了她,三天两头去他们跟前跪着,却毫无悔意。
云兰笑了笑,“灵老爷该是心疼主子的,即便教训也是轻罚,要不主子怎会到现在也拿不起一针一线呢?”
苏氏皱了皱鼻子,一脸不苟同,“这你可说错了!我家老爷严厉是出了名的,要罚那可是真罚,只是这孩子脾气倔,越罚她就越不学,最后反倒把老爷气了个够呛!”说着话,放下手中的绣品走到灵歌身边,拉过她的手坐下,“原本我以为,我生不出儿子,又生了这么个不听话的闺女,这辈子就算完了,谁知老天有眼,她反倒成了这家里最出息的一个,我这个做娘的,也跟着沾了光,享了福,如今想一想,还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想起大夫人往日的欺辱,想起丈夫昔日的冷落,眼泪就那么流了下来,止也止不住。
灵歌赶忙坐起身,拭去娘亲脸上的泪水,“娘,您这是做什么?让云兰看了笑话!您为我忍了大半辈子,如今享福也是应该的,女儿没本事,争不上个宠妃,不过女儿答应您,一定不会给您丢脸,不会让您失去您该得到的一切!”
苏氏又哭又笑地点头,也紧忙擦着眼泪,“是娘失态了……。”缓下情绪,方又道,“娘不求你去争什么宠,家里不过这几个女人,已经闹成这样,娘看了这么多年,还会不明白吗?后宫佳丽三千,你怎么去斗?娘还能活几年?用不着那么些福气,只求你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也就够了!”
灵歌红了眼圈,吸了吸鼻子,忙垂下头,“娘放心,女儿心里有数。”
“有数就好!”苏氏欣慰地拍了怕她的手,叹了口气,又起身走回灯旁,“每个做娘的,都盼着自己的闺女嫁得好,你入宫匆忙,娘也没来得及给你绣个鸳鸯,图个吉利,正巧趁这次机会,给你绣一双,娘就盼着你,能心想事成,好事成双。”
“心想事成……好事成双……。”
灵歌念着念着,一直隐忍的泪终是夺眶而出。苏氏忙过去安慰,只是除了云兰,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哭。
是夜,月华凝成一抹氤氲的清雾,宛若烟丝轻绡。
灵歌轻轻坐起身,看了一眼犹自伏在桌案上沉睡的曹嬷嬷,悄无声息地出了房。夏日的夜晚,月淡如水,阵阵虫鸣传来,反而更显幽静。
漫步在屋前的庭院,四周的景物皆是那般熟悉,只是不知是因为心境还是身份的转变,灵歌只觉愈看愈是陌生,仿佛自己真就只是一个过客,从未属于过这里。
穿过临水复廊,抬目远眺,远处那一片竹林,依旧修竹簇簇,安逸不张的挺立。她记得,那曾是她夏日里最钟爱的地方,竹林,加上林边的一弯溪流,汇成了她儿时所有的快乐。
只是如今,那些快乐还能找回来吗?要知道睹物思人的后半句,永远都是物是人非。
寻着淙淙水声,回到满溢着竹叶清香的林间。溪边那块与师父一起寻来的白石依然还在,只是底边已长满苔藓,显然许久未有人理会过它。
“这么久不见,有没有想我?”灵歌轻抚着它,像抚摸一个孩童。浅笑坐于其上,长长的裙裾散落入水,瞬间便被浸湿。
“小主风寒未愈,衣衫若湿,只怕病情会加重。”简之的声音突然从身侧传来,虽然声音不大,还是吓了灵歌一跳。
怎么会是他?灵歌站起身,“你怎么在这儿?”算日子,昨日他们便该到了行宫。
简之一笑,从袖中取出一支精巧的古瓷瓶与一个锦绣香囊,呈递道,“太子殿下听闻小主病倒,征询过太医之后,特命奴才快马将这瓶七宝玉露丸和这个宁神香囊送到小主手中,祈望小主早日康复!”
“太子……。”灵歌讶然接过瓷瓶与香囊,心下禁不住又涌起一股暖意,“太子还好吗?”大皇子监国,他该是听了不少流言蜚语了吧?
简之自是心细,略略一想,便也明白灵歌所指,当即道,“小主放心,殿下一切安好!奴才与殿下在外奔波十年,再大的风浪也见了,只这一点小事,殿下不会放在心上!”
“那就好。”灵歌这才放下心,“替我谢谢太子,相隔这么远,还劳他惦记,实在是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日太子殿下若有吩咐,我必定会倾力而为,以报他这份情谊的。”
简之闻言,垂下了头,“小主言重了,只怕,殿下不会想要回报的。”其实,有一事他刻意没说,临行前,若不是他将太子打晕,恐怕太子早已不顾一切亲自前来探视了。
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局势微妙,一旦被人发现太子不在行宫,而且去向不明,势必会引起一番骚动,到时若再有小人作祟,只怕后果不堪设想。再加上太子那焦急的模样……他真怕日后会生出什么大祸,毕竟,她是皇帝的妃子呀!
灵歌也沉默了。经历了岳沨一事,她已不再是那个对男女之情淡漠无知的少女,只是连让自己心动之人她都无可奈何,又何况是明日之君呢?
“简总管,太子的厚意我心领了,只是这些东西——”灵歌欲还回去,然而话未说完,便被简之急急打断,“小主,有人来了!您保重,奴才先走一步了!”话音未落,人已没入竹林,转眼不见了踪影。
远处,传来曹嬷嬷急切的呼唤,灵歌看了一眼手中的东西,只得微叹一声,放入了袖中,迈步往回走去。
深夜独自外出,虽安然无恙,却仍免不了被曹嬷嬷一顿唠叨。灵歌只微笑地听着,时不时撒两下娇,道一声歉,事情便也不了了之。
只是值夜的守卫又被她害惨了,罚了半个月的俸禄不说,还被无情地拉去操练了起来。想来也有些奇怪,她那么一路走过,竟没有一个人发现她的存在,到底是这些禁卫军真的能耐有限,还是早已习惯了玩忽职守?
若是后者,那么皇宫与行宫的安全,还真是让人忧心。
这一日,太医诊过脉,面上难得透出了喜色。“小主脉象沉稳,可见身子已经大好了,如此下去,再过一两日,便可启程回行宫了!”
曹嬷嬷一听,更是喜上眉梢,二话没话,已先命人飞鸽传书示与太后,灵歌见状,不由哑然失笑,不是自己的奴才,终归不是自己的,即使伺候的再尽心,心也不在这儿。
“小主您先歇着,奴婢去吩咐车马,让他们早些准备,也免得到时候抓瞎!”曹嬷嬷显得异常勤快,似乎早已归心似箭了。
灵歌淡然点头,看着她带着三个嬷嬷出了门,这才伸手招过云兰,“我娘呢?”往日一早就来了,何以今天日上三竿了还不见人?
“回主子,奴婢早就想说了,只是几个嬷嬷在这儿,一直没敢开口,夫人今儿一大早就赶回了别庄,听说是大夫人病了,想吃夫人亲手熬的桂花粥。”
“病了?”灵歌一挑眉,“什么病?”
云兰摇头,“这奴婢不清楚,当时也只听夫人说了那么一句,因为夫人走得急,奴婢也没来得及细问。”
灵歌闻言,默然垂下眸,须臾,方才抬眸看向前方,“出去吩咐一声,备车,我要去一趟别庄!”
“主子去别庄做什么?”
“自然是去探病了。”
“探病?主子,您是美人,她一介无品级的庸妇,怎么能劳您大驾?这于礼不合呀!”
“我要的就是于礼不合!”
灵歌执意要出门,连四个嬷嬷也拦不住,之后更是以“临别叙家常,不劳众人费心”为由,只许了云兰随行。曹嬷嬷这时才隐隐发觉,眼前这个小主子,似乎不一般。
别庄距离知府府并不远,连梳妆带赶路,也不过一刻钟的光景。
灵歌下了车,微仰着下巴扫了一圈地上跪着的一干人,才淡淡瞥向灵忠南,“爹,听说大娘病了?”
灵忠南一笑,“是病了,现下正在床上躺着呢!”
灵歌眉梢动了一下,语气冰冷,“哦?可是病得要死了?”
没想过灵歌会说出这番话,灵忠南明显一愣,半天才回过神来,“呃,不是,大夫说,只是小病,休养几日即可!”
灵歌这才淡淡一笑,转头看向云兰,“我就怕爹会怕我担心,不敢告诉我实情,咱们这趟算是来对了,亲自去探望一番,也省得别人说我失了孝道。”
云兰眼珠一转,当即蹙眉,“主子,您胡说什么呢!您可是美人,正六品的爵位,去探望大夫人已是纡尊降贵,若是大夫人真的病重也就罢了,如果真是小病,您又亲自探视,这若是传到皇上与皇后耳朵里,虽不至于罚,但也会怪您失了皇家贵仪的!”刻意压低了声音,却仍保证在场众人皆听得清楚。
灵忠南果然脸色一变,立马回头瞪了管事一眼,管事心领神会,一溜烟跑进了庄内,显然是请大夫人去了。灵歌心底一声冷笑,只听灵忠南道,“庸妇不懂礼数,是臣疏于管教,请元美人入内看茶!”言下之意,自是进了自家门,万事好商量。
灵歌怎会不懂亲爹的意思,知他是爱面子之人,当下也不再刁难,施施然进了庄。穿过前院,一路走向花厅,大夫人果然已在厅内等候了,低垂着头,瞧不见神情,不过想来也不会是高兴的样子。
“臣妇李氏给元美人请安!”
毕竟出身商贾之门,又久居官家,该有的仪态,李氏是不会失的。
灵歌微撇了一下嘴角,在她目光抬起之际,又陡然热络了起来,“大娘这是做什么?都是自家人,听说您又病着,快别这般多礼了!”说着话,又亲自上前扶起李氏,态度亲厚无比。
李氏眸中闪过一丝诧异,轻瞥了管事一眼,又微笑垂下了头。苏氏由花厅的侧门走出,看见灵歌,自是十分高兴,“你怎么来了?”
灵忠南见状,忙重咳了一声,吓了苏氏一跳,“老爷,您这是怎么了?”话落,触及他沉肃的目光,又骇得噤了声,忙低下头,瑟缩不语。
灵歌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唤过灵忠南,一同坐了首位。
侍婢们上了茶,又恭谨地退了下去,其中亦不乏灵歌昔日的玩伴,只是她们被灵忠南的礼教所束,始终连头也不曾抬一下,更别提打声招呼了。
灵歌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也只一瞬间,失望便也淡去。“大娘与娘也都坐吧,我后日一早也就走了,如今自家人叙旧,暂且忘了那些个宫规教条!”说罢,看了云兰一眼,云兰识相地退了下去。
堂上寂寂无声,灵歌淡扫了众人一眼,慢悠悠地端起茶碗,以盖轻拨开浮叶,方才浅啜了一口,笑道,“这该是大娘珍藏的铁观音吧?醇香浓郁,厚润甘滑,与我儿时偷喝的味道一样让人难忘!”
李氏顿时有些尴尬,偷瞄了灵忠南一眼,才笑了笑,“三个月前,臣妇的父亲过世,家中的茶叶生意也一落千丈,臣妇手中那些极品的铁观音早已被拿去应了急,如今美人喝的,可是老爷的珍藏!”
“哦?”灵歌微讶,转头看向灵忠南,“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家中有人亡故,怎么也不写信知会女儿一声?”
灵忠南忙颔首,“是爹疏忽了。”说完,又顿觉用“爹”这个字不妥,但想了想,终是忍了没改。
瞧着他脸色变了又变,灵歌心思一转,便也明白了一二,却也只当不知道,又笑看向李氏,“他老人家的后事可已安排妥了?”李氏应声,灵歌又道,“对了,回来这么久,怎么一直不见大哥与二哥的影子?”
李氏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可惜,皆不成器。
灵忠南笑了笑,不待李氏开口,已先一步抢了话,“你大哥一直在他外公家帮忙料理后事,正巧家中有个夫子,学问不错,爹就让他暂且留在那里一起学习,你二哥月前去了岳丈那里,带着你妹妹灵娇一起去的,她外婆家离那里不远,正好去探望一番。”
灵娇是三夫人所生之女,比灵歌小三岁,自幼与她亲厚。可惜三夫人生第二胎时难产而亡,一尸两命,灵忠南悲痛惊吓之余,自此便没有再娶,在这一点上,灵歌虽觉有些不厚道,但多少是有些感谢这位三夫人的。
灵歌点头以示了解,又一次端起了茶碗,“我记得再过几个月,就是科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