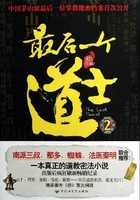第十三章男人的世界 (6)
正因为如此,她觉得自己不如维奥莱特?哈比。哈比小姐是个出色的教师。她能使课堂保持秩序并且效率极高地把知识给班上的学生灌下去。厄秀拉就是给自己鼓气说她比维奥莱特强千百倍也没用。她知道维奥莱特?哈比在她自己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而且是在一项对她来说几乎是个考验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功。她觉得有点儿什么一直在使她恼火,使她厌倦。开头这几个星期她想方设法地否认这一点,对自己说她还和过去一样自由自在。她试图不在哈比小姐面前感到自己不行,尽力保持她的优越感。可是有一副重担压在她肩上,维奥莱特?哈比受得了,她却受不了。虽然她没有放弃努力,可她从未获得成功。她的班级里的情况越来越糟,她知道自己越来越无法胜任这个班级的教学。她是否该退让或是又回到家里?她是否该说她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就退职了?她的生活道路此时面临着考验。她顽强地、盲目地继续干下去,等着出现转机。哈比先生现在开始来为难她了。她对哈比先生的仇恨增长了,越来越明朗化了。
她担心他要欺负她,整垮她,因为她无法使班上保持正常的秩序,因为她的班是学校这根链条上薄弱的一环。其中一件惹祸的起因是:当哈比先生在教堂另一头给七年级学生上课时,厄秀拉的班吵吵嚷嚷,惊动了他。一天上午,厄秀拉上写作课,和其他的老师一起走进教室。有些男同学的耳朵和脖子挺脏,衣服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些她可以视若无睹。她走进来就改正作文中的错误。她问:“如果你说‘它们的皮毛是棕色的,’‘它们的’怎么拼写?”有一阵没人说话。男生们总是故意不踊跃回答问题。他们已经开始全体来嘲弄她的权威。“小姐,是这样拼写,t-h-e-i-r,”一个男生带着嘲笑的调子大声地拼读。正在这时哈比先生走过来。他高声喊:“希尔,站起来!”人人都被吓了一跳。厄秀拉瞧瞧那个男生。一看就知道他家境贫穷,也很狡黠。一小绺头发直挺挺地竖在脑门上,剩下的头发紧紧贴在他的瘦脑袋上。他脸色苍白,没有血色。
哈比先生怒喝道:“谁叫你大声喊的?”这男生面有愧色地抬眼望望,垂下,狡猾地一声不出。“先生,我是在回答问题,”他答,同样是口气谦卑却不服气。“到我的办公桌来。”这男生朝着教室的另一头走去,一件宽大的黑色茄克打着褶颓丧地挂在他身上,两条细腿,膝盖严重地向外翻,迈着乞行的步子,穿着大靴子的脚几乎没抬起。厄秀拉看着他拖着两条弯腿朝教室的那一头挪去。他是她的班上的一个学生!他走到那张桌子边,偷偷地看了看周围,淘气地向七年级的男生们咧咧嘴,投去可怜巴巴的一瞥。他样子令人怜悯,脸色苍白,身着丧气的外衣,倚着威严的校长办公桌,一条细腿的膝部一弯,那只脚朝旁边拐着,双手插在那件成年人穿的茄克垂得低低的口袋里。厄秀拉想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到课堂上来。这孩子有点让她讨厌,同时她又因同情他而激动。她真想尖声喊叫。这学生受罚她有责任。哈比先生正在看着她写在黑板上的字。他转向班上的学生。“把笔放下。”
孩子们放下笔抬头望着。“两臂相交坐好。”他们把书本挪挪,手臂交叠在桌上。厄秀拉立在后排,没法摆脱窘境。校长问:“你们的作文写什么?”每个学生都举起了手。“写——”一声抢着回答的声音吞吞吐吐地刚说出一个字。哈比先生说:“我没叫你们乱喊。”要不是他的调子里常常带着可恶的威吓,他的嗓音应该很好,洪亮悦耳。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双眼在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看着班上的学生。他站在那儿有股慑人的魔力,厄秀拉又想尖叫了。她受了严重的刺激,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说:“好吧,艾丽斯说说。”
“兔子,”响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尖嗓子。“对于五年级的学生这是个非常容易的题目。”
厄秀拉有点感到无能的羞愧。她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亮相。她被所有这一切的相互矛盾折磨着。哈比先生那么强壮地站着,那么有男子气,眉毛浓黑,额头轮廓分明,脸庞线条粗犷,留着大胡子,好一个孔武有力、具有不修边幅的自然美的男子汉。把他看作一个男人,厄秀拉可能会喜欢他。而现在他以另一种身份站在这儿,为一个男生不经允许就说话这样一件小事恶狠狠地训人。他又不是那种琐屑卑微的人。看来,他的心残忍、固执、邪恶。他被一个任职禁锢住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太小太无足轻重了,可是出于一种奴性的默认,他得完成这个任务。他要挣钱过日子。他只有这种鲁莽、固执、一锅端的劲头,不能更好地约束自己。既然他要干工作,就不能让它停下来。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孩子们把“谨慎”二字写好,句号后另一个句子开头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带着被压抑的怨恨他埋头于工作,总是控制住自己,直到发狂。厄秀拉忍受着痛苦看着矮墩墩、英俊、强有力的哈比先生站在那儿,给她的班上课。做这件工作看来对他是件难受的事。
他有一个不俗、强健又直率的心灵。那他对写“兔子”的作文还计较些什么?可是他的意愿使得他站在这个班的学生面前,翻来覆去地拿这件小事做文章。这么琐碎、这么庸俗,这么过分,他现在已养成了习惯。她看到了哈比先生给这个职位抹的黑,感觉得到他受抑制的邪恶终究会燃起凶狠的怒火,他就像一个被缚的固执、强壮的尤物,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刚才的冲突对厄秀拉是个折磨。她看看安静、注意力集中的全班学生,他们像是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呆板的、没有特点的整体。是哈比先生用他的权力使这个班变成这样的,把孩子们变成一块块木讷不言的碎片,依他的意志将他们固定成形。就是他那残酷的意志,纯粹用威慑力压服人的意志。她也必须学着让学生们服从她的旨意了,她必须这么做。这学校既然就是这个样,那么这就是她的职责。哈比先生把班上整顿的秩序井然。但是,看到他这样一个强健有力的男人用尽全力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简直是令人厌恶。还有更可怕的:他那奇特、温和的目光实在是凶恶吓人,他的微笑使人感到痛苦。
他不可能超脱个人情感。他也不可能有一个纯洁单一的目的,只能是实现他的残酷意志。他并不相信自己年复一年地强加给孩子们的教育。所以他就要威吓人,甚至在这样做的同时,给他坚强健康的性情带来的羞辱像一块心病时常折磨着他,他还是只知道训人。他是那么地昏庸,乖戾,不相称。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厄秀拉不能忍受下去了。整个情形都是不正常的、丑恶的。下课了,哈比先生走了。她听得见从教室的那边尽头传来的嗖嗖的鞭打声。她的心一阵紧抽。她忍受不了这个,不,听着这孩子挨打她受不了。她讨厌这种事。她觉得必须离开这个学校,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而且,她恨透了这个校长。这个畜生,不知羞耻么?他这种残忍的威吓人的暴行理应受到制止。过了一会儿,希尔一边可怜地哭着,一边慢吞吞地挪着步子回来了。他的哭泣声带着凄凉,厄秀拉的心都要碎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她把班上的学生都管得规规矩矩的,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希尔就不会大声喊叫,不会挨打。她开始上算术课。可是她心神不定。希尔那孩子坐在最后一排,把身子缩成一团,一边哭一边吮吸着手。时间过得真慢。她不敢走近希尔,不敢跟他说话。她在希尔面前感到羞愧。而且她觉得,她不能原谅这孩子做出那缩成一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哭啼啼的样子。
她接着改正孩子们做的算术题。可是学生太多,她不能全班一一顾到。为希尔的事她心里感到内疚。他终于停止了哭泣,双手垫着伏在桌上,不声不响地玩。然后他抬头望望厄秀拉。他的脸被泪水弄脏了,眼里有一种奇怪的湿润的神色,仿佛大雨过后的天空,暗淡倦然。他不带一点怨恨。他已经忘了刚才的事,正等着让他回复正常的位置。她说:“希尔,继续做作业。”孩子们边做算术题边玩,而且她知道,完全是在消磨时间。她在黑板上写下另一道题。她不可能全班一一顾到。她又走到前排去看。有一些学生已经做好了,有一些还没做好。她该怎么办?终于到了娱乐时间。
她命令停止做作业,凑合着把班上的学生弄出教室。然后,她面对着那些乱七八糟到处扔着的、墨渍污涂还没改的本子,折了的尺子和牙咬过的笔,心里懊丧极了。愈发觉得痛苦难熬。烦恼一日又一日地生出,没完没了。她总有一堆堆本子要改,有数不清的错误要纠正,她厌恶这种劳神费心的事。作业越来越糟。只要她自以为学生们的作文越来越活泼有趣,就不得不看到他们的字写得越来越马虎,本子越来越邋遢。她已经尽力而为,可是不起作用。然而,她不准备把这看得很严重。她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她为什么要对自己说,她无法教这个班的学生写得干净整齐,这就关系重大?为什么她就该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发薪日到了。她得了四英磅两先令一便士。
这一天她非常自豪。她从来没有得过这么多钱。而且这是她自己挣来的。她坐在有轨电车的顶层,用手指抚弄着金币,真怕她会弄丢。因为有了钱,她觉得心里踏实牢靠了。她到了家就对妈妈说:“妈妈,今天是发薪日。”“哎。”她妈妈冷冷地应了一声。然后厄秀拉把五十先令放在桌上。她说:“这是我的伙食费。”“哎,”妈妈又应了一声,随意它放在桌上。厄秀拉的感情受了伤害。然而,她付了自己的那份开销。她轻松了。她付了自己的吃用。另外,她自己还剩下三十二先令。她一个先令也不愿意花,因为她不忍心失去精致的金币,而她的手不紧,一花就花光了。
现在她有一个不依靠她父母的立足点了。她再也不仅仅是威廉?布朗温和安娜?布朗温的女儿了。她是自立的。她自己养活自己。她是劳动大军中重要的一员。她敢肯定,一个月五十先令足够她的食用了。如果她妈妈一个月从每个孩子那儿都得到五十先令,那她一个月就能有二十英磅,还不用管做衣服,那就很好了。厄秀拉是不依赖父母的。她现在在另外一个圈子里。“教育部”,现在她听起来意义非同一般。离她非常遥远的白厅,她觉得是她最后的归宿。她知道政府部门里哪一位部长掌管教育大权。而且,在她看来,这位部长在某些方面与她是有关联的,就像她父亲与她有关联一样。
她还有另一个自我,另一种责任。她再也不是威廉?布朗温的女儿厄秀拉?布朗温了。她是圣菲利浦学校五年级的老师。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她就是五年级的老师,别的什么也不是。她无法逃脱这个职责。她也干不好这个工作。这是她最害怕的事。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再也没有一个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厄秀拉?布朗温了。只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姑娘,她为管不住班上的孩子们这个事实而烦恼。到了周末,就到了她感情激动的日子。她欣喜若狂地享受这点空闲,这种享受只不过就是早上没事,坐下来绣绣花——把彩色的丝线一针针地绣下去是她喜爱做的事。
那间囚室时时在等待着她!她那颗被禁锢的心很明白,这只是个小憩。所以她不放过周末飞逝的时光,就是还有最后一滴甜蜜也要带着点残忍的急切把它挤出来。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种状况对她的折磨。她觉得当个小学老师是多么可怕,对戈珍或父母亲她都没有吐露这个想法。可是一到星期天晚上,她就觉得星期一上午马上就要到了,她被这种恐怖的预感弄得精神紧张,因为劳累和折磨又近在眼前了。她相信她永远也教不了这么粗野、这么大的一个班,又是在这么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学校里,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可是,如果她教不了,她就要一败涂地。她就得承认男人的世界对她来说太强大了,她没法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她就要在哈比先生面前败下阵来。
那么从此以后她的一生,还会像过去那样,永远摆脱不了男人的世界,永远得不到进入这个重要世界担负要职的权利。玛琪在那儿已经占有了自己的地位,她甚至和哈比先生平起平坐,摆脱了他;她的心灵时常遨游在富有诗意的遥远的峡谷和林间空地。玛琪是自由的。然而,就是在玛琪的自由之中还有着某种服从。哈比先生,作为男人,他不喜欢玛琪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作为校长,他敬重斯科菲尔德小姐,他手下的老师。不管怎么说,目前厄秀拉只羡慕和钦佩玛琪。她自己还得争取玛琪已经得到的地位。她还要站住脚。她已经在哈比先生的领地得到了一个职位,必须保住。现在哈比先生开始对她进行经常性的攻击,要把她赶出他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