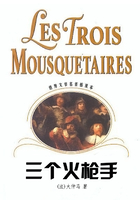第十一章初恋 (4)
在工房里,他们做亲吻游戏,真的是玩一玩。这是个有趣的、激动人心的游戏。厄秀拉满脸笑容,转向他,像是在挑战。他马上接受了这个挑战。他一只手缠满了厄秀拉的头发,然后轻轻地,用绕着头发的手托着她的头,慢慢在送到自己面前。厄秀拉笑得喘不过气来,他两眼放光,望着厄秀拉,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他吻了厄秀拉,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愿,厄秀拉也回吻了他,表明了对他特别的喜爱。他们知道这个大胆的游戏是不顾后果的、危险的,两人都不是出于爱,而是由于火热的激情。在这场游戏中,占据厄秀拉心头的是藐视一切,只要她想吻斯克里宾斯基就吻。而斯克里宾斯基呢,心里的念头是大胆妄为,好像玩世不恭,与他假装恭顺相待的一切一刀两断,来一次报复。这时,她非常美丽,敞开了心胸,容光焕发,心儿突突直跳,极度脆弱。这又引起了斯克里宾斯基的狂热。
犹如阳光下怒放的一朵花儿在摇曳,厄秀拉引诱他,向他挑战。他接受了挑战,暗自做出了某个决定。在她的笑意和强烈的忘情举动后面是颤动着的泪滴。看到此情此景,斯克里宾斯基欲火中烧,几乎要发狂,受不了了。欲念只有一个,就是要占有她的肉体。
他们俩又回到厨房,回到厄秀拉父母的身边,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他们俩都多了件心事,一下还不可能摆脱。这件事加强了他们的感觉。他们更加朝气蓬勃,更有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倏忽即逝的感觉。从他们双方看来,这是一个绝妙的自我突出的时机:他在厄秀拉面前表现了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男子汉,完全不可抗拒;厄秀拉也在他面前表现了自己,知道了自己有无穷的魅力,因而,也是无比地强壮。除了各自最大限度地证实了自我,从这样的情感中,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第二天下午,他悄然到来,厄秀拉和他一起到教堂去了。
厄秀拉和斯克里宾斯基一起穿过教堂的院子,跑进教堂躲起来。里面比起照耀着午后阳光的外面要暗一些,可是那些弓形石块间的柔和光线非常美妙。窗玻璃燃烧着红宝石色和蓝色,给这神秘的石头砌成的精致房子挂上了一块华丽的花毯。“真是个约会的好地方,”他悄声说道,一边四下打量。厄秀拉也在到处打量着这熟悉的教堂内部。暗淡的光线和寂静使她觉得凉飕飕的。不过她一点儿也不怕,双眼闪闪发亮。在这里,就在这里,她将要表现她那不屈不挠的灿烂的女性自我。在这里,她那女性的花朵将像一团火焰一样怒放。在这昏暗的地方,这朵花比光线更为热烈。他们站了一会儿,然后,都转向对方,渴望身体的接触。厄秀拉双臂环抱着他,把身体紧贴在他身上,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背上。厄秀拉似乎摸透了他,完全懂得了他这年轻的紧绷绷的身体。
如此美好,如此坚实的躯体,又是那么微妙地受她支配,在她的控制之下。她的嘴朝斯克里宾斯基的靠拢,大口吸吮着他的深吻,深深地吸了又吸。这滋味真好,好极了。她感到好像全身充满了斯克里宾斯基的吻,大口大口地吞下了强烈灼人的阳光。她的胸腔发热了,阳光好像直射在心上。她吸进去的东西美极了。厄秀拉放开他,容光焕发地望着他,心满意足,那副神采飞扬的模样宛如美丽的云霞。她那么容光焕发,那么满意,斯克里宾斯基看了泛起苦味。她朝着斯克里宾斯基笑,不管他怎么样,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以为他也同样高兴,根本就没怀疑这一点。
她光采照人,犹如一位天使,和斯克里宾斯基一起走出教堂。她的双脚似两道光,行走在花间。他走到厄秀拉旁边。精神上感到压抑,肉体上不满足。厄秀拉是否就要这样轻而易举地战胜他?对他来说,只有痛苦和莫名的愤怒,没有自己的欢乐。时值盛夏,干草的收获已近尾声,星期六就能结束了。斯克里宾斯基星期六无论如何都得走了。他不能再住下去了。决定了要走,斯克里宾斯基对她就非常温柔非常亲热,轻轻地吻着她。他们俩都为这温和、甜蜜、不知不觉的亲近而陶醉。在他逗留的最后的那个星期五,他去等着厄秀拉放学,带她在城里吃茶点。然后,他开汽车带她回家。
厄秀拉坐在车上,兴奋到了极点。斯克里宾斯基也非常得意最后露的这一手。他看着厄秀拉为这浪漫的情景激动,欢闹。她把头昂起来,像匹小马在撒欢,在使劲吸气。车在一个拐角急转弯。厄秀拉身子一晃,靠在斯克里宾斯基的身上。身体的触碰使她意识到斯克里宾斯基的存在。一阵突来的冲动,厄秀拉摸到了他的手,把它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像两个孩子,手握得那么紧。风儿吹拂在厄秀拉的脸上。车轮下扬起的尘土在狂翻。乡间一片墨绿色。新割下的干草这儿一堆那儿一垛,泛着银光。银白的天空下有一片片的树林。
厄秀拉的手有意识地又握紧了他的手,感到了不安。他们好一阵子都没说话,坐在车上,紧紧地握着手,兴奋得发亮的脸儿都避开不望对方。随着车子的摆晃,厄秀拉不时地靠着他。他们都在等车子颠簸把他们俩晃到一起。可是,他们都一声不响地盯着车窗前方。她看到熟悉的田野掠过车窗。现在到不熟悉的地方了,那是一片奇境。耸立在杂草丛生的小山坡上的石块叫汉洛克石。在这潮湿的夏季傍晚,它看上去很古怪,模模糊糊地竖在一片魔幻的土地上。
树林里飞出几只白嘴鸦。啊,如果她和斯克里宾斯基能够下车,走进这片从来没人到过的神奇土地该有多好!那么,他们就会心醉神迷,摆脱沉闷、守规矩的自我。要是她能在这儿漫步多好啊!不断变幻的银白色天空下,有一个小山坡,许许多多的白嘴鸦在天空中化作了急匆匆的黑点。要是他们能够走过那割完草的潮湿土地多好!呼吸着傍晚的空气,走进林子里,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金银花的香气,一碰着树枝,水滴就掉下来,掉到脸上真是冰凉惬意!她却和他坐在车里,紧挨着。风儿撞在她昂起的,热切的脸上,把头发吹得往后飘。斯克里宾斯基掉过头来看她,看到她的脸儿洁净得如同一尊雕塑,风儿把她的头发吹到了后边,她小巧的鼻子尖尖地翘着。看到她敏捷、轮廓分明又纯洁,斯克里宾斯基感到痛苦,真想杀了自己,把那讨厌的尸首扔在她的脚下。想把自己改换一新的欲望在折磨着他。
突然,厄秀拉看了他一眼。斯克里宾斯基似乎拜倒在她的脚下,向她靠拢,似乎要在她双目注视下退缩了。
但是,一看到厄秀拉那双闪亮的眼睛和容光焕发的脸,他的表情马上变了,对她露出了漫不经心的笑容。厄秀拉欣喜地按紧了他的手,他忍着没动。突然厄秀拉低下头,十分崇敬地把那只手送到嘴边。吻了吻。斯克里宾斯基热血沸腾。但他还保持镇静,一动不动。她吃了一惊:他们已经摇摇晃晃地进入了考塞西。斯克里宾斯基就要离开她了。然而,这一切是那么神奇,她的杯子里已经装满了明亮的酒液,她的眼睛只能是闪闪发亮的了。斯克里宾斯基和家里的男人打了招呼。车子贴着紫杉树拐了过去。厄秀拉把手伸给他,像一个女中学生那样天真地道了声再见。她站在门口看着斯克里宾斯基走了。
他开着车越走越远这个事实与她无关,她的全副身心已被欢乐喜悦占据了。她没有看见斯克里宾斯基走,因为他的光辉已经照在她身上。像她那样兴高采烈地沐浴着一束奇异之光,怎么可能想念斯克里宾斯基呢?在卧室里,她伸出双臂,明显地感觉到了极为撩人的痛苦,哦,她脱胎换骨了,超越了自己。她想纵身扑向空中一切隐藏着的光明。在那儿,就在那儿,要是她能遇见就好了。到了第二天,厄秀拉知道他已经走了。她的荣耀消失了一半,但永远不会从她的记忆中抹去。这值得炫耀的事来得太真切了。可是这一切已经过去,留下的是惆怅的怀念。深深的思念之情在她心中油然而升,她有了一个新的秘密。她回避别人的接触和探问。
她为此感到很骄傲,可是她太不老练,太敏感了。哦,谁也别来招惹她!她更喜欢自己一个人来来去去。沿着小巷走下去,什么也看不见,但又和这些事物在一起,可真是有趣。放假了,她自由了。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独往独来:蜷着身子缩在花园里松鼠才去的地方;在小树林里拴个吊床躺着,鸟儿飞得很近,很近,飞得近极了。再就是,阴雨天,她到玛斯庄去,在堆干草的顶棚里埋头读自己的书。这一段时间,她一直在想念着斯克里宾斯基,斯克里宾斯基给她的梦境涂上了一层暖色调,是使她的梦想炽烈的热血。当她不舒服的时候,她就在反复回想着斯克里宾斯基的外表、衣服、有军队标志的扣子——他给过厄秀拉那种标志。要不,她就是在想象着斯克里宾斯基在军营里的生活,或者想象她在斯克里宾斯基眼里的形象。斯克里宾斯基的生日在八月。她为他做了一个蛋糕。她觉得,要是送给斯克里宾斯基一件礼物,显得不大合适。
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很简短,差不多就是互寄明信片,而且还不频繁。但是,送蛋糕她要附上一封信。
亲爱的安东:我想,在你的生日来临之际,阳光特意为你而照耀。
蛋糕是我自己做的,祝你生日愉快。如果蛋糕变质了,就别吃了。妈妈希望你在离得近的时候来看看我们。你诚挚的朋友:厄秀拉?布朗温
她厌烦写信,即使是写给斯克里宾斯基也一样。天气晴朗了,收割机哒哒哒地在田里开来开去。厄秀拉收到了斯克里宾斯基的信。他在乡间执行任务,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他现在是野战骑兵队的少尉。很快他就有几天假,要到玛斯庄来参加婚礼。谷物收割很快就要结束了,弗莱德?布朗温将要娶一位在伊开斯顿以外的小学教员。芳香炎热的秋天一片淡蓝色,一片金黄色,收割结束了。在厄秀拉看来,世界盛开着最柔和最纯洁的花朵,开着菊苣花,番红花。天空碧蓝,小路上的黄叶子看上去像是自由漫步的花朵,在脚下沙沙作响,奏起刺耳的尖声,令厄秀拉无法忍受。而且,秋天的气息对她就像夏天的狂热。她像个受惊吓的林中仙子从一簇紫红色小菊花旁跑开。另一种鲜黄的小菊花散发的味儿那么浓,熏得她脚步晃晃悠悠的似喝醉了酒。
前面走来了她舅舅汤姆,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将要把快活的婚礼、丰收的晚餐和婚宴合而为一:在自己家附近搭个帐篷,请个乐队来伴奏跳舞,露天办一次盛宴。弗莱德犹豫不决,但汤姆肯定会感到满意的。而且劳拉,那位新娘,一个端庄聪明的姑娘,她肯定也要举办一个盛大欢乐的宴会。这与她受过教育的观念很合拍。她曾就读于索尔兹伯里师范学院,会唱民歌,会跳莫利斯舞。准备工作开始了,由汤姆?布朗温来指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搭了个大帐篷,准备了两大堆营火。请来了乐师。宴会准备停当了。斯克里宾斯基要来,在宴会的当天上午到。厄秀拉穿一条柔软的绉纱白裙,戴顶白帽子。她喜欢穿白色。配上她的黑头发和金色的皮肤,她看上去带点儿南方或者不如说是热带情调,像个克里奥耳人。她的穿着不带一点儿彩色。那天准备参加婚礼的时候她总是颤抖,她要去当女傧相。斯克里宾斯基要下午才能到。婚礼两点钟开始。参加婚礼的人们回到家时,斯克里宾斯基正站在玛斯庄的客厅里。从窗口望出去,他一眼就看见了汤姆?布朗温。他是男傧相,穿着燕尾服,白色的内衣和鞋罩,沿着花园小路风度优雅地走过来,满面笑容的厄秀拉勾着他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