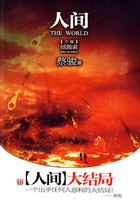第十一章初恋 (3)
然后,他们走到旋转木马那边休息。他两腿分开,骑上一匹面朝着厄秀拉的木马。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悠闲自在,自得其乐。他们坐在旋转着的木马上,耳边响着手摇风琴奏的乐曲。厄秀拉感觉得到站在外面的人群,就好像他们俩骑在木马上漫不经心地从人们的眼前闪过,总是那么轻快活泼,那么得意,那么风流地在人们仰着的脸庞面前闪过,一下又升得高高的,不把那些普通人放在眼里了。他们该下来了,不得不离开。她一下变得不高兴了,觉得如同一个巨人突然被削降到一般的高度,由那一群下民摆布。他们离开庙会,朝他们的马车停放处走去。走过那座大教堂,厄秀拉总要朝里边望望。可是,现在那里面搭满了脚手架,地板上到处都是石头和杂物,走在上面,脚下嘎吱嘎吱地踩着小块的灰浆。整个教堂回荡着世俗的声音和锤子的敲打声。厄秀拉有一阵子陷入了忧郁的状态,渴望能安静一下。刚才在庙会那边不顾一切地在众人面前骑完木马后她就想静下来。得意之后,她想得到安慰,得到平静,因为傲慢和藐视破坏了她心头的宁静。她发现在这悠久郁闷的教堂中充满了点点坠落的灰浆,悬浮在空气中的灰尘,带着一股陈旧的石灰味,还有脚手架和一堆堆的垃圾,圣坛上扔着抹布。她说:“我们坐一会儿吧。”
他们在阴暗的最后一排长凳坐了下来。一个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嘎嘎地走过通道,带着粗俗的口音大声喊:“嗨,伙计,他们的角模板拿来了没有?”教堂的屋顶上传来了粗鲁的大叫声作答。空荡荡的教堂里响起了回声。斯克里宾斯基紧挨着她坐下。在厄秀拉看来,一切都好极了,世界坍塌成一片废墟,他们俩安然无恙地爬出来,可以无法无天了。也许她心里还有点害怕。斯克里宾斯基紧挨着她,触到了她。厄秀拉感觉得到他对自己的影响,很高兴。这促使她去感受斯克里宾斯基对她的紧逼,似乎他的存在就促使自己去干点什么。他们乘马车回家的路上,斯克里宾斯基坐在她旁边。随着车子的摇摆,他情欲荡漾地朝着她摆过去,靠着她,直到为了保持平衡不得不摆开身子。他从盖毯下面把厄秀拉的手拉过来。
虽然他的脸抬起来望着路,并不看手,却用一只手解开她手套上的扣子,把手套拉开,小心地把她的手裸露出来。他在厄秀拉手上的细腻触摸,把这年轻的姑娘弄得神魂颠倒,情窦大开。他的手是那么奇妙、专注,就像一个活灵灵的尤物,在黑暗的底层灵巧地操作,把她的手套解开除掉,露出了手掌,又露出了手指。然后,他把手合在厄秀拉的手上,合得那么紧,似乎两人手上的血肉已经交融,合而为一了。同时,他脸朝着道路望,留心听着马的步子,稳稳当当地赶着马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厄秀拉就坐在他旁边,欣喜若狂,被这一道新的光芒照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俩都没说话。从外表看,他们的注意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他们俩中间,通过紧紧握着的手,两个人的肉体坚实地连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他对厄秀拉说:
“坐在教堂里时我想起了英格拉姆。”她问:“谁是英格拉姆?”
她知道某种受禁的事就要发生了。“他是和我一起在查塔姆的,一个中尉,比我大一岁。”“那教堂怎么会使你想起他呢?”“噢,他在罗切斯特有个情人,他们总是在那个大教堂的一个特定的角落谈情说爱。”她冲动地喊了一声:“多好啊!”他们俩互相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这也有不好。守教堂的人为这大吵大嚷了一顿。”
“太不像话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坐在教堂里?”“我想大概他们都认为这是亵渎神灵。只有你、英格拉姆和那位姑娘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这是亵渎,我认为这是对的,在教堂里谈情说爱是对的。”她几乎是用挑衅的口气说这些话,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斯克里宾斯基没有说话。“她好吗?”“谁?爱米丽?是的,她挺好的。她是个卖女帽的头饰的。她不能在街上让人看见和英格拉姆在一起。这可是糟糕透了,真的。因为那看教堂的暗中监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就经常吵吵嚷嚷的。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她怎么办呢?”“她去了伦敦,进了一家大商店,英格拉姆还去看她。”“英格拉姆爱她吗?”“他和那姑娘好,到现在已有一年半了。”“她长什么样?”“爱米丽吗?一个小巧娇羞的姑娘,眉毛长得挺美的。”厄秀拉沉思着。这似乎就是外部世界的一桩真实的风流韵事。
“所有的男人都有情人吗?”她脱口问出,暗自惊诧自己的鲁莽。可是她的手还是被斯克里宾斯基的手紧紧握着;斯克里宾斯基的脸也还是原来的样子,表面上挺镇定的。“他们经常谈到这个或那个令人惊异的漂亮女人,喝得醉醺醺地谈论她们。一放假,大多数人都急急忙忙地跑到伦敦去。”“去干什么?”“去找这个或那个令人惊异的漂亮女人。”“什么类型的女人?”“各种各样的都有。一般来说,她的名字经常变换。他们之中的一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狂热分子。他身边总是准备好一个小提箱,一有空,就带着提箱急急奔到车站,到火车上更换衣服。不管车厢里有什么人,他一下就脱掉短上衣,至少是把上半身的衣服换好。”厄秀拉一阵颤抖,又感到奇怪。她问:“为什么他这么着急呀?”她的喉咙发硬,很难发出声音。“我猜他是心里惦着个女人。”她心里一凉,又麻木了。
然而,这个情感的世界和不受约束的行为使她着迷。这不顾一切的行为在她看来好极了。这一天她在玛斯庄待到天黑以后,斯克里宾斯基送她回家。她不愿离开斯克里宾斯基。她在等待,等待着再发生些什么事。天刚黑,还挺暖和的。他们俩的影子在脚下。厄秀拉感觉到是在另一个更坚实更美好而又较少涉及个人的世界。现在,一个新的国度要产生了。斯克里宾斯基走近她,热切地用胳膊揽着她的腰,非常温柔地把她拉近自己,直到把胳膊按在她的身上。厄秀拉好像被带着走,漂浮着,双脚几乎不着地,倚靠在他那坚实的、移动着的身体上,似乎要在醉人的晕眩中移动,倒向那身体的一侧。正当她处于晕眩状态中,斯克里宾斯基俯身把脸对着她,她就势把头靠在了斯克里宾斯基的肩膀上。厄秀拉的脸感觉得到他呼出的温暖气息。然后,斯克里宾斯基的嘴唇轻柔地碰了碰她的脸颊。哦,轻柔的吻,那么轻柔,她好像要晕过去了。
她还在等待着,在她的晕眩和漂移的状态中等待,宛如故事里的睡美人。她在等待,斯克里宾斯基的脸又俯向了她的脸,温暖的嘴唇贴到了她的脸上。他们的脚步停住了,站在树下。他的嘴唇贴在厄秀拉的脸上,像一只蝴蝶停在花儿上一动不动。厄秀拉的胸脯朝他挨得更近一点,他动了一下,两条胳膊将厄秀拉环抱着,紧紧地抱着。在黑暗中,斯克里宾斯基俯向她,用自己的嘴轻轻地触她的嘴。厄秀拉还在他的怀抱里,感到害怕,感觉得到斯克里宾斯基的嘴唇在自己的唇上。她不动,没办法动。斯克里宾斯基的嘴贴近,把她的嘴压开。
她的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把嘴唇张开,在强烈的情感涡流中,她把斯克里宾斯基抱得更紧,让他再吻。他的双唇又贴上来了,一阵又一阵的热吻,多么温柔啊,然而,又像水中的巨浪不可抗拒。直到随着一声低低的呻吟,她才挣脱。厄秀拉听见他在身边喘着粗气,没见过他这样。由他这不正常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种可怕而又绝妙的感觉占据了厄秀拉的心。但是,她退缩了一小步,把情感藏在心里。犹豫了一下,他们又往前走,像是榛树下的两个影子在颤抖。在这个山坡上,她的外祖父曾拿着黄水仙向她的外祖母求婚;她母亲也曾和年轻的丈夫在这里漫步,紧紧地靠在丈夫的身上,和厄秀拉现在靠在斯克里宾斯基身上一样。
厄秀拉感觉得到黑黝黝的大树枝披着树叶在头顶上伸展。细碎的树叶装点着夏夜。他们走着,两人的身体紧挨着,结为一个整体。斯克里宾斯基抓住厄秀拉的手,沿着那条长长的路向前走。厄秀拉觉得她不是靠两条腿支撑的,腿轻飘飘的似一阵微风在摆动。斯克里宾斯基还会吻她的,但不是在今天晚上再来那么一次深深的吻。她现在知道了,知道吻是什么滋味的了。所以,斯克里宾斯基就更不容易再进入这种状态。她睡觉时浑身热乎乎的。好像拂晓前喷薄而出的光亮积蕴在胸中,涌动着。她睡得又沉又香,哦,睡得香极了。早上醒来,她感觉良好,像一穗麦子,芬芳,结实,饱满。在这头一次遇到的奇妙但不可能实现的世界里,他们继续相爱着。厄秀拉对谁也没有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了。
在学校她有一位生性严肃的朋友叫埃塞尔。厄秀拉肯定要向她吐露这段心事。厄秀拉在诉说这个秘密时,埃塞尔低着头,注意地听着,愿为她保守秘密。啊,他谈情说爱时那温柔体贴的方式是多么令人迷恋!厄秀拉像个情场老手似地说着。厄秀拉问:“你觉得,让一个男人吻你是不是太不正派了?我指的是真心的吻,不是调情。”埃塞尔说:“我想,这得看情况。”“在考塞西山坡上的榛树下,他吻了我。你觉得这事对还是不对?”“什么时候?”“星期四晚上,他送我回家的时候。不过这可是真心的吻,真的……他是个军官。”埃塞尔故意问:“那是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大概是九点半。”有几分钟谁也不说话。“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埃塞尔不耐烦地抬起头来说,“你并不了解他。”她的话里带着轻蔑。“了解,我了解他。他的血统有一半是波兰人,还是个男爵。在英国,他相当于贵族。我的外祖母是他父亲的朋友。”
可是,两个朋友从此成了仇人。似乎厄秀拉一表明她和安东的关系——她现在对他是直呼名字了——就是想和自己的熟人绝交。斯克里宾斯基到考塞西去得很勤,因为厄秀拉的母亲喜欢他。安娜?布朗温和他在一起就像个贵妇人似的,心平气和,什么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厄秀拉和那位小伙子一进门,就没好气地大声问:“小家伙们还没睡?”她妈妈说:“他们过半小时就睡。”厄秀拉嚷嚷道:“那就没个安宁。”她妈妈说:“厄秀拉,孩子们也要过日子呀。”斯克里宾斯基也反对厄秀拉这样做。她为什么要这么过分?那时,正如厄秀拉所知,他身上并没有小孩子那种没完没了的霸道。他对厄秀拉的母亲彬彬有礼,布朗温太太对此报以宽容、友好的招待。母亲装出来的宁静样子也使厄秀拉高兴。看来,布朗温太太的地位是无法降低的。布朗温和斯克里宾斯基两人之间保持着沉默。有时,两个男人交谈几句,但没有交流。看到她爸爸自己退避,不理这年轻人,厄秀拉很高兴。在这个家里,她很为斯克里宾斯基感到骄傲。厄秀拉恼火他那一副无精打采的懒散样子。可是这一点又使她着迷。她知道,这是放任自由的精神和勃勃的青春活力合为一体的结果。
然而,这一点还是使她非常恼火。尽管如此,斯克里宾斯基在她家以巧妙的方式闲混日子,她却为他感到得意。斯克里宾斯基对她母亲和她都是那么彬彬有礼,殷勤周到。有他在这个屋子里多好。一想到这里,厄秀拉就感到充实了。似乎她自己是个确定的吸引力,而斯克里宾斯基是朝着她而来的流动体。他的礼貌、随和也许都是冲着她妈妈来的,可那飘忽不定的身体却是她的,她抓住了。她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的魅力。她说:“我想给你看看我的小木雕。”她爸爸说:“我敢肯定,这可不值得看。”“你想看看吗?”她一边问,身子就朝着门边倾斜。斯克里宾斯基已经从椅子上站起了身子,虽然面子上还想顺着她父母的意思办。她说:“在这间工房里。”不管感觉怎么样,他还是跟着厄秀拉走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