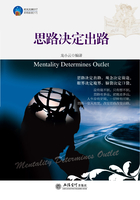陈寅恪(1890~1969年)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建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等。
陈寅恪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有中国最佳“读书种子”之称。20年代时,他的朋友,留美博士吴宓说,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能熟练运用世界十几种文字,其中有几种已失传。他读书多,许多书不但谙熟章节,甚至还能背诵。如四部典籍,随你翻哪一本书,读哪一段文字,他都能正确说出在哪一卷甚至见自第几页上。据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见面谈话后也称他“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就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
“欲纵观所未见之书”
陈寅恪生于书香门第,家中丰富的藏书,吸引着他从小就读了一本又一本,他几乎看遍了家中所有的藏书,养成了空下来就想读书的习惯。常发誓:“欲纵观所未见之书”。
晚清以来,国家多难,内忧外患,激起了陈寅恪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十二三岁时就跟着大哥,踏上了出国留学征途。从日本到西欧,陈寅恪越学越坚定了自己“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想法。认为:振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蕴育出的文化精萃,才是民族挺立之根本。十六年中,他留学国外,曾在许多大学读书。每当读完了所需的几门课程,他就转校。结果虽然满腹经纶,却因没有自始至终读完学校的全部课程而不能获得毕业文凭。为此在20年代初,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请导师时,梁启超郑重其事推荐他,但北京政府教育部却以陈寅恪没有大学毕业为由拒绝聘请,若不是梁启超一再坚持,并声称自己虽著作等身,却不及陈先生几百字论文等,陈寅恪真还差点进不了清华园。
留学期间,陈寅恪很用心读书。在德国时,有一时期官费停止,断绝了经济来源,但他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只买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在图书馆度过一天。为了读书,还得把钱节省下来买书。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重要看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几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国外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异之矣。”他真是千方百计读书。
陈寅恪读书还善于运用西方比较语言的方法。1918年,他已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古文学和佛经,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此期间,他又掌握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用一种文字的佛经与另一种不同文字译本的同一佛经相比较,从中掌握语言规律及变化。通过这种方法,陈寅恪通晓了多种古代语言并熟习佛教内典,达到熟能生巧,巧能生华,这使他后来能广泛利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资料来佐证历史,且运用自如,其所论精辟,为他人所不能及。
从常见书中发现不常见问题
陈寅恪读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从一般人都能找到的常见书中,发现问题,提出和解决新问题。
1932年,他的学生蒋天枢在听陈寅恪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课时,所记的课堂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这段话,可以说是陈寅恪读书方法的总结。
1928年冬,陈寅恪在北海图书馆看书,看到满文版《几何原本》七卷。为弄清满文版《几何原本》的来龙去脉,他对照了利玛窦、徐光启在万历年问合译的《几何原本》,发现版本不同。又同清人梅彀成主编的数学丛书《数理精蕴》中十二卷本《几何原本》核对,感到二者也不相符。他又转向考证《数理精蕴》,说“尝读数理精蕴本,怪其与利徐共译本体裁绝异。仅就利徐共译本删节者,皆不相类,颇致疑于清圣祖及诸臣删改之说”。他根据早年留学欧洲时所作的德文本、英文本《几何原本》笔记,如海外图书馆夏乌氏(sommervoyel)耶稣教会著述目录中满文几何原本,及法兰西人支那学书目,认定满文本与《数理精蕴》同出自耶稣教会另一教士版本,比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简略得多。对此,他深表疑问,说:“寅恪因之疑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间接直接出于浩氏相类似之本,而数理精蕴本恐非仅就利徐共译本所能删改而成者。”读书要在不疑和可疑处获得新知,这就是陈寅恪读书不断进步的一个原因。
天头地脚批注得水泄不通
陈寅恪熟读群书,还有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即用批语和评点。
陈寅恪从德国留学回来,除带回他的书以外,还有一部分是他经过筛选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分门别类,现存有藏学、蒙文、法华经、梵文等六十四本。这是他留学十六年的部分读书笔记。
他读书时采用密点、圈点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可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其内容和文字的丰富,为通常学者所不识。通常他还喜欢将几种基本的书,以平日阅览时意见,或发现其中有新的问题时,写在每页的书头。
八九十年代,陈寅恪写在书籍天头地脚的眉批已被陆续整理发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王邦维在《中国文化》第二期上公布的《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卷二上发表的陈寅恪《读(弘明集)(广弘明集)札记》;《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包敬第整理的《陈寅恪遗作(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等。人们于此当可一窥史界一代宗师读书的辛勤。
读书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陈寅恪说,读书要先识字,懂得多种语言。他自己就能运用十几种文字和语言。
1923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曾写信给国内的妹妹,请她代购《大藏经》。他说:“西藏的藏经,多龙树、马鸣译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源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文字。从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两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书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只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校勘一遍,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下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国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逐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见后恐益难得矣。”此信关于为什么要学语言,学语言与研究学问有何关系,及怎样读书做学问,谈得再明白不过了。
陈寅恪因为读书广博,善于选择增进自己学问的书籍。20年代初期他在柏林时,有一天,同学毛子水上他那儿,发现他正伏案读kaluza的古英语文法。毛认为当时在德国已有较好的同类书,便问为何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陈寅恪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毛过后一想,认为陈不是戏言。因为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也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都有可以启人深思处。
陈寅恪驾驭语言的能力已达信手捻来、出手成章的程度。回国后,他仍继续学外语。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每逢星期六上午,他坚持去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一直坚持到钢和泰回国。他学语言,并非为了多掌握一个语种而已,而是为学术研究。例如学梵文,就是为了研究佛经。他曾多次与钢和泰比较、分析各种语文版本的《金刚经》。他学习满文、蒙文、藏文,也是为了研究佛教经典。
史中求识
中国诗词文字,无不留有历史痕迹,陈寅恪善于以诗证史,他的读书已达到一切遗存皆史料的最高境界了。
1944年,在四川成都,有人发现一方唐砖刻有跳丸,围观的人数后说有六丸。陈寅恪根据白居易诗“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中所描写的唐时百戏,认为这是胡伎,应该有七丸。观者再详细数,果真是七丸。当人们刚刚体会到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重要意义时,陈寅恪又出口说道:“日本正仓院考古记图版陆南棚漆弹弓背,亦绘跳丸之伎,所印图版,史见六丸,惟左手指尖黑暗不明,未审其上别有一丸否待考”。陈寅恪历史知识如此渊博,胪列史料如数家珠,令闻者惊叹不已。
从来历史学家、大学问家都十分重视史料,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在分析史料中发现真理,探索规律的。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香港学者许冠三,曾对陈寅恪作的《柳如是别传》中引用的史料作了抽样统计,发现仅《复明运动》一卷,所征文献共在三百一十种以上。其中诗文集八十五种,包括《左传》、《史记》在内的史传二十三种,地方志二十四种,新闻、纪略类十九,杂记、随笔类十六,丛话、野史类十二,年谱九,实录四……在诗文集中,钱牧斋一人独占十二,钱氏同时代的士人二十余种,内顾炎武五,黄宗羲、吴梅村各二,余下的以唐宋名家居多,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应有尽有。
书读得越多,越不敢妄说,陈寅恪实质上是用他总结王国维时的方法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可概括为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用这三种方法,他晚年发表约七十七万字学术著述,参考引用了各类文献九百零七种,六千一百四十四次,内容分别为哲学二十四种,佛教二百二十六种,道教十七种,政经二十一种,语言三十一种,文字一百八十种,史地三百四十九种,综合二十七种,科技二十一种,艺术十一种。
1948年陈寅恪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当局将他作为抢救国宝第一批名单,派专机从北平将他与胡适一起接往南京,但陈寅恪却没有去台湾,他在南京转道上海,来到岭南大学。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对政治局势判断得如此明了,不能不说源于他的读书功底。对此,他这样说:“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的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研究和读书生活,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也不为左右倾思潮所左右。
张培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