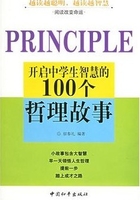嗡嗡的声音自北方临近,警报声如独狼的哀号,让它的哀鸣弥散在夜空,指望形成对它的保护膜呢。小文奔出屋望夜空,自北方而来的飞机越过绥化城,根本不理睬绥化城南去。人人都已经知道,那是苏联的轰炸机。在这 1945年的秋季,日本人真正正正地成了秋后的蚂蚱,人人都知道没几天蹦跶了。之前的夜晚,就有飞机轰鸣地南去。后来又轰鸣着北去。有消息传来:苏联人轰炸了长春、沈阳。苏联的轰炸机四平八稳地就溜达了来,扔完了炸弹再四平八稳地溜达回去。鬼子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毕经纬也仰望夜空看南去的轰炸机,当轰鸣声在南方的夜空消隐,他向小文一笑:“那飞机有点像大大的蚊子。”孩子立即想到曾经被小伙伴喊做“小蚊子!小蚊子!叮人肉,喝人血”,犹在耳际。
孩子咧嘴一笑,想:嗯,真想当那大蚊子呢,叮鬼子的肉,喝鬼子的血!毕经纬望轰炸机的时候,冷冷的神情,若有所思。白天晚上,日本宪兵咔咔地来去。听说苏联飞机不光来丢炸弹,还空投了谍报人员,前来侦察鬼子。据说那些谍报人员都是抗联,是鬼子的老对手。
宪兵队白天在街上来去,盘查可疑人;夜晚会突然闯进查户口。对没国民手账的,一律抓走。那被抓走的人被卡车拉到郊外,在大甸子里枪决。不知道有多少冤死的,不知道有多少真抗联为国牺牲。鬼子在发疯,垂死挣扎。
风中都掺杂着一股子血腥气。毕经纬坐在他的写字台前,若有所思地以手指点击着桌面。多年以后王景文才明白,那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习惯动作。绥化城火车站那儿,鬼子的军列一列接一列地北去,准备着迎击苏联军队。毕经纬经常斜背着猎枪乘马出城,去大甸子里打野兔。一顶瓜皮帽扣脑袋瓜上,麻秆似的身材,白皙的面庞,斜背猎枪的形象其实显得有点滑稽,风大点没准儿能把他刮天上去呢。但是,回城的时候,马背上或是搭着野兔,或是搭着野鸟,还真不空手呢。到了大院,那野味扔给厨子,为大院内全体人员享用。毕经纬沿袭老毕的作风,伙计们吃啥,自己家人跟着吃啥。
战争的脚步临近。
毕经纬的猎事倒频了。
有天小文跟毕经纬待在书房,毕经纬虽然捧着本书,但漫不经心,眼睛倒是在书上,可看到的不知道是啥呢,手指缓缓地、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下人进来了,带进了个鬼子,说太君要在这里订豆腐,让每天给他们送 300块豆腐。毕经纬眯缝着眼睛瞅鬼子,而后跟下人说:“收钱就是。”而后摆手让下人领鬼子出去。
“给鬼子的豆腐里应该放点耗子药!”小文说。毕经纬眯缝着眼睛瞅小文,溢出笑,有那么点诡异的笑。给鬼子送豆腐的事不交给小文。哼,许是真怕我爹给放耗子药呢!夜空中,一家苏联运输机低飞。机舱就几个人,舱门打开,两人跃出,舱内的人将绑缚着一只皮箱的降落伞抛出。此次的飞行,专为送谍报人员潜入。完成运送任务的飞机折转北去。
落地的雷鸣解下降落伞,隐约中望见绑缚着发报机的降落伞正稳稳地落下,可是,他听到了扑通的一声,惊骇地发现,装着发报机的皮箱像瞄准似的,落进了一池塘。在这秋季,整个大甸子都干爽着,可是,发报机就不偏不倚地落进了一个池塘。池塘那头扑通一声,雷鸣的心中咯噔了下。这一个谍报小组由两人组成:雷鸣、余昌文。都是抗联退往苏联的人,现在奉命潜回。雷鸣是组长。
余昌文扑进了池塘中,捞出了皮箱,还有一个包裹。皮箱打开,里边已经进满了水,发报机已经被水浸泡。“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余昌文说。西方,绥化城的方向,一列火车鸣叫着北行。“你赶往望奎吧,我们得立即离开这里,省得鬼子的搜索队赶来。两天后按计划与我碰头。”组长说。发报机由组长掌管。那包裹中,给每一位潜伏的人备了三套服装:日军军服、苏军军服、中国百姓服装。绥化城的毕家大院当然也是养着马车呢,不过不是送货的,毕氏豆腐卖出名了,都是商贩来上货。但是,毕家的马车给鬼子送货。
小文赶着驴车拉水,水箱已经装满了水,往回走,人呢,有点走神,想呢:那苏联的飞机咋不把这绥化城也炸一炸呢?驴车晃了下,停下,原来是一个人挡道呢,毡帽下一张脸笑吟吟地望向自己呢。“你干吗呀?”这话到了嗓子眼,咽了回去,瞅那挡道的人面熟。
四目相视。挡道的摘下毡礼帽,让孩子看自己完整的面庞,铁色的面庞哦。小文惊呼:“雷叔!”跳下车。差一点喊出“营长”,就是喊出了雷叔,也立即警觉地四外撒目了下。“吓,大小伙子了!”雷叔说。“你们要是打鬼子,可以带上我啦!”小文憨笑地说,当然目光也是四处撒目跟前没人才敢说,压低声音说。“可别瞎说,可别在大街说这。”雷叔说。“那你到我那儿!”小文迫切。“你那说话就方便?”小文就说了毕家大公子在绥化开豆腐坊的事,压低声音说羊的事马的事是跟老东家说了实话的,老东家可是没怪罪的,一点没怪罪,只是不让再跟别人说。“哦,去你那瞧瞧。不过,你咋跟别人说我是谁呢?”“嗯……”小文挠头,后来咧嘴一笑,“就说你是我舅!”“也成!”雷鸣笑着点头。小文牵了毛驴和营长并排走。“叔你有手账吗?”小文问。“没有。”叔低声回答。小文将缰绳递叔手中:“那你赶驴车,鬼子对这驴车很熟悉,遇着了从不盘查。”“哦……有我这样赶驴车的吗?”营长的意思是自己倒是乔装了,可还是不太像赶驴车的,营长的大手拍了下驴的脊背:“驾!”驴激灵了下,麻溜地快步。“我碰见我舅了。”进了大院,小文跟每一个遇见的人说。营长微笑,点头,回应人家的打量。“我碰见我舅了!”小文兴高采烈。水箱的木塞一拔,水汩汩地向水桶喷流,桶满了,再换上空桶,一桶桶地往缸中倒。
“舅”帮着干,抢着干。小文想起先前营长的伤,惊奇地看营长,那伤仿佛就没有过,营长已经完全康复。“我领你见下少东家?”小文征询。“好啊。”“我碰见我舅了。”书房,小文跟少东家说。打营长进来的时候少东家就打量。营长向少东家点点头。小文突然就冒出个舅。在记忆中使劲地捞,也捞不出小文还有舅舅在这边。少东家轻轻地“哦”了声,站起,抱拳:“哦,那也是我的舅了。”友好地笑。其实心里嘀咕:哪来这么个舅呢?向小文道:“还不看茶!”示意“舅”在一旁的茶几前落座。在小文倒茶的当口,少东家问:“舅舅贵姓?”“姓孙!”小文抢着回答。娘叫啥不知道,但还是知道姓的,可营长哪能知道我的娘姓啥呢?“舅舅”从容端杯喝茶。少东家盯视小文。小文向少东家憨憨地笑。小文已经感觉到少东家在审视营长在盘查营长。
少东家向小文摆摆手:“你出去忙活,我跟舅说说话。”少东家嫌小文碍事,往外撵小文了。小文望营长。营长说:“嗯,你去忙,我和少东家说会儿话。”小文一出去,少东家就站了起来,问:“舅到这绥化城做啥?”“想做个买卖,来探探行情。”“大买卖吧?”“舅”笑而不语。“‘舅’可有国民手账?”“没有。”“那在这绥化城可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可能掉脑袋!”“外甥可能帮上舅的忙?”“外甥”笑而不语。“外甥”从写字台后走出,到了“舅”的面前,竟然把挂在‘舅’腰带上的一个水葫芦给解了下来,拿在手中端详。那葫芦上刻着“小文”两字。那是毕经纬在王村的毕家大院时,小文到书房唤少东家去吃晚饭,少东家看到了小文腰间晃荡着的装水的葫芦,就说:“把你那葫芦拿来,我给你刻上名。总得认得自己的名的。”拿着葫芦,刻上去的是“小文”俩字,并且念给了小文。可是从打小文和双子帮助抗联营长之后,那刻着“小文”俩字的葫芦就不见了,却在眼前的这个“舅”身上。“舅吃过我家的羊吧?舅骑走过我家的一匹马吧?”少东家得意地说。
“舅”只是个笑。离开大甸子的时候,营长带走了小文的水葫芦,留作纪念。难以忘怀的两个孩子。
小文惦记着和营长近乎,可是,营长一直待在少东家的书房,晚饭的时候也没出来,厨子做了好菜,两人喝酒呢。小文等到深夜,也不见营长出来,就睡了。小文和伙计们睡在一块。
午夜的时候,少东家才想到得安排营长睡哪,安排人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在鸡叫头一遍的时候,少东家让营长歇息,自己也歇息。所以啊,早饭的时候,小文也没见到营长。少东家也没在书房。后来知道营长睡了单间。来到那单间的屋前,里面静悄悄,知道人在里面酣睡呢,不能搅扰。少东家也还睡呢。
后来少东家起来了,也没唤营长,就自己一个人在伙房吃了早饭,而后就扎进了书房。小文等了阵子营长,营长就是没动静,就溜到书房。正忙活的少东家猛地抬起头,注视着小文,微笑地念叨:“小文子。”案上,有些凌乱的纸张,有剪刀,有国民手账,不知道是谁的国民手账,小文进来的时候少东家正拿着个大印章瞅着纸张预备盖下去呢。小文有点明白,少东家可能是在做国民手账,可能是给营长做国民手账。先前也见过少东家这阵势,做国民手账对少东家可不是第一次了。少东家的胆子可是够大的!本事也大,能自己做国民手账!小文知道少东家在做天底下最机密的事,跟少东家一笑,说:“那我去了。”就是少东家对自己再好,也得做个知趣的人。
营长是被叫醒的,少东家叫人叫醒的,被叫进了书房,少东家还叫伙房送了饭菜到书房。先前小文是可以随便去书房的,但是,营长来了,营长和少东家在一块的时候,小文感觉到不能随便去了,好像自己是局外人,对两人的亲近似乎有着什么妨碍。吓,抗联的营长和少东家瞬间就搞到了一起,而且简直要黏糊成一个人了!小文醋溜溜的。
伙计马方要去给日军宪兵队和兵营送豆腐了,临走的时候,去了书房,出来的时候,后面跟了营长。小文刚凑上前,营长:“我跟着送豆腐去,有啥话回来说。”
“哦……”小文吃了一惊:营长自己往虎穴里闯!就想到少东家书桌上的国民手账,就明白八成是给营长做的。少东家在帮营长。大车上,一屉一屉的豆腐摞得高高;开始就日本宪兵队要豆腐,后来鬼子的兵营也要。每天都得一大车豆腐呢,先在宪兵队卸,而后再奔兵营卸。其实有固定跟车的,可是大清早被少东家打发去王村了,过些日子是毕来福老爷子的生日,少东家派人去问爹要不要来绥化城这儿过生日,如果来,可包家酒店。小文怀疑少东家是特意倒出了位置,好让营长自自然然合情合理地跟车。“你的,良民证的有?”见了陌生的跟车的,鬼子很可能盘问。营长肯定有国民手账递上,一定有国民手账递上。难道少东家是地下党?是共产党?
当营长要按约定时间去大甸子里和潜伏到望奎和佳木斯的手下会和的时候,毕经纬问雷鸣,可否愿意让自己随着一同前往大甸子?毕经纬说,也许还能帮上什么忙的。我们的发报机落到河里受了潮,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毕经纬咧嘴笑。那就先看看能不能还好用,他说。毕经纬斜背的是发射子弹的新式猎枪,而营长斜背的是发射火药的老洋炮。也就毕经纬吧,能大模大样地背着猎枪来去。两人乘马出城,毕经纬跟城头日军岗哨说:“犬养,今儿个若是打着了野兔子,送你只。”本来那被叫作犬养的鬼子班长目光在雷鸣身上呢,听了毕经纬的话,立即咧开了大嘴:“好的,好的。”纵马远离了盘查过往行人的日军岗哨,毕经纬骂:“瞧鬼子的这姓,狗养的!”雷鸣大笑。就在落进发报机的那个池塘,潜进佳木斯的人已经等待在那。而潜进望奎的人已经无须等待,毕经纬的人昨日报告:一位抗联的人在望奎被日本人抓获,头颅被日本人挂在了电线杆子上。潜进佳木斯的人带来的情报与毕经纬提供给雷鸣的情报是相吻合的,因而,雷鸣决定采信毕经纬提供的望奎、绥化日军的情报。
在两个人接头的时候,毕经纬远离着。当发现一只野兔的时候,纵马而追,一枪将其毙命。枪声令潜往佳木斯的人一惊:“那是什么人?”
雷鸣望向捡拾野兔的毕经纬,说:“自己人。他在帮助我们。”
发报机被藏在树丛中,有一些干草遮掩着。箱子的盖是敞开些的,为的是在秋日的烘烤中挥发发报机中的湿气。但是,雷鸣按下电源按钮的时候,期待的指示灯没有闪亮。他望向乘马在大甸子中晃荡的毕经纬。
“难道发报的事他也能帮上忙?”同志问。雷鸣一笑,点头,说:“你回佳木斯继续执行任务,两天之后我们仍然这里会和!”见前来接头的人要离去,毕经纬纵马过了来,跟奔往佳木斯的人说:“把这兔子烤了再走吧。”“这兔子我们给吃了,回去的时候你拿啥喂狗呢?”雷鸣说。毕经纬知道是指出城时自己跟犬养说的话,哈哈大笑:“野狗,可喂可不喂!”烤了野兔子之后,雷鸣的手下奔了佳木斯。毕经纬和雷鸣来到一株老树面前,旷野中,这株老树率领着几株小树矗立。而这株老树老得狰狞:粗粗的躯干腐朽得成了空心膛,那树洞透着阴森,残余的躯干撑着树冠硬撑着绿,居然还生命着。
就在那树洞中,毕经纬掏出了一只皮箱,皮箱中是发报机。“老哥,会使这玩意儿?”毕经纬还调侃呢。“你这毕家大公子,可会杀人?”老哥反问。“时局迫人啊!”毕经纬慨叹,上马,“老哥。您忙,我得再去打只兔子。”纵马而去。抗日,使国共两党走到一起;但是随着胜利曙光的呈现,国民党开始再次审视共产党,共产党人也感觉到了那被审视的目光。而上峰对他毕经纬的指示,最近期的就是:防范共产党人夺取胜利果实!对雷鸣的帮助,是毕经纬的擅自行为。他知道自己的上峰对于这种行为很难允许,而且可能被审视,被作为亲共分子审视,甚至被怀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最后关头,在这大甸子里,国共合作。为了毕经纬的安全,这秘密被雷鸣长时间严守。枪声响起,毕经纬击毙了一只奔逃的野兔。在这大甸子里,只要你一惊扰,往往就会有野兔窜出、奔逃。
雷鸣结束发报,站在那株老柳树下看毕经纬,毕经纬纵马而来,马背上已经搭了三只野兔,雷鸣很惊讶这个军统特务的枪法。毕经纬将手中猎枪扔向雷鸣,雷鸣扬手接住,毕经纬说:“老哥,你也试试这枪。”
“好的。”雷鸣上马而去。毕经纬将发报机在此隐藏。大甸子里传来枪声。雷鸣带了两只野兔回来,毕经纬说:“老哥也不赖啊!”当毕经纬将一只野兔扔给犬养的时候,那鬼子向毕经纬挑着大拇指:“你的,朋友!朋友!”
小文失魂落魄的样。遇见了雷叔,本来是多么欣喜的事,可就是没多少机会亲近。
就是吃着野兔肉也不欢喜,因为不是和雷叔在一起吃。雷叔和少东家在书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