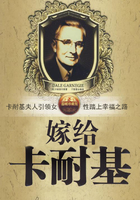好象他什么时候对我说过,我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子,不适合他。而我也知道,他算
不得才学出众,事业心不太强,又没有独特个性,也未令我倾心。
这就是我的真实故事,并非荡气回肠,美丽动人。
那么,读者朋友,你的故事又怎样呢?
猛记起你有千百种美丽,
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
——日已正午
何处再追寻你的踪影?!
——蓉子
昨天下了一场雨
采访对象:柳新
采访时间:2000年12月
采访地点:北京
我叫柳新,是北京联合大学二年级学生,学法律的。我家就在北京市西城区,家里还不赖。上个星期,我跟我女友洁“吹”了。一天之间,5年的感情全部泡汤,说完就完。这就好像是一场瓢泼大雨,冲得我分不清方向了。真的,我挺后悔,可有啥办法,“吹”了就“吹”了呗!我是不会去求她回心转意的。
5年前,我刚读高中,与洁同在一个班。因为我俩是班上长得比较中看顺眼的两个男孩、女孩,同学们就老爱拿我俩开玩笑,说什么“天生一对”。很自然地,我俩就往来了,也就相好了。不过,我俩的相好与成人那种正式的恋爱还是不同,当时只是停留在彼此有些好感,平常在一起学习、玩儿的机会相对多一点而已,也就是一种异性朋友吧。但还是很纯洁,很有分寸的。若不信,可去我俩的母校调查么。
我们的关系在高中保持、发展了3年,一直挺融洽的。到1999年高考,我们又都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不过,我读的是法学专业,她读的是金融专业。这不奇怪,因为我爸在法院当刑事庭的庭长,而她的两个哥哥都在银行系统上班,都是受了家庭影响。由于仍然在一个大学,我们非常高兴,大家依旧保持着像高中一样的经常往来与友好关系。有些公开课与基础课,我们还在一起上呢!于是,我们走过去坐在一块,感觉跟高中差不多。到周末,我们会电话联系,约个双方都有空的时间一同去看邮展,去玩大雪,去吃“麻辣烫”,或去科技馆看机器人表演。
进了大学,大家的年龄慢慢大了,有点懂事了。看到周围的同窗,特别是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一双双、一对对,亲密“拍拖”的样子,我也挺向往,开始蠢蠢欲动。自己不是生得也不“次”么,为甚么不也痛痛快快来一场“爱情闪电战”?
是呀,旁边就有现成的追求对象。洁的模样这么妩媚、俊俏,我对她早已害着“相思病”了。也许开始有不少男生明里暗里在打她的主意,千万别让那些肚子里满是坏水的家伙捷足先登,我可要抢取主动。我就在大一上学期期中的某个星期天傍晚,尽力控制着激动、紧张的心情,上街买了一束鲜艳的玫瑰,给洁送到了她家门口。洁接到我的电话,出门来一看,惊讶马上写进双眼,身子忸怩了一下,脸颊迅速绯红一片,像此刻西天的晚霞,好看极了。而以前我为什么从没见她这么灿烂过?以前说她漂亮倒是漂亮,却是静止的、平淡的,不像此刻完全开放,魅力四射,容光焕发,楚楚动人。这大概也就是蓓蕾与鲜花的区别了。或者说,以前的她,更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幅仕女画,而今天站在我面前的才是她的真人。我为自己第一次发现了她真正的美而吃惊,而得意。
我正在欣赏洁的容光,只听她轻轻地说,没想到,你也会来这一手。谢谢啦!在目前情况下,她不好邀请我进她家里,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进去,因为她全家人都在呢。反正她接受了,这让我内心一阵狂喜,好像中了什么大奖。我告辞她回家,一路上就像踩在云头,轻飘飘的。我恨不得把这条天下第一喜讯告诉每个人,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
既然第一步成功了,我紧接着就采取了第二步行动。过两天后,我给洁捎去一桢小纸条,约她下个星期天上午去日坛公园玩,8:30在她家楼下“集合”,不见不散。我想,这次与以往不同了,以往只是普通的同学、朋友关系;这次要“升级”了,是正式的“拍拖”呢!她也应该明白的。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8:20来到洁的楼下,忐忑地等着。她会下来吗?如果她不下来,我该怎么办?可容不得我想,到8:30,她还没下来。我暗暗说,这回完了,她不会下来的。正当我胡思乱想,准备打退堂鼓时,8:40,她却下来了,脸上一种似笑非笑的诡秘神气。原来,这就是小女孩们捉弄、或曰考验男孩的惯用伎俩。但她今天是刻意打扮了一下的,虽不是浓妆艳抹,却也娇媚、可爱。起初我俩有些紧张、局促,不习惯,但经过短时的调整,彼此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毕竟有多年的交情了嘛!两人各自跨上自行车,向月坛而去。
我们像其他同学一样,谈起“恋爱”来了。可是,这与过去有什么两样?还不是在一起玩儿,一起学习,一起去吃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对对方说过“我爱你”或者是它的英文版“Iloveyou”,甚至连“喜欢”一词都说不出口。但我们彼此都很清楚,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的。再说,洁“警告”过我,不要靠她太近。她答应跟我“暂且”保持“那种”关系,算是给我面子;但是,她不想发展太深,因为我们还小,又只是在校学生,她不想让这些事影响她的学习,更不希望有人过多干扰她的个人生活圈子。可我已经够开心了,因为这么美丽、可爱的女孩,她只接受我一个人,她是我一个人的,绝不会再有其他小子侵入她的心田的。
我俩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既然是有这层心意了,偶尔还可以轻微表达一下的。比如说,有些晚上,在公园的小树林内,或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眼见旁边没人,我俩会略有一丝冲动,轻轻搂抱一刻,互相环绕着腰,在脸上、额上、嘴上很温柔地、短时间地吻几下。两人的眸子里映着对方的小像,而眼波的微光就在那里和煦地闪烁。
我们还是正常地生活着,一切都像一条直线,但是这条直线太水平了。既没有波澜与曲折,又没有飞升与高潮。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周而复始。很快,日历翻到了2000年12月。本来,如若不是发生了上星期的变故,也许故事还要改写。可是,谁又知道,将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呢?
上星期天——又是星期天,我的许多好的、坏的消息,都是出现在星期天,我真是与星期天有缘了——我在我家宿舍楼下的街巷里一个“网吧”“冲浪”。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迷上了“冲浪”,几乎天天要玩一阵。由于怕父母说我因为“冲浪”耽误学习,我有时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自己家那台漂亮的电脑,去外面“上网”。
突然,我看见洁就站在我的电脑旁,一时愣了。我随着她走出门,原以为她要劈头盖脸地骂我一顿的,可我见她脸上非常平静,没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点也不像生气,暗暗放心了。的确,“上网”、“冲浪”,并不是犯法的勾当,也不是“玩物丧志”的低级游戏。它也是一种有益的智力活动,是新时代的学习方式。再说,我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也不用为高考,为大量复习资料与模拟试题发愁了。
我正准备跟她来一番缠绵,因为我们好些天没见面了,却只见她有躲闪的举动,很是反常。这时见她开口了:“果然,你在这里,我没猜错。本来咱俩也没什么关系,我没资格说你;而且,‘上网’并不是坏事,你不妨尽兴地玩。但是,作为一个你曾经的同学与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几点我个人的意见,供你参考。你过去玩小动物、玩邮票、玩电子游戏、玩摇滚乐,如今又玩电脑,这都无可厚非。然而,你没有一项特长,能力不突出,成绩也一般,真的,你很平凡。作为男子汉,今后你怎么在社会上立足?”这一席话,说起来也许轻描淡写,听起来却语重心长。她是我的什么人,妈妈?姐姐?老师?教育工作者?这样说我!
而且,我觉得毛骨悚然。她怎么跟我用这种口气说话?让人一点也不爽快,倒不如大骂、狠揍我一场。
她又说了:“我跟你摊牌了吧。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追我,我准备答应他了。他是大三年级的,还是班长、分团委支书。人家组织、活动能力强,政治思想好,口才出色,会演讲,又懂书法、写作,成绩也是顶呱呱的,比你只知道玩,还是强多了吧?光长个漂亮皮囊,有啥子用?‘绣花枕头’而已。好,‘大玩家’,尽管开心玩吧,咱们再见了。”她一说完,就迈开碎步,走着笔直的步伐,没有回头,倏忽不见了。待我回过神来,她已经消失在巷口。
那天,天空很晴朗。洁也没骂我,没跟我吵,彼此没有激烈的冲突,我俩安静地分手了。可是,我却觉得,自己身上仿佛淋了一场大雨,弄得形象非常狼狈。我很伤感,除了失去好女孩洁外,还有她那席话对我的当头棒喝。
我是不敢奢望好女孩洁回心转意了,但我打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希望下次碰上她时,让她看看我的新面孔,听她夸奖我“好样的”,而不仅仅仍旧叫我“大玩家”或“绣花枕头”什么的。
昨天下了一场雨,带走了我的一个希望,却送给了我另一个希望。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它们价值三枚炮弹。
在罗密欧的爱情里
它们是未来的全部考验。
在新世界商场的超市
它们是斩钉截铁的二十一世纪。
——清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鸳鸯怎过考试关
采访时间:2001年11月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对象:刘晋、王滇
这篇文章所要反映的故事,也是与北京的户口制度有关。本书内与北京的户口制度有关的文章一共是5篇(第一辑中的第三篇《苦尽甘来,北京公主10年等待外地穷小子》、第二辑中的第三篇《亚热带阳光下的热吻》、第三辑中的第二篇《南方诗人的第二次选择》、第三辑中的第五篇《追逐北京“绿卡”,靓丽女大学生付出惨重代价》,以及本篇)。北京户口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我不是专家,对此不能做出权威的分析;我也不是权威,对此无法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可喜的是,北京有关部门对此正在逐渐想办法解决,状况在一步步改善。我只是作为一个曾经在京城读过4年书的外地大学生,了解到一些在自己周围发生的、发生在北京与外地大学生或外地与外地大学生之间的或好或坏的情感故事,这些故事都或多或少与北京的户口制度有关,觉得它们或许还有点动人与参考价值,于是把它们写下来,供师弟、师妹们一读。仅此而已。
这个故事来自我的另一篇文章《京城高校的外地学子:校园生涯四部曲》(见鄙人专著《大学校园里的“第四只眼”》,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年7月):
外地学子留京不易,特别是来自边远省区的,原则上必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北京毕竟是北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留在这儿不见得更好,大家还是舍不得放弃。除非成绩遥遥领先(可得15%的留京名额),除非是校系主要学生干部,除非关系网强,否则,“自古华山一条道”——考研究生。笔者隔壁一档案系刘姓老兄,原籍山西,其女友则来自云南,两人情深意笃,不想做“牛郎织女”,除了考研,岂有他途?都说考研渺茫,但在成绩揭晓前,这也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了。现在破釜沉舟,是离是合,一切届时再说。“风萧萧兮易水寒”,这种悲壮的场面,令局外人唏嘘不已:“做学生真苦!”
“刘姓老兄”就是本文中的男主角刘晋,山西晋城乡下人,与笔者一样,1994年考到北京念大学。他读的是档案学专业,他的宿舍与笔者隔壁。对刘晋,其他方面的印象我已不大深了,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不穷不富、不好看也不难看、成绩不好也不坏。我只记得两件:一、他可以拿醋当水喝;一瓶老陈醋,见他“咕嘟咕嘟”吞下去,我们都由于吃惊把眼睛瞪得牛瞳人一样大。二、他喜欢刚打完球回来,气喘吁吁的,便急着要用冷水洗头,且每回一洗头必感冒不可。他的女朋友王滇,一个小鸟依人般的南方镇子姑娘,有长长的睫毛、颤颤的歌喉,老家在云南滇池附近,也是1994年进入我校社会学系深造。大一上学期国庆结束后,他们刚刚从昌平军训回来,恰好碰到两个系在一起上《马克思主义原理》课,认识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开始同上另一门“课”——恋爱。多年来,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当时我们都认为,并且我们至今也都认为,这两位真是天生的一对鸳鸯,组合非常科学。原因之一,两人的名字都与老家的简称相同;原因之二,两人都出生于1975年,属兔;原因之三,两人一个来自南方,一个来自北方,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原因之四,两人很早就一见钟情,关系发展神速,是极宝贵的真爱;原因之五,王滇对刘晋非常好,好得连我们局外人都感动甚至嫉妒(因为刘晋还是有些脾气的,而王滇一丁点脾气都没有,偶尔他们吵架,王滇绝对不还嘴;而且王滇平时轻言细语吐气如兰、对刘晋照顾得无微不至特别是他感冒时给他打饭洗衣喂药补课等,哪怕最坚强的人也要被她软化);等等等等。我们大家都说,如果这一对还不能成功,那在整个世上我们再也不相信什么爱情了。
刘晋家与王滇家都不够富裕,王滇家可能还好一点。但在大学4年里,他们节衣缩食,将生活费积攒下来,把北京城内城外的名胜古迹、公园景点,从故宫天坛到颐和园圆明园,从鲁迅故居毛主席纪念堂到世界公园中华民俗园……都玩了个遍,还远去承德避暑山庄、山东泰山、河北小五台山、天津渤海湾旅游。他们去居庸关、十三陵、卢沟桥等地时,是踩自行车的。1995年寒假,他们一同去刘晋的山西老家过年;1996年寒假,他们又一同去王滇的云南老家欢度春节。在我们周围一群人中,据我所知,最早一批去看美国大片《辛得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的,最早去欣赏维也纳音乐会的,也是他俩。这就让我这个平日自负于稿费颇丰厚,却老是感到手头很紧、捉襟见肘的人非常蹊跷:他们是怎么攒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