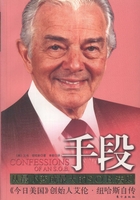胡适,人们都知道,在此之前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他是以“全盘西化”论著称的。胡适最早谈论中西文化,是在1926年前后。这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中说:“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1928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 Manhind)里的一章。”在1926年所作《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里。胡适对当时一些人继续高叫西洋有物质文明而东方有精神文明的老调,给予了批驳,说它赞赏西洋文明则可,说它提倡“全盘西化”却没有道理,因为他没有这样说。1929年,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作《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首次使用了“全盘的西化”一语。此文发表后,潘光旦撰文说,文中一个词可以译为“全盘西化”,但不够确切,最好不用这个说法。1934年,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一书,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在1935年6月22日作《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专门讨论这个口号。虽然他说“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点语病”,“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但他还是“赞成”这个口号。因为在他看来,“全盘西化”就是“充分世界化”,“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他“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人们自然把他当做“全盘西化”论的领袖。
也许胡适已经预料到他这次讲演将会产生巨大的反响,并引起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他在讲话的开头以“魔鬼的辩护士”自喻,说:“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驳倒、推翻。”
李敖应《文星》杂志之约,发表了《播种者胡适》,作者带着充沛的感情写的。字行里洋溢着他对胡适崇敬和爱护,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
李敖对胡适的批评是不留情面的。文中说:“在上面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也就是说,胡适不该钻到真正的学术中间去,写什么《白话文学史》,搞什么《红楼梦》研究、《水经注》研究。
文章对胡适的人格做了分析,特别赞赏胡适“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的善举和人情味。李敖说:“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作者嫌胡适的斗争精神不够,说:“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李敖这样批评胡适,一点也不奇怪。这是真正的李敖!李敖跟胡适最大的不同,就是一直坚持在现实斗争的最前线,他不摘纯学术,他的学术研究是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所以我们读李敖的著作,总觉得“人世”很深,就像在读报纸上的政论。读胡适著作,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大声疾呼实现民主、捍卫民主的声音,一种是讲学论道的声音,至于面孔,却只是一副,呼吁民主也是学者的面孔。而读李敖的著作,却只有一副战士的面孔。不过不是拿枪的战士,而是拿笔的战士。因此,这里对胡适的批评,勿宁看做李敖对自己心灵、对自己人生观的表白,要更符合实际一些。
六、给李敖浇冷水的人
1961年8月18日,李敖考取了台大历史研究所。李敖在姚从吾帮助下,来文献会工作,开始他的文化论战。
对《播种者胡适》,胡适本人并不十分满意。杨树人于1964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七十六期上,发表了《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其中说:
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地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
“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划。“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划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
后来钱思亮告诉李敖,胡适逝世以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一封胡适读了《播种者胡适》以后给李敖的信。过了三十六年,1998年,李敖碰到他在台大历史系的同班老同学陶英惠,陶当时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分兼领胡适纪念馆,李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恩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陶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去找。后来果真找到了,陶英惠寄来一份复印件。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批语:“这是一(封)信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信是这样写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奉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前,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l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 A.,井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胡适死在2月24日,说明这封信是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这封信写得既认真又婉转诚恳,足见其光明正大,胸怀磊落。
胡适这封信是给李敖“浇”“冷水”的,可是只举材料上的是非,不提观点(评价)上的是否得当,大约因为他是当事人,不好置喙,也许他会说,只是没有把信写完——这是否是胡适的绝笔?——从道理上说,胡适对李敖的一些批评是不会完全首肯的。据《李敖快意思仇录》所言:“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以下是李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他举了胡适为其搞《红楼梦》考证所说的一段话,意在说胡适摘《红楼梦》考证,是“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叫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也是借题发挥。是不是“借题发挥”,可以看做李敖和胡适两人在做学问上的一个根本分歧点。李敖一贯如此,这也是李敖之所以为李敖的原因所在。胡适自述搞《红楼梦》考证,是为了“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是为了叫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多少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如果说搞《红楼梦》考证是出于这个目的,那么搞《水经注》研究又是为了什么呢?搞其他的种种古典文学研究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说胡适为他所做辩护是对的,那就又出现一个问题:曾经用“借题发挥”的手法搞学问的胡适,现在反对年轻人这样做,这不就违背了胡适自己在二十七岁时所作《不老》一文的精神了吗?
七、给谈中西方文化的人看看病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作于1962年1月26日,发表在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五十二期上。
文章开头说,自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都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作者慨叹,“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作者要为中国文化诊诊病。过去也有人诊过病,但“历代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自然不能看清病象,弄清病源。以下他把病例分为十一种,每种厘定一个病名。计有:
义和团病。这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这类人清朝以阮元为代表,民国以后是熊十力,六年以后,“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滥用‘民族自信心’”。
古已有之病。“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现代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熹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们,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中土流传病。“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西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
不得已病。“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好使他心安一些。”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作者称“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这种论调“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1935年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