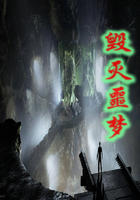“我亲手交给他,”她想,“他自然会来的。”
第二天,莱昂打开窗子,在阳台上低声唱着歌,擦亮他那双浅口皮鞋,抹了好几层鞋油。他穿上一条白长裤,一双精致的短统袜,一件绿上衣,把他所有的香水全洒在他的手帕上。他去烫头发,又弄直,让头发更显得自然美。
“还早得很呢!”他看理发店里的杜鹃鸣钟(是钟声仿杜鹃叫的挂钟。),正九点,心里想道。他看了一会儿一本旧的时装杂志,走了出去,吸着一支雪茄烟,走了三条街,心想时间到了,就慢慢地朝圣母院前的广场走去。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天的早晨。金银器店铺里的银器在闪闪发光。太阳斜照着教堂,灰色的石头裂缝被照得明亮耀眼。在蓝天上一群鸟在盘旋,绕着有三叶饰的小钟楼飞着。广场到处是喧哗声,铺石路的两旁的鲜花发出阵阵香气,它们是玫瑰、茉莉,香石竹,水仙,晚香玉,中间不均匀地间隔着潮湿的草地、樟脑草和喂鸟的海绿。广场中央的喷水池汩汩地响着。
在宽大的伞下面堆成金字塔形的罗马甜瓜中间,没有戴帽子的女小贩用纸包一束束堇菜花。这个年轻人买了一束花。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位女人买花。他闻花香的时候,胸脯因为得意挺得高高的,仿佛这件他准备送给别人的礼物又回到自己手上一样。但是他怕给人看见,就果断地走进了教堂。教堂侍卫这时正站在门口,左面的大门当中,“跳舞的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原应是莎乐美,但被看成为玛丽安娜。莎乐美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的雕像底下,帽上插着翎毛,长剑拖到腿肚,手上拿着一根木棍,比一位红衣主教还威风,又像一只圣体盒一样闪闪发亮。他向莱昂走过来,带着教士向孩子提问的时候露出来的假惺惺的微笑。
“先生想必不是本地人吧?先生愿不愿意看看教堂里的珍品?”
“不要。”莱昂说。他先在侧道走了一圈,然后又到广场上张望。爱玛还没有来。他一直走到祭坛那里。中殿的尖形拱肋起端和一部分彩画玻璃窗倒映在盛满水的圣水缸里。但是彩画的反光在大理石边上分开了,照到更远的石板地上,就像是铺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地毯。外面的强烈的阳光从三扇敞开的大门照进教堂,形成三道宽宽的亮光。在中殿的深处,不时地走过一个圣器室管理人,像匆匆忙忙的信徒那样,在祭台前面斜着身子跪一下就走开了。水晶分枝吊灯一动不动地挂着。在祭坛前点着一盏银灯。从侧面的偏祭台,教堂的一些阴暗的地方,有时候会传出叹息似的声音,还有放下栅栏门的声音,在高高的拱顶底下回响。莱昂踱着庄重的步子,沿着墙走着。他觉得生活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
她马上要来了,她一定很迷人,又很激动,并且暗暗看身后有没有眼睛注视她,她会穿镶边饰的裙袍,手执长柄金丝眼镜,脚穿细巧的高帮皮鞋,千百样的娇美,他从没有感受过,还显出将失去贞节的女人难以形容的诱惑力。教堂仿佛是一间在她周围准备妥当的特大的客厅,拱顶向下倾斜,为了在黑暗里听取她供认自己的爱情,彩画玻璃窗亮闪闪的,为了照着她的脸,香炉将要点燃,为了让她在芳香的烟雾中像一位天使那样出现。但是她没有来。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眼睛忽然看到一扇蓝玻璃,上面画着几个拿着篮子的船夫。他很专心地对它看了很长时间,数鱼身上有多少鳞片,船夫的紧身短上衣有多少钮扣孔,而他的思想却飘忽不定,在寻找爱玛。教堂侍卫站在一旁,心里暗暗生这个人的气,居然独自一人来参观大教堂。在他看来这个人的表现实在太奇怪,可以说抢了他的东西,几乎是犯了渎圣罪。但是石板地上响起丝绸衣服的声,一顶帽子的边,一条黑披肩……是她!莱昂站了起来,向她跑过去。爱玛脸色苍白。她快步走着。
“看吧!”她交给他一张纸,说道,“啊!不。”
她急忙把手缩回来,走进了圣母堂,靠着一把椅子跪下,开始祈祷。年轻人对这种心血来潮的过于虔诚的行动很恼火,接着看到她在约会的地方,像一位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的地区名。)的侯爵夫人一样沉溺在祷告中,又感到她有点可爱,再后来立刻不耐烦了,因为她的祷告一直没个完。爱玛祈祷着,或者不如说是在努力这样做,希望上天会突然赐给她某种决心。她想得到上帝的救助,两眼牢牢地望着华丽的圣体龛。她吸着一只只大花瓶里盛开的白香芥的香气,仔细听着在教堂的寂静中有什么声音,寂静只会增加她内心的烦乱。她站起来了。他们正想离开,那个教堂侍卫连忙走过来说:“夫人想必不是本地人吧?夫人愿不愿意看看教堂里的珍品?”
“不要!”办事员叫道。
“为什么不要呢?”她说。因为知道贞节很难保住,她想从圣母,从雕塑,从坟墓,从一切机会得到支持。
于是教堂侍卫为了按顺序进行,领他们到靠近广场的进口处,在那里,他用木棍指给他们看用黑色石头铺成的一个大圆圈,那上面没有说明文字,也没有刻什么花纹。
“瞧,”他庄严地说,“这是照那口漂亮的昂布瓦斯(昂布瓦斯,在今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大钟的钟口大小做的。大钟重四万斤。整个欧洲没有这样大的钟。铸钟的工匠因为太高兴死掉了……”
“我们走吧。”莱昂说。那个人开始向前走,接着又回到了圣母堂,他伸出双臂,做了一个概括说明的手势,那神情比一个乡下地主指给你看他种的果树的时候还要得意:“这块普通的石板下面,葬着瓦朗纳和布里莎克的领主,普瓦图大元帅,诺曼底总督皮埃尔·布雷泽,一四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死于蒙莱里战役(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在蒙莱里打败“公益联盟”。)。莱昂咬着嘴唇,直顿足。
“右边这位全身披甲,坐骑直立的贵族是他的孙子路易·德·布雷泽,布莱瓦和蒙肖维的领主,莫勒夫黑埃伯爵,莫尼男爵,国王内侍,骑士团骑士,也是诺曼底总督,死于一五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天,就借碑文上说的那样,在下面,你们看到的这个将要下葬的人正是他本人(墓碑分两层,上为骑马雕像,下为平卧雕像。)。表现死亡的雕塑有这样完美,不可能看到第二个了,对不对?”
包法利夫人拿起长柄眼镜放到眼睛上。莱昂却动也不动地望着她,一句话也不说,一个手势也不做,这两个人,一个唠唠叨叨,一个态度冷淡。他望着他们,真感到泄气。没完没了说下去的向导再往下说:“在他身旁这位跪着哭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布雷泽伯爵夫人,瓦朗蒂诺瓦公爵夫人,生于一四九九年,死于一五六六年;在左面,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圣母。现在,请转过身来看这边,这是安布瓦斯家的墓。两个人都担任过卢昂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那边是路易十二国王的一位大臣。他给这座大教堂做过许多善事。他的遗嘱里还写明给穷人三万金埃居。”
他一面说,一面不停地走着,把他们推进一座满是栏杆的小教堂里,他挪动了几根栏杆,露出了一大块东西,很可能是一座雕坏了的塑像。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这块东西是英国国王,诺曼底公爵,狮心王理查(狮心王理查,即英国国王理查一世(1157—1199),英国金雀花王朝国王。“狮心王”为其诨号。)陵墓上的装饰,先生,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的统称。)教徒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他们用心恶毒,把它埋在主教府的地底下。喏,主教就是走这道门进他的邸宅的。下面我们去看画有毒蛇(传说七世纪时卢昂有毒蛇害人,当时主教圣·罗曼将其杀死,为民除害。)的彩绘大玻璃窗。”
可是莱昂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然后抓住爱玛的胳膊。教堂侍卫惊得愣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早就慷慨地赏了他这么多钱,还有许多给外地人看的东西没有看,所以他叫道:“喂,先生。还有尖顶(指钟楼上的尖顶。)!尖顶!……”
“谢谢啦。”莱昂说。
“先生不看可错过机会了!它有四百四十尺高,只比埃及的大金字塔低九尺,整个是铁铸成的……”
莱昂赶快逃走,因为他仿佛觉得两个小时以来他的爱情已经在教堂里变得像石头一样固定不动,现在又快要因为尖顶化为一道烟,那座尖顶就像是长方形鸟笼上的截去一段的管子,又像是有窟窿的烟囱。它居然敢这样古里古怪地立在大教堂的屋顶上,好像某个异想天开的锅匠在做什么怪诞的试验。
“我们上哪里去?”她问。他没有回答,继续快步向前走。包法利夫人已经用圣水浸湿了手指,这时他们听见后面有很粗的喘气声,同时被一根棍子敲到地上的声音匀称地打断。莱昂回过头去。
“先生!”
“什么事?”
他看出是那个教堂侍卫,胳膊底下夹着二十来本装订好的厚书,贴住肚子,好保持平衡。这些都是介绍大教堂的著作。
“蠢货!”莱昂低声骂了一句,奔出教堂。一孩子在广场上玩耍。
“去给我找一辆出租马车来!”
孩子像一只皮球一样奔向四风街,于是他们两人面对面地待了几分钟,彼此都有些尴尬。
“啊!莱昂!……真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
她在撒娇,接着又显出严肃的神情:“这很不合适,你知道吗?”
“怎么不合适?”办事员反驳说。“在巴黎都这样!”
这句话如同一个无法抗拒的理由,使她只好顺从。可是出租马车还没有来。莱昂怕她又回到教堂里去。终于马车来了。
“你们至少要从北面的大门出去!”教堂侍卫站在门口喊道,“可以看到‘复活’,‘最后的审判’,‘天堂’,‘大卫王’,以及‘地狱里受火刑的罪人’那些玻璃窗上的彩画。”
“先生去哪里?”车夫问。
“随便你去哪里!”莱昂一面把爱玛推进车里,一面说。笨重的车子上路了。它顺着大桥街走下来,穿过艺术广场,走过拿破仑码头街和新桥,突然在皮埃尔·高乃依(高乃依(1606—1684),法国大剧作家,是卢昂人。)的雕像前面停住了。
“往前走!”车子里发出来的声音说。车子又走起来,过了拉斐特大街,就顺着下坡路走,飞速地跑到了火车站。
“不要停,一直走!”还是那个声音叫道。马车走出了栅栏门,立刻到了林荫大道,在高大的榆树当中慢慢地小跑着。车夫擦了擦前额,把他的皮帽子夹在两条腿中间,把马车赶出了平行侧道,到了靠近草地的河边。马车沿着河走上碎石铺的纤道,在瓦塞尔这边走了很久,把一个个小岛丢到后面。但它跳了一下,又向前奔了,穿过了四水塘,梭特维尔,大河堤,埃博夫街,在植物园前面第三次停下来。
“走呀!”那个更加发火的声音叫道。马车立刻又跑起来,它经过圣—塞维,居朗迪埃码头街,石磨码头街,又过了一次桥,走过练兵场广场,到了济贫院的花园后面。花园里一些穿黑色短外套的老人,沿着长满常春藤的碧绿的平台,在阳光里散步。车子又走上了布弗勒伊大街,跑过科舒瓦兹大街,接着经过整个里布德坡,一直跑到德维尔坡。它再往回走,这时没有明确方向,无目的地乱走。人们看到它走过圣—波尔,莱斯居尔,加尔冈坡,红水塘和快活林广场,然后是麻风病院街,铜器街,驶过圣—罗曼教堂,圣—维维安教堂,圣—马克鲁教堂,圣—尼凯斯教堂,海关,再是老矮塔楼,三烟斗,纪念公墓。车夫不时地从他的座位上对沿路的小酒馆失望地看几眼。他不明白是什么使车里的人不愿意停车。
有几次他试着想停一会儿,就立刻听见身后发出愤怒的叫声。于是他更加用力地鞭打那两匹全身是汗的瘦马,但是他也不管车子怎样颠簸,到处乱撞,因为他并不在乎这些了。他垂头丧气,又渴又累,又发愁,几乎要哭出来。在港口,在四轮大车和大桶中间,在街上,在有路程碑的拐角处,市民们都张大了惊讶的眼睛望着这件在外省少见的怪事:一辆马车,窗帘拉得紧紧的,一直奔跑不停,比坟墓还要和外界隔绝,好像一只海船那样摇摇晃晃。中午,到了田野里,强烈的阳光照到镀银的旧车灯上。立刻一只没有戴手套的手从黄色的小布窗帘下面伸出来,扔出一些撕碎的纸片,它们好似白蝴蝶一样随风飘散,又远远地落到开花的红车轴草的地里。后来,将近六点钟光景,马车在博瓦辛街区的一条小街里停下来了。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下了车子,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