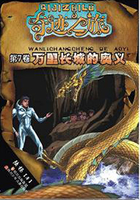莉莲笑了。“他确实爱过她。噢,我一开始必须装做对她很感兴趣。我甚至跟他一起哭。而从头到尾我却嫉妒得要死。现在我受不了。你只听听这件事怎么开始的好了。他们是在鲍镇一家疗养院认识的,他们两个都因为被认为害了结核病而运到那里去。事实上他们却都没有这个病。但是他们都以为自己病重了。他们都是异乡人,互不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那里的公园里的露台上,他们并排躺在各自的躺椅上;周围都是病人,他们躺在外面——整天,接受阳光治疗。由于他们相信注定早死,便自以为反正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什
么后果。他一直反复不断的讲,他们两人没有一个活得过一个月一而那是春天。她在那里完全独自一人。她的丈夫是法文教授,在英格兰。她离开他,到鲍镇来。她结婚六个月。他必须节衣缩食才能把她送到这里来。他天天给她写信。她是个出身很好的年轻女子——教养好——非常保守——非常害羞。但一到了那里——我不很清楚他对她究竟能有什么说的,但第三天她告诉他,虽然她睡在她丈夫身边,也属于他,但她不懂快乐两字是什么意思。”
“那他怎么说?”
“他握住她垂在椅子边的手,在上面长长的吻着。”
“当他对你说这个的时候,你怎么说?”
“我?噢,可怕!想想看!我发出一阵fourire〔控制不住的大笑〕。我收不住,一开始笑出来我就收不住了。倒并不是他讲的内容那么好笑——而是为了要鼓励他讲下去,必须表现的兴趣与惊吓。我怕我表现得太过分了。但事实上又是那么美,那么感人。你无法想像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是多么感动。他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父母自然是全不知道的。”
“你才是应当写小说的人。”
“Parbleu,moncher〔当然哪,亲爱的〕,如果我知道用哪一种语言写就好了!但究竟该用俄文,英文还是法文,我就无法决定了。好啦,第二天夜里他到他新朋友的房里,在那里教会了她——她的丈夫从没有教会的东西——我料想他是个能手。不过,由于他们相信活不了多久,他们自然没有做预防,而也自然,借着爱的滋润,过了不久以后,他们两个都身体好多了。当她发现她enceinte〔怀孕〕了的时候,两个人都恐慌得不得了。那是上个月。天已经开始热了。乡镇的夏天是让人受不了的。他们一起回巴黎。她丈夫以为她跟她父母一起——她父母在卢森堡附近开了一家膳宿学校——但是她不敢回他们那里。她的父母呢,则以为她还在乡镇;但用不了多久事情都会传出去。文桑一开始发誓不遗弃她,他提议跟她一起远走天涯——到哪里去都行——到美国去——到太平洋去。但他们没有钱。正是在这个时侯他遇见了你,开始赌。”
“这些事他一样也没告诉过我。”
“不管怎么样,不要让他知道我告诉了你他的事。”
她停下来,听了一会儿。
“我觉得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告诉我,在从鲍镇坐火车回巴黎的路上,他以为她要疯了。那时她才开始明白自己要有孩子了。她坐在他对面,车厢那一带只他们两个。整个上午她都没有对他说话,旅行的事完全由他一手包办——她一动不动——她似乎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似的。他握起她的手,但是她眼定定的直看前方,就好像她没有看到他似的,她的嘴唇却一直不停的动。他弯身向她。她在说:‘一个爱人!一个爱人!我有了一个爱人!’她一直用相同的声音反复同样的话,就好像这是她唯一记得的话似的。说真的,劳伯,当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笑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更叫人心疼的事。不过,我仍然感觉到,在他说这个的时候,他跟整个事情离得越来越远了。那就好像他的情感随着他说话的呼吸消散了;就好像他感谢我的情感可以让他将他的情感依靠在上面。”
“我不晓得如果你用俄文或英文会怎么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用法文说得太好了。”
“多谢。我自己也感觉到。一是在说了这个之后,他开始对我讲博物,我尽力说服他了,为他的爱情放弃他的事业是不智的。”
“换句话说,你劝他牺牲他的爱情。而你是不是有意取代呢?”
莉莲不说话。
“这一次,我想真的是他来了,”劳伯说下去,站起身。“他进来以前最后一句话。我父亲今晚死了。”
“啊!”她单单这样呼了一声。
“你没有想过要做巴萨望伯爵夫人吗,嗯?”
莉莲仰头大笑。
“噢,噢,我亲爱的朋友!我的问题是,我模模糊糊还记得我在英格兰的什么地方遗弃过一个丈夫。什么!我没有告诉过你?”
“我不记得。”
“你可以猜得到,照惯例,一个夫人总有个爵爷配的。”
巴萨望伯爵,由于从不大相信她的名衔属实,只是笑笑。她接着说下去:“是为了要掩盖你自己的生活,你才想到这个念头要向我提这件事。不行,我亲爱的朋友,不行啊。让我们保留现状吧。做朋友,呃?”她伸出手来,他吻了。
“啊!啊!我猜得一点不错文桑进屋来的时候喊道。“这个出卖朋友的人!他换了衣服!”
“不错,我答应过不换,为的是叫他自在一点劳伯说。“对不起,我亲爱的朋友,但是我突然想起我正在服丧。”
文桑的头抬得高高的,全身发散着胜利与欢乐的气息。他一进来,莉莲就跳起来。她上下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欢欣的冲向劳伯,开始在他背上拚命捶打,跳着,一边舞着,叫着(莉莲这样装孩子气的时候,相当叫我气恼)。
“他打赌输了!他打赌输了!”
“打赌什么?”文桑问。
“他赌你今晚又输。告诉我们!快!你赢了。赢多少?”
“我在五万的时候,鼓起了不起的勇气,还有这个了不起的道德离开了。”
莉莲发出一连串的欢呼。
“棒啊!棒啊!棒啊!”她叫着。然后她投过去抱住文桑的脖子。从头到脚,他感觉到她灼热的、柔软的、发着那奇异的檀香的身子贴着他,莉莲亲他的额、脸、唇,文桑勉强把自己挣脱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
“这里!把你垫给我的拿回去吧他说着,把五张拿给劳伯。
“不对劳伯回答。“现在你该还的是贵妇莉莲了。”他把钱递给她,她则丢在长沙发上。她在喘气。她走出去,到阳台上呼吸。这时是幽明的时刻,黑夜将尽,魔鬼要弃手而去了,屋外没有一丝声音。文桑坐在长沙发上。莉莲转向他: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她问,这是她第一次称他为“您”。
他双手撑住头,带着抽噎似的说:
“我不知道。”
莉莲走到他旁边,用手抚住他的前额,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又干又热。
“我们还是先干杯吧!”她说着,倒了三杯托凯。他们喝了,之后,她说:
“现在你们该走了。已经很晚,我累了。”她陪他们走到前室,然后,由于劳伯先走出去,她把一个金属的小东西塞进文桑手里。“跟他一起出去她小声道:“一刻钟以后回来。”
前室有一个仆人在打瞌睡。她摇他的胳膊,把他摇醒。
“领这两位先生下楼,”她说。
楼梯是黑的。不用说,如果用电灯,再简单不过,但她坚持她的客人一定要由仆人持灯带路出去。
仆人把一座大分枝烛台上的蜡烛点亮,高高的擎在手上,走在劳伯与文桑的前面下楼。劳伯的汽车在门口等他,仆人则关上门回去了。
“我想我可以走路回家。我需要运动运动来稳定一下神经,”当劳伯打开车门并做手势要文桑进去的时候,文桑这样说。
“你真的不要我送你回去?”劳伯突然抓住文桑握着的拳。“打开!开呀!让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文桑还有点纯真,他怕劳伯嫉妒。他的手松了,一枚小小的钥匙掉在人行道上,同时他脸红起来。劳伯立刻捡起,看了一看:大笑着还给文桑。
“原来如此!”他一边耸肩一边笑。在他要进车时,又转过身来,看着有点发呆地站在那里的文桑说:
“现在是星期四早晨了。告诉你弟弟,说我下午四点钟等他。”然后他不等文桑回答,就迅速关了车门。
汽车走了。文桑沿着码头走了几步,越过塞纳河,继续走,一直到了栏杆外的杜乐利区,他走到一个小池泉边,用手帕沾了水按在前额和太阳穴上。然后,他慢慢走向莉莲的房子。就让我们离开他吧——当他无声无息把那小钥匙伸进钥匙孔中,有魔鬼在有趣的看着他……
就正是在这个时候,洛拉,他昨天的情妇,终于在她阴沉的旅社小房间中经过了长久的哭泣哀伤之后睡着了。在向法国回航的船的甲板上,艾杜瓦在晨光下正重读她的信一她哀怨的信,向他求助的信。他祖国的溫柔海岸已经在望了——尽管在早晨的幽光里非得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望见。天上丝云全无,高特的神眼似乎在上面微笑。地平线业已睁开玫瑰眼帘。在巴黎,将会多么热!现在,该是回过来说柏纳的时候了。他在这里,在奥利维的床上刚刚醒来。
柏纳醒来
我们都是杂种;
那最可敬的,我称之为父亲的人
当我被打下印记的时辰人不知在何处。
莎士比亚:Cymbeline
柏纳做了个荒诞的梦。他不记得内容,他也不想记得,只想从里面解脱出来。他回到现实的世界,感觉到奥利维的身体沉重的压着他。当他们睡着的时候(至少柏纳是睡着了),他的朋友向他靠过来——而床太小,他无法保持多大的距离,他翻过了身,现在侧卧,柏纳感觉到奥利维温暖的呼吸搔着他的脖子。柏纳除了那一件白天的短衫外他并没有穿别的衣服;奥利维的一只胳膊横搭在他胸上,又压人又不得体。有一段时间柏纳不确定奥利维是不是真睡。他轻轻地把他挪开。他起身,而没有弄醒奥利维,穿好衣服,又在床上躺一躺。出门还太早,四点,夜幕刚退。再一个钟头的休息,再一个钟头的聚积力量来勇往直前的迎接今天。但他已经没有睡意了。柏纳看着透着微光的玻璃窗、小屋的灰墙和乔治在上面翻滚做梦的铁架床。
—眨眼以后他自己对自己说:“我就会出去迎向我的命运了。精彩的世界!冒险的人生!我命运的‘冒出’!种种惊人的未知数都在等着我!我不知道别人像不像我,但是我一醒,就会皁视那还在睡的人。奥利维,我的朋友,我不等跟你说再见就要走了。起来吧!勇敢的柏纳!时间已到!”
他用毛巾角沾了水擦脸,梳了头,穿上鞋,无声无息的走出屋子。终于出来了!
啊!那还没有被人呼吸过的晨间空气对于身体和灵魂是多么清新啊!使人充满了活力!柏纳沿着卢森堡公园的栏杆走到柏纳帕街,来到码头,越过塞纳河。他想到他最近才构想出来的新生活态度:“如果‘我’不做,谁做?如果我不现在做,什么时候做?”他想道:“了不起的事情!”他觉得他正在走向它们。当他一边走着的时候,他一边反复对自己说:“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他知道那是什么就好了!而同时他却知道他饿了,现在他在哈尔区。他口袋里有八个苏—一个都不多!他走进一家酒馆,拿了一个蛋卷和一杯咖啡,站在酒柜边吃喝起来。价钱是六个苏。他还剩下两个,他大大方方的留了一个在柜台
上,把另一个给了在垃圾桶翻东西的衣服破烂的小孩。慈善?虚张声势?那又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快乐得像个国王,他一无所有了——而全W界又都是他的!
“老天要叫我遇到的一切都在我预料之内他想。“如果午餐的时候它要给我一块漂漂亮亮的烤牛排,我就跟它成交。”——因为昨天晚上他没有吃晚饭就出来了。太阳已经升起很久。柏纳现在又回到码头。他觉得里外都是轻盈的。当他跑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在飞。他的思想敏捷的跳跃着。他想:
“生活里困难的是对同样的事情维持长久认真的态度。譬如说,我母亲对那个我一向称做是我父亲的人的爱——这件事我一直相信了十五年。昨天我还在相信。她,就不能够认真的对待她的爱情。我不晓得因为她把她的儿子生成一个私生子是叫我更卑视她或更尊敬她……但事实上,我对这些事情是不大理会的。人对他们的袓先的情感属于那种最好不要探得太深的事情。至于对古科德先生,那再简单不过——因为从我记得的时候开始,我就总是恨他的,不过我现在必须承认,我这样也并不怎么值得称赞——这是我惟一遗憾的事。想想看,如果我没有把那抽屉打开,我会一辈子都相信我对一个父亲怀着不自然的情感!知道了实情是多么轻松!但是,我并不是把抽屉打破的,我从没有想到要打开过它……再说还有别的原因促成我做这件事,那天叫人厌倦得要死。还有我的好奇心——费奈朗所说的‘要命的好奇心’,那一定是从我真正的父亲继承来的,因为普洛菲当杜一家人性格里连一个这种东西都没有。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比身为我母亲的丈夫的那位先生更没有好奇心了——除了他制造出来的孩子以外。我一定要以后再想他们——等我吃了饭以后……把一块大理石板从桌子上抬起来,看到下面有个抽屉,那当然和撬开锁不一样。我不是顽劣之徒。德秀斯在抬起石头的时候,一定也在我这种年纪。桌子上放的钟总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我不是要修钟,做梦也想不到要把石板抬起来……不常见的是在下面藏了武器或罪恶的情书。呸!重要的是我本来就该知道这些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那种奢侈的机会,叫鬼魂指示他秘密的,像哈姆雷特那样。哈姆雷特!人的观点随着自己是罪恶之子还是合法之子而不同,真是奇怪。这个,我也以后再想——等我吃过饭……我看了这些信,错吗?不错,如果我没有看,我才会懊悔!我会继续在无知、虚假与屈服中过下去。噢,为了自由的空气!噢,为了广阔的汪洋!‘柏纳!柏纳,你的惨绿青春……’像波修所说。把你的青春坐在那长凳上吧,柏纳。好一个美丽的早晨!真的有些时候太阳像吻着大地。如果我能够把自己抛开一些,真没问题我可以写诗。”当他在长凳上躺下来,他真把自己抛开了,以至熟睡起来。
莉莲与文桑
太阳,已经高悬天上,抚着文桑在宽阔的床上赤裸的脚,他躺在莉莲的身边。她坐起来看他,不晓得他已醒来,吃惊于他脸上忧虑的表情。
葛利菲夫人爱文桑是可能的,但她爱的是他的成功。文喿个子高,瘦长,英俊,但他不知如何举止,不知如何坐下,如何站起来。他的脸富于表情,但他头发梳得很糟。她最喜欢他的,是他智力的鲁莽与健全,毫无问题他受过高等教育,但她却认为他是没有教养的。凭着母亲与情妇的本能,她垂视着她的这个大男孩,把改造他视为她的任务。他是她的造物——她的雕像。她教他刷指甲,把头发分向一边,而不是向后拢,如此可以让他那老是被一绺头发盖住的额头白一点、轩昂一点。他平常打的那个现成的、小心的、不起眼的蝴蝶结,她也把它拿掉了,给他换上真正的、帅气的领带。葛利菲夫人爱文桑是毫无问题的了,但是当他沉默或她所谓的“闹情绪”的时候,她是受不了的。
她轻柔的把一根指头按住文桑的前额,就像要抹去一条皱纹似的——从他眉头开始的那两条深深的纵沟使他的脸看起来几乎是苦痛的。
“如果你要带给我的是懊恼、忧虑和悔恨,”她一边依向他,一边幽怨的说,“那最好你不要回来。”
文桑闭上眼睛,就像要把刺目的光亮关在外面。莉莲脸上的欢情使他目眩。
“你要把这个地方看成清真寺——进来以前把鞋子脱掉,免得把外面的泥土带进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文桑要用手捂住她的嘴,她则像顽皮的孩子那样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