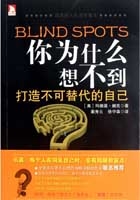他滑稽的小小个子加上一本正经的干幽默,使他成为一个能让人开心的人物,他诙谐的言谈、趣味的笑柄、以及突梯滑稽地阅读些幽默的文章,在这乡下地方每当有什么节庆场合时,几乎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节目了。
“哎,安东,我说呀,”有一个人说,说时他还在笑,“您老今天晚上可以给我们读一点什么了。好久好久您都没跟我们讲点什么了呢。别忘了您还欠我们施特茵那个故事,她怎么去上中学的经过您还没跟我们讲哩。”
“是了,是了,说给我们听吧!讲吧!讲吧,安东!”立即有几个声音附和着。
这位校长闭起了一只眼睛,带着微笑环视了一下四周,而当大家的喧闹声越大时那笑容也越扩大起来了。
“孩子们,好啦,好啦,既然这么说,”当那坐在火炉附近的妇女也跟着一起起哄请求时,他终于说,“要是没有人要讲点什么,我当然是不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的。没有让施特茵到中学去读书,这会让俺良心上觉得不安呢!”
“但是我们不该先唱首歌吗?”一个无礼的叫声从女孩子坐的板凳那边响起。那是漂亮的阿比侬的声音。她是一个二十岁的高大女孩子,浅黄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黑色锻带,胸前别着一朵艳丽的玫瑰,还束着一条中学生不可少的光亮皮带;她是牧师公馆里的仆人。
“好的,让我们先唱首歌吧伊曼纽表示同意。“唱首自己国家的歌吧!我相信在这些时日里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要唱哪一首呢?”
“千万勇士葬身海滨。”有个人提议。
“好,这首很适合;我们都记得怎么唱。阿比侬,你带头吧。”
那首歌一结束,房间即刻鸦雀无声。那些年轻人把手臂搁在桌上、坐好身子,女孩子们放下了她们手中编织的东西,或把它塞入她们围裙下的口袋里去,然后双手手指交叉着搁置于腿上,以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于听安东讲故事、读文章。
作为一个诵读者和吟诵者,他是杰出无匹的,只有山丁吉那位中学的老管理人还可以和他一比。但是后面这位,在讲述民间传说和流传于北欧的英勇故事之时,他自己也随之气喘咻咻、兴奋激动,并发出奇异的尖锐声音,几乎可说是声震屋瓦——那声音像战争时的号角那样在讲堂里回荡着,也像咒语般把神话中的巨人、侏儒,以及战神奥典的婢女维吉莉等人的鬼魂一一召来,幢幢出现于他们之前,他是讲得那么的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好像居住于爱思加的整个光辉灿烂的神族都真的在他们眼前出现了;相形之下,这位校长却着重于讲述一些发生于日常生活里的,平淡而寓有道德意味的故事,在当时成为大受欢迎、甚为风行的东西。他模拟故事里角色的举止动作——特别是那些喜剧人物的样子——十分地熟练老到,并且借他滑稽突梯的小小个子之助,而使他的人物模拟显得惟妙惟肖、栩栩传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经由这些诵读方法,他大有贡献于现代作家作品的介绍、推广,并且把过去盛行的浪漫诗歌逐出于这类夜晚集会场合之外,而以他所讲的那些取代之。伊曼纽起初试着想重新激起民众对那些诗歌的兴趣,但是他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过。那些古老的诗歌十分地生动有趣,小时候读它们曾带给他不少快乐的时光——他不能了解他的朋友对于欣赏那些诗歌为什么兴趣缺缺。但是随着他逐渐地深入生活,历经了其间的奋斗、挣扎,他开始看出来夜莺啦、小仙子和月光啦,这些无益的幻想故事,事实上是太过远离现今民众的思想、情感,而与现实脱节了。另外他也注意到,在异教的鬼神世界里,男女的爱情常为古代的诗人们所描述、颂赞。他们常描写一些大胆、不贞的行为以夸示女人身体的诱惑力……这一点屡次地为他所注意而深具印象。可能是由于同样的一种感觉而使众会友们对那些诗歌反应冷漠,觉得索然,谈论它们时感到不好意思,难于启口吧……而在那些现代作家的作品里,那些适度而真实的描写,本身就是出于小民老百姓的作家笔下的,尤其是在那些伟大的挪威作家反映社会的戏剧作品里,他们重温了自己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努力奋斗、喜怒哀乐的情景。在这些作品里他也发现到了道德的真诚、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望,举凡这些往往都震撼了会众们的心弦,使他们深受感动。
同一个夜晚,维林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店铺后面温暖舒适的小客厅里坐着。厅当中的桌子上面燃亮着一盏高脚、红纸灯罩的灯。女主人坐在沙发上打着毛线,那灯光柔美地流照于她身上;而维林则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把有靠臂的椅子里,大声地读着报。
铺子里完全寂静无声。里面的灯已把灯焰转小了,那灯悬吊于天花板,其下堆置了一些马梳、绳索之类的东西,因而发出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在最暗的一个角落、一大桶白兰地的后面,坐着那个幽灵般的小伙计。这一名小店员每二年或三年就要更换一次,届时都要到大都城里去找人来替补,但是换来换去结果找来的还是一个同样瘦巴巴的、怯怯懦懦像个鬼似的家伙,将近二十年来人们见到的都是同样冒冒失失、慌慌张张地在维林的店里横冲直闯的家伙。此刻他已经睡着了;他的头靠在墙上,嘴巴张得开开的,双手深深地插到他的口袋里面去,就好像他永远不必抽出来似的。
营业时间末了的几个小时,甚至打瞌睡做梦也没人来打扰他了。维林的铺子以往常是顾客众多、熙熙攘攘的;而现在连白天也大半不见人影。借着教区再分配的办法,斯奇倍莱那家火合作商店抢走了大半的生意,逐渐地只给他留下村里的穷人贫民几毛几文的买卖交易,做一点煤炭的生意,以及卖卖麦酒白兰地和巴伐利亚啤酒。
然而看起来这些坏年头好像没有严重地影响到维林或他的妻子,而使他们难于度日。
他自己——个子小小的,有个宽宽大大的头,一些黄色发髯——这几年反而胖了,面色红红润润的;当然啦,他的妻子在工作时不得不戴副眼镜了,但是她的脸上仍然保有那温柔和顺的表情,好像她也相信了她丈夫常称的“出自职业训练的优越”和“最后的战胜”这些说法,因而找到了宁静。
那份维林正在读的报是哥本哈根出的—份保守派的报纸’合对于首都发生的事钜细靡遗详尽的报道,很久以来就是人们最为喜爱的,并且也是这一对夫妇惟一的读物。由于小心防备政治风波之故,多年来他们一直不曾订阅报纸,只是请商业界的朋友把报纸充做包装纸暗中运来给他们。今天晚上特别读他们觉得很乐很开心的是,那报上报道了宫廷里所举行的一次盛大的舞会,冠盖满京华,而此会集首都的显赫高贵与富丽堂皇于一堂。维林每次总是用那种庄严、颤抖的声音来读这一类的文字,不学无文、识字不多的人常以此方式来显示他们对诗书文章的爱好、敬重之意,现在他逮住了机会,便尽量地驰骋他的抑扬顿挫、高声朗读的天才了。他把那些描写制服、制服上有几颗星、佩带什么勋章、仕女们所穿着的华丽礼服、耀眼夺目的珠光宝气,一连串的句子滔滔不绝地读着,读来有板有眼,津津有味。
“我们的皇后陛下一向是活活泼泼富有生气的,此刻看起来更是倍加地年轻,她身着一袭饰有花边的裙子,后面拖曳着一条华贵无比的淡紫色锦锻,有五码那么长,发上戴有猫眼石的饰物,和淡紫白色的鹭羽饰,”他朗读着。“赛盈,想想看吧,有五码那么长的一条淡紫色锦缎,要是我们只以平常那种阔幅,长十二码来计算——以,就以每码四十五克罗臬?来算吧,乖乖,这样光那块料子就要花掉五百四十克罗臬呢!”
维林夫人,脸颊侧倚在一支织针上,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眼光越过眼镜边缘的上方,仰视天花板,附和着她丈夫说:
——还有十五码的花边,每码二十五克罗臬总共要花掉三百七十五克罗臬。”
“那么合计起来总共要花掉九百十五克罗臬。”
“至少要,”
“光那块料子就要花这么多!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光彩夺目、华丽壮观!但是让我们再来读一点。‘皇太子妃殿下穿着蓝色的丝缎,裙上织有银色的百合——你听说过吗?银色的百合花?——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饰满钻石珠宝的后冠,玉颈和手臂上也佩戴了同样的宝石。她的一对耳环非常好看、非常动人,每边的耳环都饰有一颗钻石,有麻雀蛋那么大的!——赛盈,你听过这种事吗!像麻雀蛋那么大的钻石!这就好比说你的耳朵每一只都悬挂着一栋乡下房子,不,应该是说悬挂着整个的村子。那一定是一种奇妙惊人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说到这里他止嘴停住,抬起头来倾听。池塘的另一端传来笑闹嬉戏的声音,因为这时有一群女孩子唱着歌走过村子。
“我猜想今晚伦特士家的集会已经散了,”他说,望着墙壁上的钟。“再说也该是散会的时候了,都已过九点啦。好,让我们继续吧,我希望我们不会再被打扰了——”
就在这当儿店铺的门铃响了起来——铃声已破裂走调了。维林赶紧把他看的报纸合起来,准备好必要时可以瞬即塞入抽屉里去。
铺子里传来喃喃、咕哝的声音,还有酒瓶的叮叮当当;随后门铃乂响了一次,可是门还是关着没打开。
“伊利雅士!”维林把报纸持于背后,以他那洪亮的声音叫喊着。
那个小伙计鬼魂般的面孔在半开的门间出现了,披散着头发,睡眼惺忪。
“是什么人来?”
“啤酒桶席温和白兰地派尔……他们要一品脱酒。”
“好,给他们吧,今晚你可以打烊关门,去睡觉了。但是,孩子,可别忘了把烛火吹灭啊!——晚安!”
那门一关好,维林重新把那报纸摊出来,但是他刚一开始读,铺子的门铃又再度响起了,而这一次门哗啦啦地被拉开来,柜台的活动边板也被推举起来,一个人进到了店里面来了。维林慌得脸都白了,客厅的门被打开前他差点就来不及把报纸塞藏到抽屉里去。
“唉,是你。”他说,放松地喘了一口大气,因为他看到进来的人是爱格勃勒,他整个宽宽大大的身体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我们没想到你会光临……在夜里这个时候出门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噢,刚去看一名患者,”爱格勃勒喃喃地说,一面游目四顾想找个角落放下他的帽子和拐杖。
“这天气坏透了!简直讨厌得要命的鬼天气!这种天气不适合在外奔波的。那种泥泞难行,不适合踏入高门大户人家的屋子里的。但是我想我还是进来一下再走吧。”
“爱格勃勒,你来看我们太好了,”维林太太说,眼光含着警告意味地瞪了她先生一眼,因为他对这个不速之客的闯入心里很不高兴,而且也不加以掩饰——“你知道我们如今是变得很孤单了,我们总是很高兴见到你的。你进来时我们还正谈着你呢,坐下来吧,告诉我们在这种坏气候里你们一家子的近况可好?”
爱格勃勒好像没听到这话,只是在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副愁闷、心不在焉的样子,喃喃自语地咒骂着坏天气,一边伸手到右侧的裤带里神经质地摸索着,好像他正想从那里面找什么东西似的。
最后他终于把手拉了出来,把一枚二克罗臬的铜板掷在桌上。
“维林,你说怎样,你出热开水和雪茄,我出白兰地。我想,像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需要一点猛烈的东西。”
那位店铺老板和他的妻子交换了一下询问的眼光,跟着片刻间大家都没讲话。然后维林太太站起身来,进厨房里去,而维林灵巧地扭转了一下身体,一手把那个铜板抓起,瞬间又转交到另一手,紧跟着塞到他的钱袋里去了。
爱格勃勒的眼睛紧看着那个铜板的下落,露着依依难舍的目光,一直到维林把那个放钱的皮袋子关起来才作罢。然后他默然无语地望着地面。
“啊,老友,你现在过得怎样呢?”维林说,倾身往前表示友善地往爱格勃勒的膝上拍了一下。
“我过得怎样?”那位兽医冷不防动了一下,坐直了身体,好像不想给对方触及到似的,一边反问着。“当然啦,情况很讨厌!不然你说应该怎样?”
“哎呀,我们做生意的也有我们自己的烦恼。现在无论哪里价钱都下跌……事情将会演变成怎样呢?前几天我才跟我太太说,现在买什么东西都要付现款,这好讨厌、好叫人受不了啊。朋友有困难我们得乐意解囊相助,一个好顾客临时手头不便,我们得方便他一下,让他度过难关——以言辞相慰或用实际行动帮忙帮忙。可是当一个人连自己都差不多自身难保时,你说他能够怎样呢?此刻我不知道这一季的结账日我要怎么拖过去呢。在这年龄,回想二十年来我兢兢业业、诚实公道,如今却是此等光景,真是狼狈难堪啊。我是完了,彻底地完了!”
对爱格勃勒来说这种话并不新鲜,他胡须丛后的嘴巴里不晓得咕哝着些什么,眼里露着不耐烦,频频地看着厨房的门。
终于维林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碟子,出来了;爱格勃勒迫不及待地抓了一个杯子,只倒进去刚好盖满杯底的一点水,便即斟入白兰地满满的一杯,也不相互碰杯、或举杯互祝健康,就以一只颤抖着的手把杯送到嘴唇,一饮就干了大半杯,这时维林也把雪茄拿来给他了,喝过酒他随即咬掉雪茄末端,就着桌上的灯光把它点燃了,吞吐了几口,然后重又把自己掷回椅子里,双手交叉于前——这是他最喜欢的坐姿。
“啊,”他迸出话来了,那酒一下子就使他变得能言健谈。“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新鲜事儿?让我想想看!”维林回答说,搅动着他的混合饮料。“噢,最近的一件事是,今天教区会议举行了一次集会。”
“你说的哪是新鲜事?一点都不鲜!我觉得他们每天都开一次会……当他们一天没有开两次的时候!农夫们的畜牲在这一段日子里是没有什么事好忙的。他们把牛奶送到产制奶品的合作农场去,猪运到共同屠宰场去,所以他们就有时间去做一些自以为是了不起的事了。说真的,往昔的日子可不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老友,你说是不是,呃?”
“我想,那是选举委员会的关系。”
“选举委员会!”爱格勃勒的话愤然迸出,“我们又要被拖下水去搞另一个政治闹剧吗?我们上次在这里开会到现在还不到——个礼拜呢!事情不正是如我所说的那样吗?”他继续下去,咬牙切齿、拳头紧握着。“想想那些‘蠢东西’在举国上下搞出来的一切事情,简直会叫人吐血气死。他们伤天害理还不够呢——是的,我说他们把善良的老丹麦人,最后的一些和蔼、快乐的样子都杀死了……除此之外,你还得乖乖地坐在那里听他们那些该死的驴叫狗吠。要是老戴瑞克·雅可布生碰到这种事,他会怎么说呢?维林,你还记得老戴吗?啊,他是个不赖的老公子哥儿。在他的圣诞大宴会里,他供应那老式的烤猪,单一支腿就有四十二磅重,配上红甘蓝菜、脆饼、老圣诞麦酒,接着又送上最棒的咖啡拌集饮料,来安慰人们,让他们忘却生活里所遭遇的种种烦恼与失望。然后是忏悔节,人们会有连续五个夜晚的通宵作乐!哎哎,那才是叫人想过活的好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