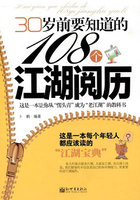空心树的洞口朝着东方,蟾蜍早早地醒来了。这一半是因为明亮的阳光从外面透射进来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一半是因为他的脚趾冰冷。这种感觉让他梦到自己躺在自家的床上,躺在那间有着都铎式窗户的漂亮房子里,可是他床上的被子等物件全都起身跑掉了,它们嘀嘀咕咕地抱怨天气寒冷得无法忍受,纷纷跑到楼下厨房里烤火去了;他也跟了出去,光着脚踩在漫长而冰冷的石板通道上,追赶着,与他们争辩着,要他们千万讲点道理。要不是因为他在铺上稻草的石板上睡过几个星期,说不定醒得更早呢。他差不多完全忘记了把盖着厚厚的毛毯拉到下巴处睡觉的那种亲切感觉。
他坐起身来,揉揉眼睛,搓搓麻木的脚趾,有好一会儿他都是在寻思着自己到底身处何处,眼睛向四周张望,寻找着那熟悉的石墙和带有铁栏杆的窗户。然后,怦地一阵心跳,他把事情一一回忆起来了:越狱、逃跑、被追捕;同时他也想起了那种最大的最好的事情——他自由了!
自由!单是这个词、这个念头就抵得上五十条毛毯。他一想到外面的欢乐世界,就从头到脚暖融融的。外面的那个世界正在等待着他凯旋归来,随时准备为他殷勤效劳,正急切地想去帮助他、陪伴他,就像霉运降临之前的昔日美好时光一样。他抖了抖身子,用手指梳理掉身上的干草枯叶,整理好行装仪容,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早晨舒适的阳光中。虽然寒冷,可是他信心十足;虽然饥饿,可是充满希望。经过一夜的睡觉和休整,昨天的紧张和恐惧已经被真诚宜人的阳光驱散。
那个初夏的早晨,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他从缀满露珠的树林穿过,四周孤寂而宁静:林边的绿色田野似乎也属于他,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走到小路上,一切也都笼罩在孤独的气氛之中,小路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狗,急不可耐地寻找着同伴。而蟾蜍在寻找的却是会说话的东西,要能明确地告诉他该走哪条路才对。当你心情轻松、问心无愧、满口袋钞票,并且没有人在乡间四处搜捕,要把你再投进监狱的时候,管它走在哪条路上,管它顺着路标走到哪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可是,讲究实际的蟾蜍却十分在乎,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可是这条小路一声不吭、毫无用处,他恨不得把它一脚踢开。
不一会儿,沉静的乡间小路与一个羞怯的小弟弟运河相遇了,运河牵着小路的手,信心十足地一同从容漫步,只是它与小路一样,也是三缄其口,不与陌生人交谈。“去它们的,”蟾蜍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它们一定都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至于究竟是什么地方,你就无法弄清楚了,蟾蜍老兄”。就这样,他沿着水边耐心地往前走。
运河的拐弯处,一匹马拖着沉重的步伐走来,头向前倾,神情焦虑,套在身上的轭具上还扯着一根粗壮的长绳。绳子随着马的脚步往下掉落,远处的一端还在不断往下滴水。蟾蜍忙给马让路,站在那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一艘驳船从宁静的水面上驶过来,扁平的船头激起一片欢快的旋涡。船舷涂着鲜亮的彩漆,正好与纤道一般高;船上只有一个女人,高高大大的,戴着一顶亚麻布太阳帽,一只壮实的胳膊搁在舵柄上。
“早上好,太太!”她边把船朝蟾蜍这边靠过来,一边向他打招呼。
“不错,太太!”蟾蜍礼貌地答道,边说边沿着纤道与她并肩走着。“我敢说,对于那些不像我遇到令人头疼的麻烦的人来说,的确不错。您瞧,我女儿出嫁了,她托人带信叫我尽快赶到她那儿去,我就出门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太太,您要是也有孩子,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的。我丢下所有的活计都不管——我是干洗衣这一行的,您知道,太太——把一群小不点儿也留在家里,让他们自己管自己。这帮家伙可是最调皮捣蛋的了。现在我的钱弄丢了,路也迷了。至于说我那出了嫁的女儿到底可能出什么事,唉,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啊,太太。”
“您女儿大概住在哪一带,太太?”船妇问道。
“她住的地方离小河不远,”蟾蜍回答说,“住在一个叫蟾宫的漂亮房子附近。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说不定您还听说过呢”。
“蟾宫?嗨,我正好要去那一带。”船妇接过话说,“这条运河再往前面几英里就流进小河了,正好在蟾宫上游不远处。到了那儿,你走几脚就到了。那您就上船吧,我捎您一程。”
船妇把船划近岸边,蟾蜍轻快地踏上船,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嘴里不停地说着谦恭的感谢话,心里却在想:“蟾蜍的运气又来了!我总是能够时来运转逢凶化吉!”
“您说您是干洗衣这一行的,太太?”当船平稳离岸时,船妇礼貌地问了一句,“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我敢说,您这一行当也很不错。”
“算得上是全国最好的行当了,”蟾蜍信口开河地说,“所有贵人都来找我,他们很相信我,就算有人给钱他们都不愿意去找别人。您瞧,我很懂行,全部活计都是我自已料理,洗衣、熨烫、上浆、为绅士们缝制配晚礼服穿的精美衬衣——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着完成的。”
“可是,你肯定不会亲手去做所有这些活计吧,太太?”船妇顿时肃然起敬。
“噢,我手下还有些姑娘,”蟾蜍轻松地说道,“大约有二十个左右吧,一直都忙个不停。不过,您是了解姑娘的性情的,太太。淘气的小丫头辫子!我就是这么叫她们的”。
“噢,我也是这么叫的。”船妇兴致倍增。“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把她们调教好了,就是那些邋遢的懒姑娘们!你喜欢洗衣服吗?”
“很喜欢,”蟾蜍说,“喜欢得有点儿过分了。只要我双手往洗衣盆里一放,嗬,别提有多快活了。说起来,这事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易如反掌!我敢说,太太,这才是真正的乐趣!”
“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船妇想了想,说道:“我俩真的都有好运气!”
“哎,你这话怎么讲?”蟾蜍紧张地问道。
“哦,瞧我,”船妇答道,“我——也喜欢洗衣服,跟你一样。而且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全都得我自己干,当然还得像现在这样四处奔波。可是眼下,我丈夫那家伙逃避自己的工作,把驳船交给了我,弄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的活儿。按理说,他现在应该是在这儿的,要么划船,要么看守马——好在是那匹马还算聪明,能自己照顾自己。可是他偏不,他竟然带着狗出去,说是要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在哪里逮只兔子作午餐。他说他会在下一道水闸处赶上我。好呵,或许会——不过,只要他带着狗出去,我就不相信他了,因为那狗比他更糟糕。可是这样一来,我该拿要洗的衣服怎么办呢?”
“哦,别把洗衣服的事放在心上,”蟾蜍说道,他并不喜欢这个话题。“试着想想那兔子吧!我敢肯定会是一只美味小肥兔。有洋葱吗?”
“除了洗衣服,我可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什么事情了。”船妇说道,“我纳闷着,你面前有这么叫人高兴的光景,怎么还能去谈论什么兔子。瞧,在船舱角落还有一堆衣服要洗呢。我们这一路上,要是您能把那一两件最急需洗的衣服——在您这样一位女士面前我不敢多说,您一眼就会看出来的——拿去在盆里洗干净,嗬,那将是您刚才所说的最大的乐趣,也是实实在在地帮了我一把。您会看见旁边的洗衣盆、肥皂,炉上烧着一壶水,还有一只水桶可以用来从运河里提水。那样一来,我就会确定您是开开心心的,而不是闲坐在那里看风景,一个劲儿地打呵欠,把头都要打掉了。”
蟾蜍一听,吓坏了,连忙说:“哎,您还是让我来掌舵吧!这样您就可以爱怎么洗衣服就怎么洗了。搞不好我会弄坏了您的衣服,或者做得没有您想的那么好。我更习惯洗的还是男士衣服,那才是我的专长。”
“让你来掌舵?”船妇笑着说,“要划好驳船得要好好练习呢。再说,这活儿很枯燥,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开心一些。您还是干您喜欢的洗衣活,我还是做我熟悉的掌舵工吧!您千万不要让我失去一次款待您的机会。”
蟾蜍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东看看西瞧瞧,想夺路而逃,可是船离岸很远,根本不可能跳上岸去,只好悻悻地认命了。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心想:“不就是洗衣服么?我想这是傻子都会的事情。”
他走进船舱取出盆子、肥皂和其它要用的物件,胡乱拣了几件衣服,努力回忆着以前从洗衣房的窗户里不经意间看到的情景,模仿着洗起衣服来。
漫长的半小时过去了。时间每过一分钟,蟾蜍心里就多一分生气。他对衣服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对它们不利,不能让它们高兴。他试着哄逗、轻拍、甚至猛砸,无论怎样,它们都从盆子里回头冲着他笑,仍然不见悔改,以自己的原罪为乐。他也曾紧张地扭头看了那船妇一两次,只是她好像一直都盯着前方,专心操舵。他感到背疼得厉害,爪子都起皱纹了,这着实让他惊愕。他的爪子一直是他的骄傲啊!他压低嗓子轻声咕哝了几句,这些话是那些洗衣婆和蟾蜍们都说不出口的。他手中的肥皂再次掉了下来——这是第五十次了。
一阵响亮的笑声响起,他不由得直起身子,四处观望,只见那船妇仰着身子肆无忌惮地大笑着,笑得眼泪都顺着脸颊直流淌。
“我一直都在观察着你,”她喘着气说,“从你说话的那副自负模样,我早就看出你一定是个骗子。好一个洗衣婆!我敢说,你这一辈子连一块洗碗布都没有洗过。”
蟾蜍先是强忍着性子,后来再也无法憋住了,一阵狂怒疾风暴雨般地冲破了一切禁锢。
“你这个粗野下贱的肥船妇,竟然敢对上等人那样讲话!”他大声叫嚷道,“我告诉你,我是蟾蜍,一个著名的、深受尊敬的杰出的蟾蜍。或许我眼下处境不妙,但也决不能被一个船妇嘲笑!”
船妇走到他的身边,用犀利的目光往帽子下面仔细端详了一番,大叫道:“啊,原来是这样!哦,我真没有想到。竟然是一只肮脏恶心的蟾蜍!还是在我漂亮干净的船上!现在,我可不能允许这事继续下去了。”
她放下舵柄,猛地伸出一只肤色深一块浅一块的胳膊,一把抓住了蟾蜍的一条前腿,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一条后腿,他的整个世界顿时颠倒了过来:驳船像是在天上轻轻掠过,风在耳边呼啸而过。蟾蜍发现自己在空中飞,一边飞一边旋转着。
只听得扑通一声,蟾蜍掉进了水里。河水冰冷难忍,不过,这仍不足以驱除他的傲气,也不足以浇息他的怒火。他扑腾着浮出水面,抹掉蒙住眼睛的浮萍,一眼看见那胖船妇站在远去的驳船尾部回头看着他大笑。蟾蜍呛了几口水,连声咳嗽,心里发誓一定要对她还以颜色。
他挣扎着游向河边,可是身上的棉衣极大地阻碍着他的努力。等到他终于碰到了河边,却发现没有人帮忙的时候独自爬上那陡峭的堤岸的确不易,不得已,他休息了两分钟,调整一下呼吸,然后把湿漉漉的棉衣下摆往胳膊上一搭,撒开两腿拼命追赶驳船。愤怒快使他发疯,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复仇。
当他赶上驳船时,那船妇还在大笑。“还是把你自己丢进绞干机去吧,洗衣婆。”她大声喊道,“再用熨斗烫一烫脸,弄出一些褶皱来,这样你就可以变成一只体面的蟾蜍了。”
蟾蜍没有歇脚回敬那船妇,虽说他已经想好了几句可说的话,可是他渴望的不是空洞的毫无价值的口头胜利,而是实质性的复仇。他看到前面就有他要的东西。他飞奔着赶上前面的马,解开纤绳扔到一旁,然后纵身跳上马背,双脚在马腹猛的一踢,策马飞奔。他骑着骏马离开纤道,拐进一条满是车辙的小道,直向旷野奔驰。他回头一看,那驳船在运河对岸调转船头,船妇挥舞着大声叫喊着:“停下!别跑!别跑!”
“我以前听过这样的歌!”蟾蜍大笑着说道,一面继续策马向前狂奔而去。
那匹牵引驳船的马不能承受长久的疾驰,不久就放慢速度变成了小跑,再后来又从小跑变成了漫步,不过蟾蜍对这已经十分满意了。他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在走,而驳船却没有。一想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他的心情又平和下来。他踌躇满志地骑着马在阳光里静静地慢跑,时而下小径时而上马路,悠然自得。他还极力让自己忘记掉从上一次饱餐到现在到底过了多长时间。不知不觉中,运河远远地被抛在了身后。
他和马一路走了好几英里。当马停下脚步、低着头开始啃食青草的时候,蟾蜍在这灼热的阳光下也开始感到昏昏欲睡,差点儿从马背上掉下来了。还好他醒来的正是时候,赶紧抓牢。他抬眼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骑马走在一片宽阔的公地。上面点缀着一丛丛荆豆和黑莓,一望无际。距他不远处停着一辆脏兮兮的大篷车,旁边有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倒放的木桶上,一个劲儿地抽着烟,两眼呆呆地望着前方的旷野。身旁燃着一堆柴火,火上吊着一只铁罐,里面发出咕咚嘎吱的声响,还飘出一缕缕朦朦胧胧的蒸汽,让人闻后浮想不断。还有那些气味——温馨、浓郁、各种各样的气味——交织混合,最后搅成一种兼蓄并容的气味,芬芳馥丽、近乎完美,就像是自然女神在她的孩子们面前显灵。那是真正的女神、一个充满了怜悯和抚慰的母亲。蟾蜍这时才深深地意识到了他以前还从来没有体味什么是真正的饥饿。今天早些时候他所感受到的不过是些微的不适,而此刻,他无疑正在经受真正的饥饿。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否则对人或对事都会产生麻烦。他仔细注视着那个吉卜赛人;脑海里模模糊糊地盘算着怎么对付他更容易些;是与他大打出手还是诱他上当呢?于是他坐了下来,鼻子不停地吸着香气,眼睛看着吉卜赛人;那吉卜赛人坐在那里抽烟,也看着他。
不一会儿,吉卜赛人从口中取出烟斗,漫不经心地问:“想要卖那匹马吗?”
蟾蜍完全惊呆了。他不知道吉卜赛人喜欢买马,而且决不错过一个机会;他还真没想到过大篷车常年移动,需要马匹牵引;也没想到能够把这匹马变成现金。此刻,他最需要的是现钱和饱餐,这位吉卜赛人的建议似乎为他得到两样急需的东西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