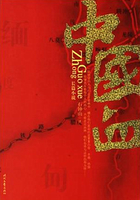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得,”他暗自想到,“我这趟来做了个糊涂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有多大影响;除此以外,还得糟蹋我的衣服帽子。真应该呆个角落啃我的法律,只图当个铁面法官。要体体面面地到交际场中混,得有双轮马车,擦得锃亮的靴子,必不可少的行头,还有金链子,早上戴六法郎的麂皮白手套,晚上一定要戴黄手套;交际场我去得了吗?高老头个老怪物,去你的吧!”
走到临街的大门口,一个马车夫驾着辆出租马车,大概才送过新郎新娘,正想瞒着东家跑几趟外快;看见欧也纳没有雨伞,穿着黑外套、白坎肩,又是黄手套,擦过油的靴子,便向他招招手。欧也纳憋着一肚子无名火,就像个掉进大窟窿里的年轻人,昏了头似的继续往里钻,以为可以找到幸运的出路。他朝马车夫点头答应了;也不管口袋里的钱不过二十二个苏,径自上了车。车厢里零零落落散着菊花和铜丝,说明果然坐过新人。
“先生去哪儿?”车夫问,他早已脱下白手套。
“也罢!”欧也纳私下想,“既然我往里钻,总得给我派点用场吧!”便高声回答,“鲍赛昂府。”
“哪一个鲍赛昂府?”马车夫说。
一句妙语,顿时把欧也纳问住了。初出茅庐的帅哥不知道有两个鲍赛昂府,也闹不清把他置之脑后的亲戚有那么多。
“德·鲍赛昂子爵,街名是……”
“格勒奈尔街,”车夫侧了侧脑袋,接过话头说道。“您知道,还有德·鲍赛昂伯爵和侯爵的府第,在圣多米尼克街。”他边说边掀起踏脚板。
“我知道。”欧也纳板着脸应声说道。“今天大家都嘲弄我!”他说着,把帽子往前座垫子上一甩。“这样出来闹一场,我花的钱就像国王的赎金。可是至少,我去拜访我那所谓的表姐,就有了十足的贵族排场。高老头已经害我起码花了十法郎,这个老混蛋!真的,我要把今天遇到的事儿,讲给德·鲍赛昂夫人听,没准会引她发笑呢。那秃尾巴老耗子同那美女勾勾搭搭,她也许知道其中的内情。那无耻女人的身价高得我吃不消,与其碰她的钉子,还不如去讨好我表姐。漂亮的子爵夫人,光姓氏就有那么大的威力,那她本人的分量该有多重呀?咱们还是走上层的门路吧。人要打天上的主意,就该看准上帝下手!”
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上面的话可见一斑。他看着纷纷雨景,恢复了些镇静和自信。他思忖道,本月份仅剩的那些五法郎面值钱币,倘若忍痛掷出两枚,也是花得值,毕竟保住了衣服鞋帽。只听马车夫大喝一声:劳驾,请开门!他禁不住得意地晃了晃。一个穿镶金大红制服的门丁,把公馆大门开得格格直响,拉斯蒂涅心满意足,看着马车穿过门洞,绕进院子,在台阶的挑棚下停住。身着红边蓝大褂的马车夫,过来放下踏脚板。欧也纳下车时,听见廊下传来忍俊不禁的笑声。三四个仆人早就在拿这辆俗不可耐的送嫁娘的马车打哈哈了。大学生听见他们的笑声,把这辆车跟人家的一比,顿时恍然大悟:那是一辆巴黎最华丽的轿车,套着两匹骏马,耳边插着玫瑰花,咬着嚼子,马车夫头发扑着粉,打着领带,用缰绳勒住马,生怕马会脱缰而跑。昂坦道区德·雷斯托夫人院里,停着一个二十六岁男子的精致双轮车;圣日耳曼区待命的,又是一位大老爷的豪华仪仗,一副三万法郎还买不下来的车马。
“什么人在这儿呢?”欧也纳心里想到;虽然迟了一点,到底还是明白了,没给人缠住的女子,在巴黎实在是难得一遇,要征服一位那样的女王,非得付出比鲜血还要高的代价。“见鬼!表姐说不定也有她的马克西姆。”
他垂头丧气,移步走上台阶。玻璃门迎着他打开了;眼前的仆人,个个一本正经,就像被人抽打的驴子。他上次参加的德·鲍赛昂公馆聚会,是在楼下大厅举行的。他在接到请柬之后,参加舞会之前,来不及拜访表姐,因而还没进过德·鲍赛昂夫人的上房;如今就要头一回领略精美绝伦的环境了;别出心裁的布置,能反映出一位贵妇的心态和情趣。他有德·雷斯托夫人的客厅以资比较,此时的研究也就更有意思了。午后四点半,子爵夫人可以见客了;再早五分钟,就连自家表弟也不会见的。对巴黎的繁文字节一窍不通的欧也纳,顺着一道金漆栏杆大楼梯往上走,白色梯级上铺着红地毯,旁边摆满鲜花;接着进入德·鲍赛昂夫人的屋子。天天晚上,巴黎沙龙里都在交头接耳,流传着种种故事,一天一个样,其中就有这位夫人的传闻,欧也纳却一无所知。
三年以来,子爵夫人和葡萄牙一位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德·阿瞿达—平托侯爵过从甚密。那种堂堂正正的交情,对当事人真是兴味浓厚,受不了第三者在场。因此,连德·鲍赛昂子爵也在人前以身作则;不管心里是否情愿,总尊重这蹊跷的关系。这两人结交之初,凡是下午两点来拜访子爵夫人的宾客,总会见到德·阿瞿达—平托侯爵。德·鲍赛昂夫人不能闭门谢客,那样就有失体统了,可是对客人总是爱理不理,目不转睛地老瞧着墙壁上方的嵌线,结果大家都明白了,自己当时于她是多么不便。直到巴黎城里知道了,两点至四点之间去见德·鲍赛昂夫人会打搅她,她才得到彻底的清静。她上滑稽剧院或者歌剧院,虽是由德·鲍赛昂和德·阿瞿达—平托两位先生陪同;可老于世故的德·鲍赛昂先生,把太太和葡萄牙人安顿好之后,就借故走开。最近,德·阿瞿达先生要结婚了。女方是罗什菲德家的一位小姐。整个上流社会里只有一个人还不知情,这个人就是德·鲍赛昂夫人。有几个女朋友向她约略提起过;她只是一笑了之,以为她们眼红她的幸福,想破坏。可是教堂的结婚公示马上就要发布了。这位葡萄牙美男子,虽说是来向子爵夫人宣布婚事的,却又不敢吐出一个字来。为什么?因为天下的难事,大概莫过于对一个女子下这样的最后通牒了。有些男人觉得在决斗场上给人用剑直指胸膛倒还好受,不像一个哭哭啼啼了两小时,再寻死觅活要闻解药的女子难于应付。德·阿瞿达—平托先生此时如坐针毡,想一走了之,心里思忖,这消息德·鲍赛昂夫人迟早会知道,他可以给她写信;男女之间一刀两断的手续,写信总比口头好办。这时子爵夫人的内侍通报,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来访,德·阿瞿达—平托侯爵听了乐得一愣。要知道,一个动了真情的女人,固然善于变着法子寻欢作乐,但却更加机敏入微,易生疑窦。一朝到了被人抛弃的关头,她对于人家一个身体反应的意义,能够一猜就中,其速度比维吉尔笔下的骏马嗅到远处传来的发情气息还快[23]。因此可以想见,德·鲍赛昂夫人果然一眼捕捉到了那不由自主的反应,虽然细微,却直露得可怕。欧也纳有所不知,在巴黎绝不可贸然去任何人家中,除非事先从这家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丈夫、妻子或子女的底细,免得捅出娄子难以收拾,应了波兰俗语形象的说法,要用五牛套车!大概是说,才能把你从泥淖的困境中拉出来。谈话中出这种乱子,在法国还没有字眼去指称,因为飞短流长会广而告之,人们认为大抵是不会出的。欧也纳在德·雷斯托夫人那里趟了泥淖,主人也不给时间让他五牛套车,此后也只有他这个牛倌,才会重蹈覆辙闯到鲍赛昂夫人府上。不过,他先前是严重地搅扰了德·雷斯托夫人和德·特拉伊先生,现在却是替德·阿瞿达先生解了围。
“再见。”葡萄牙人说着,连忙走到门边,就在这时,欧也纳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客厅,以灰色和粉红为基调,豪华之中尽显高雅。
“那就晚上见,”德·鲍赛昂夫人说着,扭过头来朝侯爵望了一眼,“咱们不是要上滑稽剧院吗?”
“我去不了啦。”他握住门钮说道。
德·鲍赛昂夫人站起身子,叫他回到自己身旁,根本没在意欧也纳;欧也纳站在那里,给富丽堂皇熠熠生辉的陈设弄得眼花缭乱,以为进了天方夜谭的世界;他面对这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女人,觉得无地自容。子爵夫人伸出右手食指,用优美的手势朝侯爵指着自己面前的地方。那手势具有情感上不容分说的力量,侯爵只好松开门钮折了回来。欧也纳不无羡慕地望着他。
“这就是乘轿车的人了!”他私下想。“难道非得要骏马健仆,腰缠万贯,才能博得巴黎女子的青睐吗?”奢华像魔鬼似的啮啃他的心,获取的热望攫住了他,对金钱的渴求使他喉干舌燥。本季度他还有一百三十法郎;而父亲、母亲、兄弟们、妹妹们,还有姑母,统共每月开销还不到两百法郎。他把自己的境况和理想中的目标很快地比较了一下,不由得心中一惊。
“为什么,”子爵夫人笑着问,“您不能上意大利剧院呢?”
“有事儿!英国大使今晚请客。”
“您可以先走一步啊。”
一个男人欺骗起来,必然会谎话连篇。德·阿瞿达先生笑着说:“您一定要我这样?”
“当然啦。”
“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嘛。”他接口说道,丢出的那种媚眼,换了别的女人都会放下心来。他抓起子爵夫人的手,吻了吻就走了。
欧也纳用手理了理头发,扭扭捏捏预备行礼,以为德·鲍赛昂夫人这就要想到他了;不料她突然冲过去,奔入回廊跑到窗前,望着德·阿瞿达先生上车;她侧耳细听他怎么吩咐,只听见跟班的给车夫传过话道:“上德·罗什菲德先生府上。”这句话,加上德·阿瞿达钻进车里的样子,对这个女人不啻是闪电和雷击;她回来时吓得心惊肉跳。上流社会最可怕的祸事莫过于此。子爵夫人回到卧室,坐到桌前取过一张精美的纸,写到:
既然您是在罗什菲德家吃饭,而不是在英国使馆,那就得给我一个说法。我等着您。
有几个字母因手发抖而写走了样,她又描了描,落款签了个C,代替全名克莱尔·德·勃艮第;然后拉铃叫人。
“雅克,”她吩咐闻声而至的内侍,“您七点半上德·罗什菲德公馆,求见德·阿瞿达侯爵。侯爵先生在的话,把这字条交给他,不必等回音;要是不在,原信带回给我。”
“客厅有人等着子爵夫人。”
“噢!对了。”她边说边推门。
欧也纳已经开始觉得很不自在了,这时终于看到了子爵夫人;子爵夫人对他说话了,情绪激动的语气又拨动了他的心弦:“对不起,先生,刚才我要写个字条,现在一心奉陪。”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些什么,因为她心里想的是:“哦!他想娶德·罗什菲德小姐。不过,他真有自由身吗?今天晚上这门婚事就得吹掉,否则我……可明天就尘埃落定了。”
“表姐……”欧也纳应声开口。
“嗯?”子爵夫人边说边扫了他一眼,傲慢的目光让大学生凉了半截。
欧也纳听出了这声“嗯”的意思。这三个小时他长了不少见识,心里早已有了戒心。
“夫人,”他红着脸改口道。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请原谅我,我太需要靠山了,沾点儿亲总归是好事。”
德·鲍赛昂夫人微微一笑,却笑得很凄凉:她已经感觉到厄运在她身边步步逼近了。
“您要是知道我家的处境,”他接着说,“就一定会做个神话中的仙女,乐于替子民排忧解难了。”
“那么表弟,”她笑道,“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怎么说呢?顺着一层久已失去联系的亲戚关系高攀上您,已是万幸了。您使我心慌意乱,简直想不起要来跟您说什么了。您是我在巴黎惟一认识的人。噢!我是想找您讨教的,请您接受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吧,我愿绕在您的裙下,为您出生入死。”
“您会为我杀个人么?”
“杀两个都行。”欧也纳回答。
“孩子!对,您是个孩子,”她忍住眼泪说道,“您才会爱得真诚,您呀!”
“喔!”他说着点了点头。
子爵夫人听了如此豪爽的回答,立刻对大学生关切起来。这个南方青年正在实施他的第一步打算。从德·雷斯托夫人的蓝色客厅,到德·鲍赛昂夫人的粉红客厅,他学完了三年的巴黎法典。这部法典虽是社会法则精髓,却无人提起,一旦学好,运用得当,就路路畅通了。
“噢!我想起来了,”欧也纳说,“我在您的舞会上,认识了德·雷斯托夫人;今天上午我去了她府上。”
“您想必打扰她了。”德·鲍赛昂夫人微笑着说。
“唉!是呀,我真是无知,您要不肯帮我,我一定会招致所有人跟我作对。我看,要在巴黎遇到一位年轻漂亮、有钱有气质,又没人缠住的女子,实在是难而又难;我需要这样一位女子给我指点人生,而你们女性教起人生来,却是那么精辟透彻。我处处都会碰到某个德·特拉伊先生。因此我来找您,是向您请教一个谜底,请您告诉我,我在那里捅的娄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提起一个老头……”
“德·朗热公爵夫人到。”雅克过来通报,他打断了大学生的话,大学生做了个非常恼火的动作。
“您要想成功,”子爵夫人低声说道,“首先就别这么心情外露。”
“噢!您好呀,亲爱的,”她说着站起来,过去迎接公爵夫人,握住她的手,亲热体贴的样子,便是对亲姐妹也不过如此;公爵夫人也无比亲昵地回应她。
“这是两个好朋友,”拉斯蒂涅心里想,“从此我就有两座靠山了;这两个女人想必意气相投,这一位没准也会关心我。”
“真是幸会,亲爱的安图瓦奈特,您怎么想到要大驾光临呀?”德·鲍赛昂夫人说。
“我看见德·阿瞿达—平托先生进了罗什菲德公馆,心想那么您就是独自在家了。”
公爵夫人说这些要命话的时候,德·鲍赛昂夫人没咬嘴唇,也不脸红,而是目光依旧,脸上反倒开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