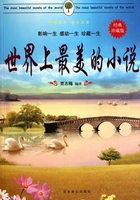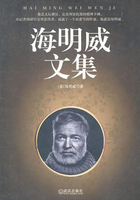使女人变得如此伟大的高尚情操,当今社会结构迫使她们所犯的过失,两者交错之下,使欧也纳心都乱了;他一边用好话安慰她,一边暗暗赞叹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痛苦呼声,竟是那么无邪无畏。
“您将来不会拿这事要挟我吧,”她说,“您得答应我。”
“哎,夫人!我哪能呀。”他说。
她拿起大学生的手按在心口上,举止之间充满了感激和友爱。
“您使我又变得自由自在,开心快乐了。过去,我老觉得有只铁手压迫着我。现在我要俭朴过日子了,分文不浪费。我这样做您觉得好,朋友,对吗?这点您就留着吧,”说着,她自己只拿了六张钞票。“其实,我还欠您三千法郎,因为我觉得应该跟您平分的。”
欧也纳像小姑娘一样不肯要。可是男爵夫人对他说:“您要是不做我的同伙,我就把您看作敌人。”他只好收下钱。
“那就留做本钱,以防不测吧。”他说。
“我就怕听这句话。”她嚷起来,脸都变白了。“您要是心里有我,就给我发誓,”她说,“今后永不上赌场。我的天!我带坏了您!那我要痛苦死了。”
他们返回了。刚才的困苦与眼前的富足,两者对比之下,大学生只觉得头晕目眩,耳朵里又响起伏脱冷那些可怕的话。
“您坐这儿吧,”男爵夫人走进卧室说道,指了指壁炉旁边的双人沙发,“我要写一封不好写的信!您给我出出主意。”
“干脆不写,”欧也纳对她说,“把钞票直接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派您的侍女送去得了。”
“您可真行。”她说。“啊!先生,这才叫做有教养!完全是鲍赛昂式作风。”她微笑着说。
“她真迷人。”越来越动情的欧也纳想到。他瞧了瞧卧室,奢侈的讲究仿佛一个有钱交际花的屋子。
“您喜欢吗?”她边问边拉铃唤侍女。
“泰蕾兹,您把这亲自送给德·马尔赛先生,一定要面交他本人;要是找不到他,就把信带回来退给我。”
泰蕾兹临走还朝欧也纳狡黠地看了一眼。晚餐备好了。拉斯蒂涅伸出手臂,让德·纽沁根夫人挽着,随她来到一间精致的餐厅,当初在表姐家赞叹过的华美席面,在这儿又见识了一回。
“意大利剧院有演出的日子,”她说,“您就来跟我一起吃晚饭,陪我一起去。”
“这种美好生活要能长此以往,我当然能够习以为常;可我现在是个穷学生,还得有所作为呀。”
“将来会的,”她笑道,“您瞧,一切顺其自然,这不,当初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开心。”
用可能来证明不可能,用预感来抹杀事实,这是女人的天性。
德·纽沁根夫人和拉斯蒂涅,双双走进滑稽剧院[51]包厢的时候,她的样子心满意足,因而十分美艳动人;每个人看了都会说些流言蜚语,非但女人没法防卫,而且常会使人相信一些随意捏造的绯闻。等你了解巴黎之后,才绝不相信那里的传言;而确有的事实,大家嘴上是不说的。欧也纳捏住男爵夫人的手,两人靠手的纠缠力度代替谈话,交流他们听音乐的感受。那天晚上,真是令他们心醉神迷。两人一起从剧院出来,德·纽沁根夫人有心把欧也纳送到新桥,一路上却执意不肯给他一个吻,就像在王宫市场给过的那种热烈的吻。欧也纳埋怨她前后不一。
“刚才,”她应声说道,“那是报答意想不到的施援之恩;现在,就会成为某种承诺。”
“您连个承诺都不肯给我,没良心的。”
欧也纳生气了。于是她伸手让他去吻,那种急切的样子,足可以使一个情人心花怒放,而大学生拿起那只手的神气却不大高兴,男爵夫人不禁十分得意。
“星期一舞会上见。”她说。
欧也纳踏着皎洁的月光,一边走一边认真思考起来。他又喜又恼:喜的是这次艳遇的结局,说不定会让他得到巴黎一位最漂亮最有气质的女子,正好是他心仪的目标;恼的是他的发迹计划完全给推翻了。直到这时他才认识到,前天模模糊糊的想法,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总是要到受挫以后,才发觉他期望的强烈。欧也纳越享受巴黎生活,就越不愿这样做个无名的穷小子。他把那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在口袋里捻来捻去,找出千般似是而非的理由想据为己有。终于他到了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登上楼梯,看见有光亮。高老头敞着房门,点着蜡烛,意思让大学生别忘了一件事,按他的说法,就是跟他谈谈他的女儿。欧也纳对他毫无隐瞒。
“哼,”高老头老大不服气,大声嚷道,“她们以为我山穷水尽了,我还有一千三百法郎利息的公债呢!天哪!可怜的孩子,怎么不上这儿来!我可以卖掉公债,从里面拿出些钱,余下的钱改成透本终身年金。您怎么不来把她的难处告诉我呢,我的好邻居?您怎么忍心拿她可怜巴巴的一百法郎到赌台上去冒险呢?真伤心啊。女婿就是这种东西!嘿!要给我抓住了,我一定要掐死他们。天哪!哭,她哭了吗?”
“把头靠在我的坎肩上哭。”欧也纳说道。
“噢!把坎肩给我,”高老头说,“怎么!这上面有我女儿的,有我疼爱的但斐纳的眼泪!她小时候从来不哭的。噢!我给您另买一件吧,这件您别穿了,送给我吧。婚约上规定,她应该享有自己的财产。嗯!我要去找诉讼代理人德维尔,明儿就去。我要把她的财产划出来单列。我是懂法律的,我是一匹老狼,还能张牙舞爪呢。”
“喏,老伯,这是赢了钱后,她一定要分给我的一千法郎。您放在坎肩里,替她留着吧。”
高里奥望着欧也纳,伸手要握住他的手,一滴眼泪落在欧也纳手上。
“您的人生一定会成功,”老人对他说,“上帝是公平的,您知道吧?我明白什么叫做诚实;我敢说,像您这样的人很少很少。那么您也愿做我亲爱的孩子了?好啦,去睡吧。您还没做父亲,能睡得着。我现在才知道,她刚才哭了,而我,为了不让她们流一滴眼泪,连圣父、圣子、圣灵都会出卖的人,在她痛苦的时候,我竟心安理得地在这儿吃饭,就像傻瓜一样!”
“真的,”欧也纳一边躺下一边想,“我相信,我会一辈子做个正直的人。凭良心办事,自有乐趣嘛。”
也许只有信上帝的人,才会暗中行善,而欧也纳是信上帝的。
第二天到了舞会的时间,拉斯蒂涅前往德·鲍赛昂夫人府。夫人带他去介绍给德·卡里格利亚诺公爵夫人。他受到元帅夫人极为热情的接待,在她家又见到了德·纽沁根夫人。但斐纳特意打扮得要讨众人喜欢,以便格外讨欧也纳喜欢。她自以为沉得住气,其实巴不得欧也纳早些看她一眼。你要能猜透一个女人的情绪,那个时候便充满了乐趣。人家等你发表意见,你偏偏要卖关子;心里暗自得意,你偏偏不动声色;惹得人家心神不宁了,你偏偏还要人家自己说出来;本来微微一笑即可消除人家的恐慌,你偏偏要去幸灾乐祸,这一套谁不喜欢经常来一下呢?在这次盛会上,大学生蓦地看清了自己的地位;他明白了,就因为他是德·鲍赛昂夫人承认的表弟,便在上流社会有了一个身份。大家认为他已经追到德·纽沁根男爵夫人,因而他格外显眼,所有的青年都向他投去艳羡的目光。看到这类目光,他第一次体味到得意的快感。从一间客厅走到另外一间,在人群中穿过的时候,他听见人家夸他有艳福。女士们全都预言,他一定会春风得意。但斐纳唯恐失去他,答应他晚上不会拒绝亲吻,而就在前天却怎么也不肯。拉斯蒂涅在这次舞会上,受到好几个人的邀请。表姐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士,都是自命高雅的人物,她们的府第也是公认惬意的去处。他眼看自己在巴黎最高贵、最气派的社会露了头角。这次晚会对他而言,是成功的开端,颇有魅力,想必直到暮年都会念念不忘,正如一个少女,总是记得她出尽风头的舞会。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当着公寓客人,把这些得意事儿,一五一十讲给高老头听,伏脱冷却狞笑起来。
“你们以为,”这个无情的逻辑学家大声说道,“一个时髦青年能够待在圣热内维埃芙新街,住伏盖公寓吗?当然喽,这儿从各方面看都极为体面,但与时髦却沾不上边。我们这公寓殷实舒服,兴旺可观,能做拉斯蒂涅的临时公馆非常荣幸;可是到底地处圣热内维埃芙新街,毫无奢华可言,因为纯粹是传统氛围拉玛。我的年轻朋友,”伏脱冷倚老卖老地挖苦道,“您要在巴黎抛头露面,非得有三匹马,早上有辆篷车,晚上有辆轿车,车辆费统共九千法郎。要是您不在裁缝店花三千法郎,香脂店花六百法郎,鞋商那边花三百,帽商那边花三百,您就不配交上好运。至于洗衣妇,您得花上一千。时髦小伙子在衬衣、手帕上面,也不免十分讲究,那不是大众最注目的吗?爱情和教堂一样,圣坛上都要有漂亮的铺陈才行。咱们的开销已经到一万四了。我还没跟您提到赌钱、打赌、送礼的花费;零用没有两千法郎是不成的。那种生活,我是过来人,知道要出多少。这些必需之外,还要加上六千法郎啃面包,一千法郎躺床板。得了,小伙子,这样紧打紧算,腰里就得每年两万五,要不就跌进烂泥潭了,落人笑话自己,咱们的什么前途、成就、情妇就全吹了!我还忘了听差和马夫呢!难道总要克里斯托夫替您送情书吗?总用您现在这种信纸写情书吗?那简直是自寻死路。相信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汉吧!”他用rinforzando[52]的男低音又说道:“要就躲到清高的阁楼上去,抱着书本用功;要就另走一条路。”
伏脱冷瞟了一下泰伊番小姐,挤了挤眼睛,这副眼神表达、概括了他那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当初为了拉人下水,已经向大学生灌输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