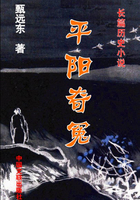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是啊,我觉得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光了,”她疑神疑鬼地咕噜说。“肯定不止的。我记得他们吵过架后,我是在客厅里边,艾德加好狠心来气我。我才不顾死活冲到这间房里来。我刚一闩上门.黑咕隆咚一大片就罩住我,我倒在了地上。我没法跟艾德加说清,要是他铁定了心来戏弄我,我准保老毛病就会发作。再不要给他气疯狂的!我已经管不住我的舌头和脑子了,兴许,他都没有猜想到我的痛苦啊。我差不多都没有足够的知觉。来逃避他和他的声音了。一直到开始破晓时分,我才恢复过来视觉和听觉。奈莉,我要告诉你我想了些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我脑子里转过来,又转过去,直到我担心起自己的理智来。当时我是躺在那里。脑袋靠着桌腿。两眼模模糊糊地瞪着那一块灰蒙蒙的玻璃窗,以为我是给关闭在老家那张橡木嵌板的大床上面了。我的心因为什么极大的悲伤,痛得厉害;可是因为刚刚醒过来,又说不上这悲伤的名堂究竟。我使劲地想,思想它究竟是什么名堂,想得好苦。而且,说来真是不可思议,我生命中过去的七年,整个儿就变成了一块空白!我一点都想不起它们是什么模样。我是个孩子。我爸才刚下葬,亨德雷下令把希斯克厉夫同我分开,由此开始了我的悲苦。我孤零零被撂在一边,这还是第一次。哭泣了一整夜后,我打了个盹醒来,伸手要去推开那嵌板,碰到的却是桌面!我的手顺着桌毯拂过去,然后记忆便汹涌而至,方才的悲痛,顿时就吞没在突如其来的一片绝望之中。我说不上为什么我觉得如此出奇出格地悲苦,一定是一时有些疯狂,因为简直就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可是,想一想在十二岁的光景,我就被人扯出呼啸山庄,每一种以往的交际,我的一切的一切,就像当时的希斯克厉夫一夜之间身份陡变那样,一下子就变成了林顿夫人,画眉田庄的女主人,一个陌生人的妻子,一个流浪汉,一个弃儿,因而哪,远离了曾经是我的那个世界——你就想一想我沦落在里面的那个深渊吧!奈莉,你尽管摇头,可真就是你帮了他来搅得我六神无主!你应当告诉艾德加,理所应当,逼着他让我安静些!噢,我在火烧呀!我真希望我是在门外!我希望我又是一个小姑娘,像个小野人似的,鬼神不怕,自由无羁,受了伤就大笑过去,绝不给它们压得发疯!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寥寥几句话,我的血就冲动得直沸腾起来?我肯定只要我是在那边山间的荒野里边,我就会变回我自己的。再把窗开大些吧,开到底再钩上窗钩!快点,你为什么不动呀?”
“因为我不想叫你冻死。”我回答说。
“你是说,你不愿给我活命的机会了,”她沉下脸说。“可是,我还不是一筹莫展哪,我自己来开。”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便从床上滑溜下来,跌跌撞撞穿过房间,一把推开了窗,探出身去,全然不顾冰冷的空气宛若小刀,嗖嗖割着她的肩膀。
我求她,最后打算硬拖她回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她精神迷乱之下,力气远远超过了我。我确信她精神迷乱,因为紧跟着她就胡言乱语,行为也稀奇古怪起来。
外面没有月亮.天底下一切都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之中,是远是近,没有一处房舍亮出灯光,一切都已早早熄灭了。至于呼啸山庄的灯光,则压根就非目力所及。可是,她仍然坚持说,她看到它们闪烁来着。
“瞧!”她急切地喊道,“那是我房间里的烛光,树在房前摇晃呢……那一根蜡烛是约瑟阁楼里的……约瑟熬夜,不是吗?他在等我回家,回家了才好锁上大门……好吧,让他再等一会儿。那条路不好走,走起来叫人伤心。我们非得走过吉默顿教堂,走那一条路!我们时常一起逗鬼来着,互相比试着胆量,站到坟茔中间,请那幽灵鬼怪只管出来……可是希斯克厉夫,要是我现在同你比试,你敢吗?要是你敢,我就陪着你。我不愿自个儿躺在那里,他们会把我深埋12英尺,把那教堂扔过来压住我,可是除非你来陪我,我是不会安息的。永远不会!”
她停顿下来,又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接着说下去,“他在想呢。他就想我去找他!那么,寻条路出来吧!不走吉默顿教堂的院子……你真慢!别抱怨,你总是跟着我!”
眼见同她的疯劲再争辩,也是枉然,我就盘算如何找点什么给她裹一裹,又不把她松开。因为让她独个儿待在大开着的窗户跟前,我着实不放心。这时候,我大吃一惊听到门栓声响起,林顿先生走了进来。他那时刚从书房里出来,走过门廊的时候.听到我们在说话,许是被好奇心吸引,许是出于担心,要来瞧瞧说些什么,深更半夜的。
“噢,先生!”我嚷道,他一眼望见这屋里的情势,及那凄凄惨惨的气氛.正要叫喊,却给我的一声嚷堵在了嘴唇中间。
“我那可怜的女主人病啦,她算是治住我啦,我对她一点办法都没有。求你,过来劝她到床上去吧。忘掉你的愤怒,因为除了她自己。她谁都不想听啦。”
“凯瑟琳病了?”他说,一下子就冲了上来。“关上窗户,艾伦!凯瑟琳,为什么……”
他哑然无声。林顿太太憔悴的神色给他当头一棒,叫他话都说不出来。他只能把目光朝我转过来,吓得目瞪口呆。
“她在这儿发气呢,”我接着说,“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呀,而且一声都不抱怨,直到今天晚上,她谁也不让进屋,所以我们没法告诉你她的境况呢,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呀。可这也没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解释前言不搭后语,主人皱起了眉头。“这也没什么的,是吗?艾伦·迪恩?”他严厉地说。“你得说清楚,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他把妻子抱在怀里,好不心疼地看着她。
起初她没有认出他来的眼色,在她恍恍惚惚的凝视当中,没有他的影子。好在她的谵妄并不长久,她的目光既然不再冥思外面的黑暗,一点一点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到底发现了是谁搂抱着她。
“啊!你来了,是你吗,艾德加·林顿?”她说着火又蹿了上来。“你就是那一种东西,你顶不需要的时候就找到了,可当需要你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我想如今我们是该好好哀悼一气啦……我知道我们是要的……可是它们挡不住我去那边我那一长条家园,我的歇息地,我准定在春天过去之前,就到那边!它就在那边,不是在教堂的屋顶底下,听着,在林顿家族中间,是在旷野里,树一块石碑。你可以自作主张,是跟他们相会呢,还是来我这里!”
“凯瑟琳,你说了些什么呀?”主人说道。“我对你已经一钱不值了吗?你爱那个混蛋希斯——”
“住口!”林顿太太喊道。“这当儿请你住口J你要提起那个名字,我就立时了结,跳出窗去!眼下你触摸到的东西,你可以占有。可是在你的手再次碰到我之前,我的灵魂就将飞向那个山巅子。我不要你。艾德加,我要你的时分已经过去了。回到你的书堆里去吧。我很高兴你有了一个安慰,因为你在我身上拥有过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啦。”
“她的心在跑野马。先生,”我插进来说。“她一整夜都在胡说八道。可是,让她得到安宁,得到需要的护理吧,她会康复过采的。从今以后,我们一定得多加小心,别让她生气了。”
“我再不想来听你的高见了,”林顿先生答道。“你明知你的女主人性情急躁,可你还怂恿我来惹她上火。而且绝口不提她这三天是怎么过的!真是残忍哪!病上几个月,也不至于导致这样的变化!”
我开始替自己辩解。觉得别人刁钻古怪,却要我来挨骂,实在不公道。
“我知道林顿太太性情暴烈,盛气凌人,”我嚷叫起来,“可是我并不知道你想要推波助澜,助长她的凶狠!我不知道为了讨好她。我应当视而不见希斯克厉夫先生。我告诉你是尽了一个忠实仆人的本分,如今我得到了一个忠实仆人的酬报!好啊,这是一个教训,教我下一回理当谨慎。下一回你向你自个儿去打听消息吧!”
“下一回你再跟我信口胡言,你将要离开这里,艾伦·迪恩。”他答道。
“那么说,你最好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想,林顿先生?”我说。“希斯克厉夫是得到了你的恩准来向小姐求爱,而且每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他就乘虚而入,以便欺瞒太太来反对你,难道不是这样吗?”
凯瑟琳虽说是迷迷糊糊,她的神志可还是相当警觉,听着我们的谈话。
“啊!奈莉当了奸细,”她大叫起来,非常激动。“奈莉是我的暗藏的敌人。你这巫婆!这么说你真是在拣小鬼的箭来伤害我们呀!松开我,我要叫她后悔!我要叫她鬼哭狼嚎给我认错!”
在她双眉底下,疯狂的怒火点燃起来了。她不顾死活地挣扎着,要从林顿的手臂里面解脱出来。我无意来火上添油,决定自作主张,去请医生相帮。我离开了卧室。
穿过花园走向大路的时候,我看到钉在围墙上的一个缰绳钩上,有个白乎乎的东西在莫名奇妙地晃动,显然不是由于风。我尽管走得急忙,还是停住了脚步,准备看个仔细,免得日后疑神疑鬼,压在心上总也摆脱不掉,认准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客人。
我看不清楚,却触摸清楚了,这清楚着实叫我大吃一惊,不知所以,因为它居然是伊莎贝拉小姐的小狗,范尼,给吊在一条手帕上面,早已是气息奄奄了。
我赶紧放下这小狗儿,把它抱到花园里边。我明明看到它跟着它的女主人上了楼,那时她正要去上床就寝。我实在纳闷它如何就跑出来到了绳钩上面,是哪个恶毒的混蛋干的好事。
当我在开解钩上绳结的时候,仿佛不断听到急骤的马蹄声。可是我满肚子的心事,都忘了来把这情势思量一下,清晨两点时分,在那么一个地方,这声音实是好生奇怪哪。
说来也巧,我走到他那条街时,肯尼斯先生刚刚出门,要去看村里的一个病人。我说了凯瑟琳·林顿的病情,他马上就跟我走了回去。
他是一个率直的人,没有太多讲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怀疑,怀疑她能不能挺过这第二次发作,除非她老老实实听从他的指令,不似前一回那样恣意胡来。
“奈莉·迪恩,”他说。“我禁不住要猜想这病是另有原因。画眉田庄发生什么事了?这里也是传言纷纷。健壮活泼一如凯瑟琳的姑娘可不是风吹草动就会病倒的,而且那样的人也不是多病的命。要让她挺过高烧什么的,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怎么发病的?”
“我家主人会告诉你的,”我回答说。“可是你知晓厄恩肖一家人的狂暴性情,而且数林顿太太最是邪火。我可以说,发病是因为吵架引起的。她狂怒之下,一时就颠三倒四起来。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因为吵到顶剧烈的当口她跑了出来,把自己紧锁起来。在这之后她拒绝进食,现在时不时就胡言乱语,总是半梦半醒的。她还认得周围的人,可是心里却装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还有幻想。”
“林顿先生后悔吗?”肯尼斯用探问的口气说道。
“后悔?要是有什么意外,他心都要碎啦!”我答道。“要不是非说不行,别吓着了他。”
“那好,我叫他小心一‘点,”我的同伴说道。“他不听我的警告。必定自食其果!近来他同希斯克厉夫先生还是挺热火吧?”
“希斯克厉夫经常造访田庄,”我答道,“虽然这主要是因为自小就认识他的太太,而不是因为先生喜欢有他作伴。眼下他是不必费心再来登门了,因为他对林顿小姐表现出些许非分之想。我想他是难得再来了。”
“林顿小姐叫他碰钉子了吗?”这是医生的下一个问题。
“我说不准她的心思。”我答道,很不情愿拉扯这个话题。
“不,她鬼着哪,”他摇着头说道。“她自有主见!可她其实是个小傻瓜。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是昨天夜里——那一夜可真美!她和希斯克厉夫在你家后面的田园里一起散步来着,散了两个多钟头。他逼迫她别再回去,干脆就骑上他的马,同他一起走吧!告诉我这事的人说,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赌咒发誓,让她准备到下一次会面的时候再作行动,才算叫他罢休。下一回是什么时候,他没有听见。可你得督促林顿先生提高警惕哪!”
这消息又给我平添新的恐惧。我把肯尼斯甩在后面,差不多是一路跑着回来。小狗还在花园里汪汪叫着。我用了一分钟光景,给它打开大门,可是它不往房门里钻,反倒在草地上嗅过来嗅过去,要不是我一把抓住它,带着它回屋,它还要窜到大路上去呢。
上楼走进伊莎贝拉的房间,我的疑心就被证实了:它空空如也。要是我早到一两个钟点,林顿太太的病情兴许还会阻止她迈出这莽撞的一步。可是现在又能奈何?要是我立时去追赶,追上他们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无论如何,我不能去追他的。而且我不敢惊动这一家人,弄得全家惊惶失措。我更不愿向我家主人披露这事,他正身临眼下的灾难,哪里还能分心来承受第二件伤心事!
我束手无策,只有闭住我的嘴,听其自然。既然肯尼斯来了,我就板着脸,去为他通报。
凯瑟琳在睡觉,却辗转反侧睡不安稳。她丈夫已成功地抚平了她越见炽烈的癫狂,此刻正俯身在她枕头上方,细察着她痛苦地扭曲起来的五官之间,出现的每一丝阴影和每一个变化。
医生亲自检查过病情,不失希望地对他说,这病是可以见好的,只要在她周围保持完全的、持久的宁静。对我,他则暗示这扑面而来的危险倒未必是死亡,而可能是理智的永久丧失。
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林顿先生也没有。真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沾过床边。仆人们,也全都早早起床,远早过平常的时辰,蹑着脚步在府邸里来回穿梭,在各司其职的当儿相互照应时,就窃窃私语交流起来。除了伊莎贝拉小姐,人人都活跃得很,他们开始讲起她睡得多么香甜。她哥哥也问起她是不是起床了,仿佛等她露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而且很伤心她对她的嫂嫂,是如此的漠不关心。
我直发抖,生怕他差我去叫她。可是我逃过作第一个人来宣告她的私奔,这倒叫我如释重负。有一个丫头,一个很是莽撞的姑娘,一早就给差使到吉默顿去,她气喘吁吁跑上楼来,大张着嘴巴,一头冲进卧房,高喊道:
“噢,天哪,天哪!我们还有什么灾祸呀?老爷,老爷,我家小姐——”
“别吵吵嚷嚷的!”我立时吼她回去,十分恼火她纷纷扬扬的作风。
“小声点说,玛丽——怎么啦?”林顿先生说。“你们小姐犯什么病痛啦?”
“她跑了,她跑了!那个希斯克厉夫把她带跑了尸那姑娘喘着气说。
“那是胡扯!”林顿失声嚷道,火气一下子就蹿了上来。“那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个怪念头?艾伦·迪恩,去找她。难以置信,这不可能。”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丫头带到了门口,再一次问她,这样有什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