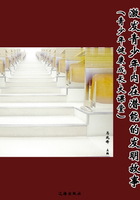希斯克厉夫,往后我得说希斯克厉夫先生了,十分谨慎使用拜访画眉田庄的自由,这是在最初。他仿佛是在估算它的主人容忍他的闯入,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凯瑟琳也觉得把接待他时的高兴劲儿压制些许。是更得当一些。他渐渐地确立了他来作客的权利。
他向来沉默寡言,这在他孩提时代就是十分突出的,这就帮他压抑下了一切大惊小怪的情感表现形式。我家主人的不安平静了一段时光,可是情势的进一步发展,又把它引导到另一个方面去了。
他的烦恼的新来源,是出自伊莎贝拉突如其来的不幸,她突然地,而且是无法抗拒地爱上了被容忍下来的客人。这时候她出落成楚楚动人的一个十八岁的小姐,风度举止天真烂漫,虽然具有敏锐的机智,敏锐的情感,而且,一旦被惹恼了,脾气也十分敏锐。她的哥哥是非常温柔地疼爱着她的,被她异想天开吓坏了。不说跟一个没名没姓的人结亲有辱门楣,也不说假如他没有男嗣,他的家产有可能落到这样一个人的手里,他还十分清楚希斯克厉夫的脾性,知道他的外表虽然变了,他的内心却是变不了的,而且也没有变。他惧怕那个内心,他专同他作对。他想都不敢想得把伊莎贝拉交给他来保管,像是有种预感。
他要是知晓她的情愫是未经挑唆就自动烧将起来的,并没有唤起对方的热情以作回报,就更要哆嗦了。他一经发现了它,就怪在希斯克厉夫头上,怪他是刻意设下了圈套。
有一段时间,我们全都看出林顿小姐是有心思,神志不定的。她变得暴躁起来,叫人头痛。她缠住凯瑟琳,又是谩骂又是冷嘲热讽,全不顾她原本耐心有限,随时都能发作起来。我们都让她几分,以为她身体不好。因为她就在我们面前萎缩憔悴下去。可是有一天,她折腾得特别厉害,不肯吃早饭,抱怨仆人们没有听她的吩咐,太太又让她在家里一事无成,还有艾德加也怠慢了她。她说门开着让她伤风了,说我们让客厅熄火,存心惹她生气,还有一百种更鸡零狗碎的怨言。林顿太太断然叫她上床睡觉。在痛骂了她一顿之后,威胁要请医生来。
一提到肯尼斯,她马上就叫唤起来,说她身体好得很哪,完全是凯瑟琳凶狠无礼,才叫她不高兴的。
“你怎么能说我凶狠无礼,你这淘气的宝贝儿?”太太嚷道,对这没来由的指责莫名奇妙。“你肯定是昏了头了,我什么时候凶狠无礼来着?告诉我呀。”
“昨天,”伊莎贝拉抽抽嗒嗒说,“还有现在!”
“昨天!”她的嫂嫂说。“什么时候?”
“我们在荒野散步的时候,你叫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溜达,你却跟希斯克厉夫先生一路逍遥啦!”
“那就是你说的凶狠无礼?”凯瑟琳大笑起来。“这并不是嫌你陪着是多余的,我们可不在意你跟着我们或是不跟。我只是想,希斯克厉夫的谈话在你听来是索然无味的呀。”
“哦不,”小姐哭着说,“你要我走开,是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待在那里!”
“她疯了吗?”林顿太太向我讨教说。“我可以重述一遍我们的交谈,一字一句的,伊莎贝拉,你倒是指出这当中哪一点你觉得有趣。”
“我不在乎谈话,”她答道,“我要同——”
“同什么!”凯瑟琳说,看出她犹豫,欲言又止。
“同他在一起。我不愿总是给打发开去广她接着说,激动了起来。“你是马槽里的狗,凯茜, 自己不吃,又不让别人吃,除了你自个儿,最好谁也不要被爱!’’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小猴子!”林顿夫人大吃一惊嚷道。“可我不信这蠢到顶的想头,你妄想得到希斯克厉夫的崇拜,你会把他看作一个可爱的人,这怎么可能!我希望我是误解你了,伊莎贝拉?”
“没有,没有误解,”那鬼迷心窍的姑娘说,“我爱他胜过你对艾德加全部的爱。要是你不拦着,他也会爱我!”
“那么,给我一个王国,我也不愿意做你!”凯瑟琳断然宣布说。她的话看来是诚恳的。“奈莉,帮我让她明白她是疯啦。告诉她希斯克厉夫是什么人:一个没开化的东西,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一片不毛的荒野,荆棘丛生,岩石裸露。我马上就把那只小金丝雀放到冬天的园林里去,给你做个榜样,叫你把心去交托给他!你对他的个性全不了解,孩子,不是因为别的,才叫那幻梦钻进你的头脑。求你了,别以为他那冷峻的外表底下深藏着仁爱和感情他不是一块原始的钻石,粗人当中的一个含珠之蚌。他是个残暴无情,狼一样的人。我从来不对他说,‘放过你这个那个仇人吧,因为伤害他们是小气,是残忍’。而是说, ‘放过他们,因为我不容他们受到伤害’。他会捏碎你就像捏碎一个麻雀蛋,伊莎贝拉,要是他发现你是个讨厌的负担的话。我知道他不会爱林顿家的人,可是他完全能够同你的财产和前程结婚,贪婪心在他身上滋长,已经成了摆脱不了的罪恶。这就是我给他的画像。我是他的朋友,正因为如此,要是他认真想来捕获你,兴许我应当紧闭嘴巴,让你掉进他的陷阱呢。”
林顿小姐却愤不可遏地看着她嫂嫂。
“羞耻!羞耻!”她气呼呼地连声说。“你比二十个敌人还要坏,你这毒蛇心肠的朋友!”
“啊!你不愿相信我,那么说?”凯瑟琳道。“你以为我说这些全是出自恶毒的自私心吗?”
“我肯定你就是,”伊莎贝拉反击说,“你叫我发抖!”
“好哇!”另一位喊道。“你自个儿去试一试吧,要是你有这兴致。我说完了,不同你争了,你自个儿去蛮横去胡缠吧。”
“可我非得为她的自私受苦!”林顿太太离开房间的时候,她哭泣着说。“所有,所有的人都在反对我。她把我唯一的安慰摧残了。可是她说谎,不是吗?希斯克厉夫先生不是恶鬼,他有一个可敬的灵魂,真诚的灵魂,要不他怎么能记得她?”
“把他从你心上赶走,小姐,”我说。“他是一只不祥的鸟,同你不配。”林顿太太话讲得太冲,可是我没办法反驳她。对他的心,她比我,甚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要了解。而且她把他说得再坏,也没有他本人坏。诚实的人是从不隐瞒他们的所为的。可是那几年怎么过的?怎么发的财?为什么他住到呼啸山庄去,那可是他深恶痛绝的人的府邸?他们说, 自从他来,厄恩肖先生是越来越糟糕了。他们通宵达旦坐在一起,亨德雷借钱借得把土地也抵押了出去,什么也不干,就是耍钱、喝酒。那是一星期前我听说的,约瑟告诉我的,我在吉默顿遇到他了。
“‘奈莉,’他说,‘我们这伙人儿,全得请验尸官来验尸啦。他们当中一人差点儿给砍掉手指,为的是挡住另一个像宰牛似的一刀把自己扎死。那就是少爷哪,你知道,他一路飞上去,要去听从大审判啦。席上的法官他一个也不怕,不怕保罗、不怕彼得、不怕约翰、不怕马太,他们中随便哪个,他都不怕!他挺喜欢把他的厚脸皮晾在他们面前!还有你的好孩子希斯克厉夫,听着吧,他可真了不起!就是真正的魔鬼来玩把戏,他也会咧开嘴大笑,谁都赢不了他。他到田庄来的时候,从没讲过如今他在我们当中过的好日子吗?就是这样:太阳落山了起床,掷骰子,白兰地,关上百叶窗,点上蜡烛,一点点到第二天正午。然后,那个傻瓜蛋就诅天咒地,满嘴胡言摸到他的卧房里去,叫好人羞愧难当,只能用手指来把耳朵塞上,那个坏蛋,哇,他倒会计数他的铜板,吃饱了,睡足了,跑到邻家那儿同人家老婆扯短拉长。当然啦,他告诉了凯瑟琳小姐他让她老子的金子滚进他的口袋里边了,她老子的儿子在下地狱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他则跑在前面,替他一一排开栅栏?’听着,林顿小姐,约瑟是个老混蛋,可他不是说谎的人。要是他讲的希斯克厉夫的行为当真不假,你永远也不会想去找这样一个丈夫,是吗?”
“你和他们都串通好了,艾伦!”她回答说。“我不听你们的诽谤。你们心肠多毒,要我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幸福了!”
我说不准要是由她自个儿去,她是会从这幻想中幡然悔悟过来,还是一味执迷下去。她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来思量了。第二天,我们邻居在城里有一堂会审,我家主人是非得到场的。希斯克厉夫知道他不在,早于往常的时分就来登门了。
凯瑟琳和伊莎贝拉坐在书房里,怄着气,可是没有出声。伊莎贝拉对她近日来的鲁莽很是惊惶,懊悔她情绪一阵发作,就把她内心里的秘密情感吐露了出来。凯瑟琳则是思前想后下来,认真生了她的伙伴的气,决计要是下一回再来笑话她的荒唐,得让她明白这可不是好笑的事儿。
希斯克厉夫经过窗口的时候,她真的笑了。我这时候我在扫炉子,看到她嘴角上挂着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伊莎贝拉专心致志在想心思,再不就是在读书,纹丝不动直到门给打开来。要是能逃的话她本想逃走的,可是已经晚了。
“进来,来得好!”太太高兴地喊道,拖过一把椅子到火炉边。“这里的两个人,正眼巴巴等待第三者进来,来融掉她们之间的冰雪呢。你就是我们两个都要选择的人。希斯克厉夫,我很荣幸,终于给你看到一个比我自己更加喜欢你的人啦。我想你要受宠若惊呢。不,不是奈莉,别看着她!我那可怜的小妹妹只要想一想你体魄上和道德上多美,就要心碎啦。要不要做艾德加的妹夫,全在于你自己!别,别,伊莎贝拉,你不要跑呀,”她装着开玩笑的样子,说着就一把揪起那不知所措的姑娘,她正气呼呼站了起来。“我们方才还为了你吵得像猫打架似的,希斯克厉夫,要争忠心和崇敬,我是败得凄惨。还有呢,我听说要是我懂得识趣,站在一边,我的情敌,就像她自命是我的情敌,会一箭射进你的灵魂,从此就紧随着你,把我的影子驱赶到天涯海角!”
“凯瑟琳!”伊莎贝拉说,振作起她的尊严,不屑于在她紧紧把握之下徒作挣扎。“我要谢谢你照直说,不要中伤我,哪管开玩笑!希斯克厉夫先生,做做好事让你这位朋友放了我。她忘了你和我并不十分相熟相知,叫她快活的事儿,在我是说不出的痛苦。”
客人一言未发,却坐了下来,她对他怀着什么样的情感,他一付无动于衷的神气。她转过身,压低了声音,认真乞求折磨她的人把手松开。
“没门!”林顿太太应声道。“我可不愿再被人叫马槽里的狗。你该留在这里,留着希斯克厉夫,听到我这好消息,为什么不洋洋得意呀?伊莎贝拉发誓说艾德加对我的爱,比起她爱你来微不足道。我肯定她说过这一类话。她没说过吗,艾伦?自从前天散步以后,她又伤心又气恼滴食未进,就因为我把她从你身边打发走了,以为你不会欢迎她哪。”
“我相信你是冤枉她了,”希斯克厉夫说,转过椅子面对着她们。“至少她现在就希望离开我身边!”
他紧紧盯住被谈论的对象,就像人聚精会神来看某个令人反感的稀罕动物,比方说,一条印度的蜈蚣,尽管它使人反胃,可是架不住好奇心,还是要细看一番。
那可怜的东西受不了啦。她脸上一阵白,一阵红,飞快地变着颜色,泪珠一颗颗挂在睫毛上面,她使足力气,用她小小的手指来扳凯瑟琳紧抓住她的手掌。眼见她才从她胳膊上扳开一个手指,另一个又紧抓下来,总也无法整个儿解脱出来,她便开始使用她的指甲,尖利的指甲当时就在紧抓住她的手指上面,印上了几个红色的新月图案。
“母老虎哪!”林顿太太喊道,放开了她,疼得直挥手。“走开吧,看在上帝的份上,藏好你那一张泼妇脸!冲着他把这些爪子亮相出来,你多笨呀。不能想想他会有什么感受吗?瞧,希斯克厉夫!那就是执法的工具哪,你可得小心你的眼睛。”
“我要把它们从她手指上扯下来,要是胆敢来触犯我,”他野蛮地答道。这时候她人已离去,门也随手关上了。“可是你这般样来捉弄这小东西,是什么意思,凯茜?你讲的不是真话,是吗?”
“我保证这是真的,”她答道。“她为你犯相思犯了几个星期啦。昨儿早上,她为你大吵了一场,滔滔不绝破口大骂,只因为我如实交待了你的缺点,好冷一冷她的痴情。可是别再理会她了。我是想惩罚惩罚她的刁钻劲儿,就那么回事。我太喜欢她啦,哪儿舍得给你一把抓去,活活吞了呢。”
“要我这样做,我是太不喜欢她啦,”他说,“除非是做得叫你毛骨悚然。假如让我独个儿和那张叫人作。区的蜡脸待在一起,你准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最平常的是在它的白板上面涂上彩虹的颜色,再不叫那一对蓝眼睛变成青紫色,每隔一天或者两天。那双眼睛跟林顿的眼睛一样讨厌。”
“是讨人喜欢!”凯瑟琳说,“那可是鸽子眼——天使的眼睛!”
“她是她兄长的继承人,不是吗?”沉默了片刻,他问。
“我很遗憾我想是的,”他的伙伴回答说。“半打侄儿想要勾销她的权利呢,谢谢老天。别老盯着这事儿,你觊觎你邻居的财产,可是过火啦。记住,这个邻居的财产是我的。”
“假如它们是我的,那还不是一样,”希斯克厉夫说。“可是尽管伊莎贝拉·林顿有点傻,她可一点也没疯。她,一句话,我们不提这事了,听你的。”
口头上,他们确实是不谈这事了。在凯瑟琳,也许她心里边也不再想它了。可是另一位,我确信无疑,那一夜却时时想起它来。我看到,只要凡林顿太太偶尔离开房间,他就自个儿发笑,应当说是狞笑,然后就沉入凶象环生的冥想。
我打定主意盯住他的行动。我的心一成不变是偏在我家主人这一边,而不是在凯瑟琳这一边。我想我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和气可信,又诚实。她呢,虽然说不上是恰恰相反,可是她太随心所欲,所以我对她的处世准则没有什么信心,对她的情感,更是懒得同情。我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可以悄悄地把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从希斯克厉夫手里解救出来。让我们回到在他闯进来之前的时光中去。他的拜访对于我像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我猜想,对我家主人也是这样。他住在呼啸山庄,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我感到上帝已经抛弃了这只迷途的羔羊,听凭它胡乱游荡,一头邪恶的猛兽潜行在它和羊栏之间,等待时机到来,一跃而起,把它吞下。
有时候,当我独个儿寻思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跳将起来,戴上帽子走出去,看看那庄子变成了什么模样。我说动我的良心,相信我有责任警告他别人是怎样谈论他的行为。然后我又想起他根深蒂固的恶习,再规劝也是白搭,便欲行又止,不愿再跨进那一幢败落相的邸宅,怀疑我的话能不能被当一回事情。
有一回我去吉默顿,绕一个圈子走过了那个古老的大门。那大抵就是我的故事讲到那里的时光,一个晴朗的霜冻凛冽的下午,地表里光秃秃的,道路又硬又干。
我走到一块界石边上,大路在这里分岔,左边一条道支出去,通向荒原。界石是一根粗糙的砂柱,北面刻有W.H.字样,东面刻着G·,朝西南的一面上刻着T·G·。W·H·即呼啸山庄 (Wathering Heights),G·即吉默顿 (Gimmerton),T·G·即画眉田庄 (Thrushcross Grange)。它是通向画眉田庄、呼啸山庄和村落的路标。
太阳黄橙橙地照在它灰白色的顶端,叫我想起夏日的光景来。我说不上为什么,孩提时的情感似一股激流,一下子冲人了我的心间。二十年以前,亨德雷和我就把这里看成是最好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