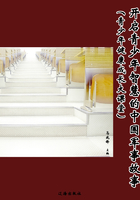“但是……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没关系,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开头嘛。我可以聘请你做我的助手,帮我四处走走,采访一些人,收集资料。开始的时候,你每月可以拿两百五十法郎,车费报销。如果你愿意做,我就去跟经理谈谈。”
“我当然愿意。”
“那么,明天你来我家吃晚饭。我只邀请了五六个人: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及夫人,你刚刚见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另外还有我夫人的一位女友。你意下如何?”
杜洛瓦红着脸,茫然不知所措,犹豫了半天才嗫嚅着说道:
“只是……我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弗雷斯蒂埃惊愕不已:“天啊,你居然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这可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难道不知道,在巴黎,即使没有床睡觉,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吗?”说着,弗雷斯蒂埃突然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数枚金币,挑了两枚路易放在老朋友的面前,然后用一种十分真诚的腔调说道:
“这些钱,你先拿着,等方便的时候再还给我。你先去租一套或者干脆分期付款买一套礼服,至少把明天应付过去。抓紧时间好好安排一下。明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到我家吃饭,地址是枫丹大街十七号。”
杜洛瓦激动不已,一边拿起钱,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你真好,太谢谢你啦……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仗义相助……”
弗雷斯蒂埃打断他的话:“行了,别说这些,要不要再来一杯?”接着,他大声叫道:“侍应生,再来两杯啤酒!”
喝完,弗雷斯蒂埃问道:
“想不想到外面走走?”
“好啊!”
于是他们走出咖啡馆,朝玛德莱娜教堂走去。
“我们接下来做点什么好呢?”弗雷斯蒂埃问道,“有人说,在巴黎散步,总有地方可以去,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每晚出来散步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该去哪里。如果有女人陪伴,到林子里转转倒是件十分惬意的事,但并不是每次都能碰上这种美事。我认识的一位药店老板和他的夫人,喜欢光顾音乐茶座,但我不喜欢。那么,我们该去哪儿呢?真的没什么地方可去。这里应该建一座蒙梭公园那样的休闲之地,供人们晚上的时候在树下一边喝冷饮一边欣赏美妙的音乐。这花园绝不是什么娱乐场所,而是休闲放松之地。门票可以卖贵一点,吸引一些漂亮的女士。人们可以在铺满细沙、旁边有灯光照明的小径上散步。想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找个或近或远的地方坐下。我们过去在缪塞尔有过一个类似的公园,但那里格调太低,地方也不够大,没有多少树荫和阴暗的角落。所以,我们一定要建一座既宽敞又漂亮的花园,这样一定能够吸引很多人。你想去哪里?”
杜洛瓦一时语塞。最后,他提议道:“我还没去过‘牧羊女娱乐场’,很想去那儿看看。”
他的同伴惊讶地说道:
“‘牧羊女娱乐场’?那里一定热得像个大烤箱。不过那地方还算有趣,行,就去那儿吧。”
于是,他们转身朝蒙马特尔郊区走去。
娱乐场的门前灯火辉煌,把在这里交汇的四条街道照得如同白昼。门外停着一排待出租的马车。
弗雷斯蒂埃径直往里走,杜洛瓦赶紧阻止他:
“我们还没有买票。”
弗雷斯蒂埃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我来这儿从来不用买票。”
走到检票口时,三个检票员都向他敬礼致意,中间一位还和他握了握手,我们的记者先生问道:
“还有好一点的包厢吗?”
“当然还有,弗雷斯蒂埃先生。”
弗雷斯蒂埃接过票,推开包着绒垫的厚厚的铜门,同他的朋友一起走进剧场。
场内烟雾缭绕,舞台、剧场的另一端以及较远的地方仿佛都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香烟和雪茄燃烧后形成的一缕缕白色烟柱,袅袅升起,一直飘到天花板,在巨型拱顶下、吊灯周围和坐满观众的楼座上方形成灰蒙蒙的一片雾气。
剧场四周,是宽敞的圆形走廊。入口处,经常有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在众多的男士中穿梭。走廊中间有三个柜台,每个柜台后面都站着一位年华已逝却依然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不只出卖饮料,也出卖色相。其中一个柜台前面正站着一群姑娘,等待着客人的光顾。身后几面巨大的镜子照出她们袒露的脊背和过往行人的面孔。
弗雷斯蒂埃拨开人群,像一个理应受到尊敬的人物一样,快速往里走去。
他走到一位女引座员身边,问道:
“十七号包厢在哪里?”
“请随我来,先生。”
女引座员把他们带到一个用木板围起的包厢。包厢很小,没有顶篷,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四把椅子也是红色的,挨得很紧,客人勉强可以从中通过。两位老朋友坐了下来,他们的左右两边都是一些一模一样的木格子,呈弧形一直排到舞台边。木格里都坐了人,但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和胸部。
舞台上有三个穿着紧身衣的年轻男子,一高,一矮,一个中等身材,正在轮流做吊杠表演。
那个大个子迈着碎步迅速走到台前。他面带微笑,向观众挥了挥手,好像是在飞吻。
紧身衣下,他的手臂和大腿上的肌肉清晰可见。他故意挺起胸,以便掩饰已经凸起的腹部。他的头发梳得和那些年轻理发师差不多,在头顶从正中整齐地分开。他优雅地一跳,一把抓住吊杠,像车轮似的在吊杠上翻转。然后他双臂紧绷,身体笔直地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平卧着,全靠手腕的力道握住吊杠。
从吊杠上下来后,他在前排观众的掌声中再次微笑致意。随后,他走到幕布边站着。每走一步,都不忘显示一下自己健壮的大腿肌肉。
第二个人个头矮些,但看起来更健壮。他走到台前重复前者的动作。第三个也做了同样的表演,却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不过,杜洛瓦无心关注台上的表演。他不时地回头,朝后面挤满男士和年轻姑娘的走廊张望。
弗雷斯蒂埃对他说:
“看看下面的观众席,全是些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的小市民,都是些蠢货。包厢里坐着的是经常光顾戏院的人,有几个搞艺术的,还有几个二流妓女。在我们身后,则是巴黎最有意思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仔细看看吧!他们来自各个阶层,不过流氓地痞占多数。银行职员、售货员、公务员、记者、妓院老鸨、穿便服的军官、打扮入时的纨绔子弟,他们有的刚在小酒馆吃完晚饭,有的刚看完一场歌剧,待会儿还要去意大利剧场。剩下的,就是些来历不明、不三不四的人,很容易分辨出来。至于那些女人,都是喜欢夜间在“美洲人咖啡馆”前溜达的那种人,只要拿出一两个路易,她们就会跟你走。不过她们每天都在期待着能吊到一个肯出五路易的外乡人。当然有空的时候,她们还是会通知自己的老相好一起幽会。她们在此干这一行已经有六年之久。每天晚上,我们都能见到她们,除了有时需要到圣拉扎尔或卢西纳医院接受健康检查。”
杜洛瓦再也听不进去了,因为此时有个女人用胳膊肘支在他们的包厢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是一个满头褐发的胖女人,脸上因为擦了厚厚的一层粉而显得特别白。她的眼睛很黑,眼角描得长长的,眉毛涂的很粗,显得十分突兀。深色的丝绸连衣裙因为丰满的胸部而高高拱起。涂了口红的嘴唇像带血的伤口,显露出一种过分热情的野性,但绝对能燃起男人心中的欲望。
她叫住从身边经过的女友,一个肥胖的、戴着红色发套的金发女人,故意大声地说话,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
“瞧!这儿有个漂亮的小伙子。如果他愿意出十路易,我决不会对他说‘不’”
弗雷斯蒂埃转过身,笑着拍了拍杜洛瓦的大腿:
“她这是说给你听的。她已经看上你了,我亲爱的朋友,恭喜恭喜。”
杜洛瓦的脸立刻红了,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块金币。
这时,舞台上幕布已经落下,乐池里响起了华尔兹舞曲。
杜洛瓦对他的朋友说:
“我们到走廊上去转转,怎么样?”
“随便你吧。”
他们一起走出包厢,立刻卷入走廊里的人流。他们被推挤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眼前晃动的是男士们戴的礼帽。那些妓女,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紧贴着男人的胳膊、胸脯和脊背,在他们中间自由穿梭,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她们的步履是那么轻盈、敏捷,恰似水中的鱼儿,游荡在这股由男人汇成的激流之中。
杜洛瓦有些难以自持,任凭人流将他推来推去。他贪婪地吮吸着弥漫在四周的烟草味、男人的汗味和妓女们的香水味,心神激荡,如痴如醉。一旁的弗雷斯蒂埃却大汗淋漓,不住地喘气、咳嗽。
“咱们去花园里透透气吧。”他说。
于是两人走进左边一个搭着凉棚的花园。花园里有两座巨大的喷水池,虽然设计粗糙,却给这里带来了一丝凉意和清新。花盆里栽着紫杉树和侧柏,一些男男女女正坐在树下的小桌边喝酒。
“再来一杯啤酒,如何?”弗雷斯蒂埃问道。
“好的。”
两人坐下来,看着从眼前经过的人群。
不时,有个在院里闲逛的妓女走到他们面前,微笑着问道:“能请我喝一杯吗,先生?”弗雷斯蒂埃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请你喝一杯喷泉里的清水。”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得转身离开,嘴里还骂骂咧咧:“去你的,没教养的家伙!”
过了一会儿,刚才依偎在他们包厢外的褐发女人又出现了。她挽着那个金发的胖女人,神情傲慢。这两个女人十分般配,真是一对尤物。
当她看见杜洛瓦时,莞尔一笑;四目相对,仿佛在传递彼此心中的秘密。她拉过一把椅子,泰然自若地坐在他对面,同时让她的朋友也坐下。她用轻脆的声音喊道:“侍应生,来两杯石榴汁。”弗雷斯蒂埃惊讶地说道:“你怎么这么没规矩?”
她回答道:“我看中的是你的朋友。他可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简直让我发狂”
杜洛瓦怯生生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傻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胡子。侍应生把果汁端上来,两个女人一饮而尽。随后,她们站起来。那个褐发女人向杜洛瓦亲切地点了点头,用手里的扇子在他手臂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道:“谢谢,我的小猫咪。你可真是金口难开啊。”
说完她们扭着腰身,摇摇摆摆地走了。
弗雷斯蒂埃大笑着说道:
“老兄,知道吗,你对女人有种天生的吸引力。你要好好利用这一点,这对你的前途大有好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有女人的帮助,成功也许会来得更容易些。”
见杜洛瓦只是微笑,没有做声,他问道:“你还想呆一会儿吗?我喝得差不多了,该回去啦。”
杜洛瓦小声说道:“你先走吧,我再呆一会儿,现在还不算太晚。”
弗雷斯蒂埃站起身,说道:“那么,再见了。别忘了明天晚上七点半,枫丹大街十七号。”
“知道了。明天见,谢谢。”
他们握了握手,记者先生转身扬长而去。
弗雷斯蒂埃一走,杜洛瓦立刻感到自由了。他再次兴奋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枚金币,然后站起身,重新走进人群。他东张西望,四处搜寻着。
很快,他又看到了刚才那两个女人。她们仍然带着那副傲慢的神情,在嘈杂的人群中寻找新的目标。
杜洛瓦径直朝她们走去。可就在靠近她们的时候,他有些胆怯了。
那个褐发女人对他说:“你现在愿意开口了吗?”
杜洛瓦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句“当然”,就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
三个人就这么站在路中间,阻断了走廊里的人流,身边很快聚集了许多人。她突然问道:
“你想到我家坐坐吗?”
杜洛瓦顿时激动万分,心中欲火难以抑制,立即回答道:
“当然愿意,可是我身上只有一路易。”
她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没关系。”
于是她伸手挽住他的胳膊,表示他今晚属于她了。杜洛瓦一边往外走一边盘算着,用身上剩下的二十法郎还可以为明天的聚会租一套礼服。
“请问,弗雷斯蒂埃先生住在几楼?”
“四楼左边那家。”
看门人的语气十分友好,表示出对房客的尊敬。乔治·杜洛瓦登上楼梯。
他有些慌乱,局促不安,感到浑身不自在。平生第一次穿上礼服,这身打扮让他觉得十分别扭,浑身上下都不对劲。尖尖的皮鞋漂亮精致,可惜没有上光;今天早上在卢浮宫附近花四法郎买的衬衣,因为料子太薄,胸口处已经破裂。至于平时穿的那些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就算最好的那件也穿不出来。
他的裤子有些肥大,不能显出腿部的线条,好像胡乱缠在腿肚上,皱皱巴巴的,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找来充场面的旧货。只有上衣勉强过得去,还算合身。
杜洛瓦慢慢地往楼上走去,心中忐忑不安,尤其担心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突然,他看见一位衣冠笔挺的先生正看着他。两人挨得如此之近,杜洛瓦不由往后退了一步。他惊奇地发现:二楼的楼梯口摆着一块高大的落地镜,而那位先生正是镜中的自己。此外,从镜中还可以看到整条走廊。杜洛瓦顿时欣喜万分,看来这身打扮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他家里只有一面用来刮胡子的小镜子,无法照出全身。今天这身临时凑合的打扮,也只是通过那面小镜子一部分一部分地看了看,不免夸大了局部的缺点。一想到有可能被人耻笑,他就焦躁不已。
可是刚才,当他突然在镜中看到自己全身的模样时,几乎认不出自己了。他竟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乍眼望过去,真的是器宇轩昂,英俊不凡。
现在,他又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起来,觉得这身打扮的确无可挑剔。
他像一个在琢磨角色的演员,自我研究起来。他对镜中的自己微笑、伸手,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做出不同的表情:惊讶、高兴、赞成。他努力揣摩向女士献殷情时,应该使用哪种微笑和眼神,以便让她们明白他的欣赏和爱慕之情。
这时,一扇门打开了。杜洛瓦害怕被人撞见,连忙上楼。他的心里惶恐不安,担心刚才的一切被弗雷斯蒂埃邀请的某位客人看见。
在三楼,同样有一面落地镜。杜洛瓦从镜前经过时,放慢了脚步,以便看清自己走路的样子。他觉得镜中的自己身材颀长,姿态优美,这让他信心十足。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外形条件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加上坚定的决心和独立的思想,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想着想着,杜洛瓦兴奋不已,恨不得跳上最后一层台阶。在四楼的镜子前,他再次停了下来,熟练地捻了捻胡子,摘下高筒礼帽,理了理头发,像平时那样喃喃自语道:“不错。”然后伸手按响了门铃。
门立刻打开了,对面站着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神态庄重且胡子刮得非常干净的仆人。见到仆人这身整齐的穿戴,杜洛瓦再次感到不安。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心神不宁,也许是他无意间拿自己的衣服和对方做工精细的衣服进行了比较的缘故。这时,脚穿漆皮皮鞋的仆人接过杜洛瓦因为害怕露出污溃而一直挂在手臂上的大衣,问道: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接着,他隔着身后半卷的门帘向客厅里的主人通报。
门后就是杜洛瓦梦寐以求的另一种生活。这时,他突然失去了镇定,心慌意乱,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但是,他最终还是跨出了这重要的一步,走了进去。一位年轻的金发女人独自站在客厅等候他。客厅很大,灯火通明,摆满了各种植物,像个温室。
杜洛瓦猛地停住脚步,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这位朝他微笑的女士是谁呢?接着,他想起弗雷斯蒂埃已经结婚了。杜洛瓦真不敢相信这位喜欢滔滔不绝的朋友会有如此美丽高贵的妻子。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夫人,我是……”那位女士向他伸出手,说道:“我知道了,先生。查理已经把你们昨晚重逢的事告诉我了。很高兴他能邀请您今天来我家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