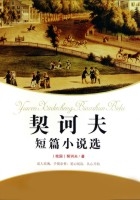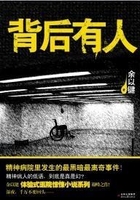晚餐和类似晚宴一样,毫无特别之处,客人们东拉西扯,尽说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杜洛瓦被安排坐在瓦尔特先生的大女儿,即长相丑陋的罗莎小姐和德·玛莱尔夫人之间。尽管德·玛莱尔夫人神态自然,谈笑风生,与平时并无两样,但杜洛瓦还是感到有点不自然。开始的时候,他感到心慌意乱,说话吞吞吐吐,就像找不着调的乐手一样。渐渐地,他开始恢复了平静。两人的目光不时地相遇,互相试探着;没过多久,他们又像以前一样眉来眼去,暗送秋波。
突然,杜洛瓦觉得桌子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的脚;于是,他稍微把腿往前伸了伸,不料碰到了德·玛莱尔夫人的腿,对方并没有缩回去。这时,两人沉默不语,若无其事地将身子转向各自的邻座。
杜洛瓦激动不已,把膝盖往前挪了挪;德·玛莱尔夫人也不动声色地做出回应。杜洛瓦知道,他们之间马上就要旧情复炽。
他们后来说了些什么呢?无关紧要。但是每次对视的时候,两人的嘴唇都在微微颤抖。
为了不冷落老板的女儿,杜洛瓦偶尔也会和罗莎聊上几句。女孩的性格和她母亲一样,说话干净利落,没有半点犹豫。
坐在瓦尔特先生右边的德·佩尔斯缪子爵夫人,一言一行始终保持着一副皇亲国戚的派头。杜洛瓦看着她,不觉好笑,于是压低嗓门向德·玛莱尔夫人问道:“您认识另外一位名为‘红衣女’的夫人吗?”
“您是指利瓦尔男爵夫人?认识。”
“也是这副模样?”
“不,但是性情一样怪异。此人六十来岁,身材瘦长,戴着一头假发,一口英国式的牙齿,思想还停留在复辟时代,就连衣着也是如此。”
“报馆到底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文坛怪人的?”
“资产阶级暴发户总是会收留一些贵族残余的。”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
这时,瓦尔特开始与两位议员及诺贝尔·德·瓦伦和雅克·里瓦尔谈起了政治。几位男士滔滔不绝地谈着,直到仆人送来甜点。
晚餐过后,客人们回到客厅。杜洛瓦走到德·玛莱尔夫人身边,紧盯着她的两眼,问道:
“今晚,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
“为什么?”
“因为每次来这里吃饭,都是拉罗舍一马蒂厄先生送我回去。我们是邻居。”“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明天中午来我家吃饭。”
说完,他们便各自走开了。
杜洛瓦觉得,再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早早告辞离开。下楼的时候,他碰到先他一步出来的诺贝尔·德·瓦伦;后者立即挽住杜洛瓦的胳膊。在报馆里,两人的工作分工不同,不存在任何竞争,因此,诺贝尔·德·瓦伦对这位年轻后生充满慈祥和关爱。
“怎么样,愿意陪我走一程吗?”他问。
杜洛瓦回答道:“无比荣幸,老前辈。”
说完,两人沿着马勒莎尔布大街,慢慢地往前走。
寒冷的冬夜,巴黎街头空无一人。一切都是那么辽阔,天上的星星显得更加遥远,夹杂在空气中的凛冽寒风也仿佛来自更加遥远的天际。
开始,两个男人谁也没说话。后来,杜洛瓦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随口说道:“拉罗舍一马蒂厄先生看上去很有学问。”
老诗人问道:
“您是这么想的吗?”
杜洛瓦一惊,吞吞吐吐地说道:“是的。大家都说他是众议院最有能力的议员”
“或许吧,不过这也是相对而言。难道您不知道,众议院那些人都是平庸之辈吗?他们思想狭隘,成天想的不是政治,就是金钱。亲爱的,他们只是徒有虚名,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这些议员的才智早已被淤泥掩埋,如同污浊不堪的塞纳河阿斯尼埃河段。”
“唉!要想找一个思想开阔、能够让你如沐春风的人,真是难上加难啊。我曾经认识几位,不过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诺贝尔·德·瓦伦的声音响亮清晰,但仍然有所克制,否则定会响彻寂静的夜空。他看起来有些激动和伤感。这些挥之不去的愁绪时常困扰着人们,让他们的心灵如同冰雪覆盖的大地一样,颤栗不已。
诺贝尔·德·瓦伦接着说道:
“管他呢!既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多一点人才和少一点人才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完,他陷入一片沉默。心情愉悦的杜洛瓦,微笑着说道:“亲爱的前辈,您今天怎么如此悲观呢?”
诗人回答道:“小伙子,我向来都是如此。等您到了我这种年龄,也会像我一样。人生就像一面山坡,当您往上走的时候,看到的是顶峰,内心就会充满希望;可是一旦到达顶峰,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可怕的下坡,终点通向死亡。上坡的时候,我们步履艰辛缓慢,可是下坡的时候,速度却很快。在您这种年龄,人人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尽管最后都是一无所获。可是到了我这种年龄,人们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只有等待……死亡的降临。”
杜洛瓦开始笑了起来:
“哎呀,您的话真让我有些害怕。”
诺贝尔·德·瓦伦继续说道:
“现在,您还无法体会。不过总有一天,您会想起我的这番话。要知道,人人都会有这么一天。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天来得很早。到那个时候,正如常言所说,谁也笑不出来了;因为透过他们眼前的一切,所看到的只有死亡。唉!您现在还不明白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死亡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遥不可及;而对于我来说,却非常可怕。是的,死亡的意义,人们总是突然之间明白,谁也不清楚其中的道理和缘由。然后,生活中的一切都会随之改变。我感觉到死亡的存在,已经有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死亡的恐惧一直折磨着我,就像一只怪兽钻进我体内,慢慢地吞噬着我。我的身体日渐衰老,就像一栋逐渐腐蚀的房子,终有倒塌的一天;每个月,甚至每个小时,我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我的模样已经完全改变,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昔日的我,早已荡然无存。想当初三十岁的时候,我是多么容光焕发,精力旺盛;而现在,一头黑发已经变成满头银丝。衰老一点点地改变着你,过程是如此缓慢而又恶毒!以前柔韧的肌肤、强健的肌肉、坚固的牙齿乃至整个身体,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剩下那颗绝望的灵魂也将逐渐死去。是的,死亡正在一分一秒地、慢慢地吞噬着我;可怕的是,我根本无法抗拒。现在,无论我做什么,都能感觉到死亡的来临。每走一步,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次呼吸,好像都在加速奔向死亡。我们所做的一切:呼吸、睡觉、喝水、吃饭、工作甚至做梦,都是为了死亡。总而言之,生就是死!啊!您会明白这一切的!只要您用一刻钟的时间仔细想想,就会恍然大悟。我还能期待什么呢?爱情吗?哪怕只是几次亲吻,我都会感到力不从心。还有什么呢?金钱吗?我用它来做什么呢?养女人?想法倒是不错。或者大吃大喝,让自己变成一个大胖子,被风湿折磨得整晚呻吟?除了爱情和金钱,还剩下什么呢?荣誉?当你不能通过爱情去得到它时,荣誉还有什么意义呢?除此之外呢?就只剩下死亡了,这是我最后的归宿。现在,我感到死神就在身边,我常常想一把将它推开,可是它却无处不在。路上被压碎的虫子,树上飘零的黄叶,朋友胡须中的白毛,都会让我感到触目惊心;因为它们时刻都在提醒我‘死神,它就在这里’。死亡不仅毁了我所做的、所看到的、所吃的、所喝的;也毁了我所喜欢的东西:皎洁的月光、初升的太阳、浩瀚的大海、蜿蜒的河流,以及夏夜里沁人心肺的习习凉风。”
诺贝尔·德·瓦伦放慢了脚步,微微喘息着,整个人陷入一阵沉思,完全忘记了杜洛瓦的存在。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人的生命之火一旦熄灭,将永不复燃……东西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根据其模型或者残片进行复制。但是,我的身体、面容、思想以及欲望一旦消失,将永远无法再现。即使有新的生命不断降临,也和我一样,拥有鼻子、眼睛、额头、面颊和嘴,甚至一样的灵魂,但是我却不能复生。虽然表面有些相似,但实际上却有着千差万别,根本就没有我诺贝尔·德·瓦伦的影子。我们可以依靠谁?可以向谁倾述内心的痛苦?可以相信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无稽之谈,那些幼稚可笑的伦理道德和自私自利的许诺,实在愚蠢至极。只有死亡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说到这里,他停下脚步,抓住杜洛瓦衣领的两端,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伙子,好好想想我的话,想上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您会对人生另有一番认识。您应该摆脱生活的束缚,摆脱您的身体、思想、利益得失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将目光移向别处。那时您就会发现,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争论以及有关日常收支的争执,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诺贝尔·德·瓦伦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着。
“您会感到害怕、绝望,就像一个溺水之人,在生死未卜的困境中努力挣扎。您向四周高呼‘救命’,可是却没有人搭理您。您伸出一只手,希望有人拉您一把,希望得到关爱、帮助和安慰,但却无人前来。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因为这是命里注定的。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而不是更多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我们想得太多,日益提高的精神要求和一成不变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看看身边那些碌碌无为的人吧。除非哪天大难临头,否则他们只会安于现状,对人生的不幸毫无感触,与那些动物没什么两样。”
诺贝尔·德·瓦伦停下脚步,思索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疲倦的声音无可奈何地说道: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既无父母,又无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连上帝也没有他沉吟片刻,接着说道:
“我只有以诗为伴。”
说着,他抬头望向星空,对着一轮皓月,吟起诗来:
“黑夜漫漫,冷月孤悬,吾将上下探索追寻生命之谜。”
这时,他们来到协和桥。两人默默地从桥上走过,沿着波旁宫往前走着。诺贝尔·德·瓦伦说道:
“朋友,赶快结婚吧!孤独终老的滋味不好受啊。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可怕的孤独。每天晚上,坐在火炉边,只有孤独与我相伴。每当这时,我就会觉得世界上仿佛只剩下我一人,四周充满了隐隐约约的危险和从未见过的可怕东西。
隔壁虽然住着邻居,可是我们从不来往,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窗外的繁星一样遥远。痛苦和恐惧,尤其是四面无声的墙壁时常让我感到焦躁不安。独自一人生活,寂静的房间会显得格外幽深和凄凉;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都会笼罩在一片孤寂之中。每次家具发出干裂声,我的心就会随之一震;在这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任何声响都显得那么突兀。”
诺贝尔·德·瓦伦再次陷入沉默。过了一会,他说道:
“不管怎样,人到老年,如果有子女陪伴在身边,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这时,两人已经到达勃艮第街中段。诗人在一幢高楼前停下来,握了握杜洛瓦的手,说道:
“人老了就喜欢嗦,年轻人,忘记我刚才所说的话,按照你们这种年龄应有的方式生活吧,再见!”
说完,他便消失在黑漆漆的走廊里。
杜洛瓦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沉重。老诗人的一席话,仿佛让他看见一个堆满白骨的洞穴;总有一天,他自己也会被扔进去。他低声骂道:
“见鬼!德·瓦伦家里气氛一定很沉闷。要不是今天偶然相遇,我才没闲工夫坐下来听他这番唠叨呢!”
这时,一位浑身香气的女人从马车上下来,准备回家。杜洛瓦停下来,让她先走;同时贪婪地吸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用马鞭草和蝴蝶花调制的香水味。转眼间,他的内心重新充满了希望和喜悦,并且希望能够马上见到德·玛莱尔夫人。
现在正是他一帆风顺的时候,生活对他如此厚爱,让他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怎能叫人不兴奋呢?
这晚,杜洛瓦睡得特别香。第二天,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在布洛涅园林大街转了一圈,然后到德·玛莱尔夫人家赴约。
由于风向改变,夜间气温有所回升。这天早晨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常来布洛涅园林散步的巴黎市民,经不住明媚阳光的诱惑,纷纷跑了出来。
杜洛瓦悠闲地踱着步子,尽情吮吸着春天甜丝丝的空气。他穿过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走上一条宽阔的林阴大道,一群男女正在这里骑马散步。杜洛瓦看着这些骑士,或缓缓而行,或疾驰飞奔,毫无羡慕之意。现在,他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并对他们的财产和生活隐私了如指掌;记者的职业让他成为巴黎名人及其丑闻的年鉴。
这时,迎面走来一队女骑士。这些女人个个身材苗条,穿着深色紧身呢绒服装,习惯性地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神情。杜洛瓦一时兴起,像人们在教堂里念诵经文一样,低声罗列着她们的情人或者绯闻情人的姓名、头衔和身份。有时,他甚至不说:
德·唐克莱男爵
图尔一昂格朗亲王
而是把这些情人的其他情妇说出来:
滑稽歌剧院的路易丝·米肖歌剧院的罗丝·马克坦杜洛瓦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一旦剥去人们道貌岸然的外表,就可以看到隐藏其中的、男盗女娼的不变本性。杜洛瓦因为能够洞穿这一切而感到欣喜不已。因此,他大叫一声:“伪君子!”然后开始在骑士中搜寻最风流的一位。他们当中许多人被认为是赌场作弊高手;对这些人而言,俱乐部便是他们巨大的财源,也是惟一的财源,当然也是不太光彩的财源。
另外有些人,虽然出身名门,却靠太太的年金维持生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还有一些更惨,要靠情妇的年金养活。不少人已还清了债务(这当然值得尊敬),但没人知道这些钱是从哪里得来的(肯定不是通过什么光明正大的途径)。杜洛瓦还在骑马的人中间看到几位金融巨子;这些人最初靠偷盗发家致富,而现在却经常出入官宦富贵之家,备受推崇。此外,还有几位备受巴黎市民敬仰的人物。每次上街,人们都会向他们脱帽致敬;而他们在大型国有企业里干的那些厚颜无耻的勾当,对于了解上流社会内情的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人无论留着短髯,还是满脸络腮,个个盛气凌人,得意洋洋。
杜洛瓦冷冷地笑着,低声骂道:“卑鄙无耻!真是一群恶棍、强盗!”
这时,一辆由两匹小白马拉着的、低矮时髦的敞篷马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由于跑得很快,马鬃和长长的尾巴都飞了起来。驾车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金发丽人,社交界无人不晓的名妓。在她身后,坐着两个年轻的马夫。杜洛瓦停下脚步,很想上前和这位靠出卖色相发迹的女人打声招呼,为她鼓掌喝彩;因为她敢于在这些伪君子散步的时候,招摇过市,炫耀从床上得来的奢华享受。杜洛瓦隐约感到,自己和这个女人之间存在某种共同之处以及某种天然的联系;他们应该属于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灵魂。而他要获得成功,必须依靠同样大胆的手段。
杜洛瓦慢慢地往回走,心潮澎湃,并提前来到情妇的家。
一见面,德·玛莱尔夫人便抱着他亲吻着,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快。那一瞬间,她甚至忘记了不在家里和他亲热的谨慎决定。她一面吻着杜洛瓦微微上翘的胡子,一面说道:
“亲爱的,烦心事又来了。我本想和你过几天好日子,谁知道我丈夫突然请假回巴黎,要呆上半个月。我实在不能忍受六个星期见不到你,尤其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所以我安排你下个星期一到我家吃晚饭,我已经跟我丈夫提起过你,到时我将你介绍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