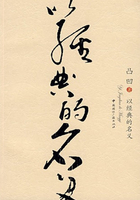艾伟:我想文学精神性是多方面的,想象力,飞离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复杂性,都是。就这部作品而言,如前所述,它同我以前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我现在的小说观念有所改变,我认为文学不是用来分析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部小说在《收获》发表后,我看到了很多读者写的文章,有人读时“数度哽咽”,读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其中有一个读者这么写道:“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无力以及内心的拯救。人性之美使悲剧又洋溢出暖意。我们是无力的,取舍并不取决于自身,但是我们一直在力求自身的问心无愧。杨小翼用一生的幸福赎回了对伍思岷的歉疚,她的此举引发我们不同体验层次的共鸣。这是我们的义。杨小翼最终在放弃中走向平静与释然,她放弃对血缘的执着,放弃对父亲的逼视;放弃相濡以沫的爱情,尊重和成全他人之爱——在这中间,杨小翼与刘世军的几度分手显得如此动人;最终她甚至放弃对丈夫的追问。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我喜欢这位读者写的这几句话,就一个读者而言,其从这部作品里得到的人生感受既感性又形而上,是整体性的。刘小枫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现代小说承担的是类似教堂里的喃喃自语,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所以,判别小说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读完后百感交集,无以言说。我想小说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动人,然后再判断其别的价值。现代学里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绽百出的小说,依旧可以分析出伟大的意义。我这么说是想强调精神性并不表明只有那些尖锐的态度才得以呈现,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广阔中亦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说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情感。
“谁不被历史捉弄”
——与王春林对话
王春林:艾伟先生,你好。作为一位长篇小说的跟踪研究者,我个人认为,你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应该是2009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收获。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2009年,恰逢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你的小说正好在这一年发表出版,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艺术地再现并深入追问反思共和国的六十年历史,可以被看做是你的创作动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你事实上采取了一种对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所以,首先想请你就这个问题展开谈论一下。
艾伟:和建国六十周年碰在一起纯粹是巧合,之所以写这部长篇同我自写作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有关。如果你读过我的《越野赛跑》或《爱人同志》等小说,你会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追问和反思1949年以来的历史。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时代意志”之下的人的境况。《越野赛跑》讲了两个时代,所谓“文革”时期的“政治年代”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年代”,小说在这两个年代下,探讨了人的欲望及其梦想、智慧及其愚蠢。而《爱人同志》则是80年代初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人被抛离的那种阵痛,我让一位被符号化的自卫反击战的残疾英雄和一位爱上英雄的圣女去承担这种阵痛,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刚好在时代的节点上。要说“正面强攻”,我的小说一直都是这样,历史一直没有缺席,我希望历史丝丝入扣地进入我的文本,希望探讨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的人性状况。我的认知是“人性”从来是历史的,我不相信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的“人性”。比如,当下人们的道德感肯定不同于别的时代,甚至同“文革”时也不一样,人性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似乎更愿意掩盖我们的善,恶似乎成了普遍真理。就《风和日丽》来说,是这种思考的延续。当然,你能感觉到,这部小说里,也有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方法,我珍视这些变化。
王春林:反思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切入方式,你所选择的,我以为是一种把对六十年共和国历史的追问反思纳入到一部成长小说模式中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样的理解对吗?如果对的话,请谈一谈你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艺术选择。
艾伟:这部小说选择了一个革命“私生女”的一生,选择了“私生女”这个视角,我也曾谈过这个视角对这部小说的意义,在此不谈。这部小说写了1949年到2000年五十年,因为杨小翼这样的身份,天然地和革命及其历史相关。但对我来说,我首先是想写一部“个人史”,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杨小翼的个人情感上,构成这部小说的主体是杨小翼作为女人一生要经历的种种情感,初恋、婚姻、婚外情、对父爱的渴望、对儿子的爱、友谊等等,这是这部小说的物质基础,所以,我愿意把《风和日丽》首先当成一部关于情感的小说。至于小说涉及共和国至今的历史及其反思,那也是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当然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更深层的内容。
王春林: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必须成功地塑造若干丰满鲜活的别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杨小翼是你用笔最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我觉得,小说中在艺术上塑造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却并不是杨小翼,而是杨小翼的父亲尹泽桂将军,是她曾经的丈夫伍思岷,甚至于还有尹南方。请问你是否同意上述判断?
艾伟:有一段日子,我重读过去读过的书。我发现,我喜欢的书都是古典作家的,简·奥斯汀、萨克雷、托尔斯泰等。我作为一个读者一次一次地被这些古典作家所创造的人物所感染,我感到古典小说真是一种情感丰沛的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当然,我也重读了一些现代主义作品,读现代主义作品,就没有这种“被感染”的感觉了。这样,我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区分古典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方法。当你用一种理性的不动任何情感的方法阅读时,你读的往往是现代主义作品。现代主义作品基本上是冷静的,分析的,寓言的,智力的,并且有几个核心的词:冷漠、孤独、异化等。现代主义小说几乎取消了戏剧性,我觉得戏剧性的取消同人物形象的取消有关的。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往往符号化,没了立体的有温度的人,当然你很难戏剧化。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说,现代主义小说真的是枯燥的。“先锋”以来,我们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对小说的基本价值有所忽视,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我想,无论如何,人物、情感、故事等都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根基,但我们现在似乎有点忽略这个常识。
你对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判断,我都没有意见。小说中的人物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非常个性化的,这种人物比较好刻画,形象也容易鲜活;另一种个性上相对中性一些,含蓄一些,暧昧一些。对写作的人来说,前一种比较好办,后一种则得下力气。杨小翼显然是后一种,她的丰富性在于她的情感,她向世界伸展的触角。
王春林:好像一般人都认为,对尹泽桂将军这一形象的塑造,是《风和日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对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但如果更深入地想一想,却又觉得,这个形象似乎不够具体。不知道你认为如何?此种情形的生成,是不是与他是共和国的领袖之一,而你在对领袖的生活进行艺术想象时,多少还是缺少了一点直接的生活体验有关?
艾伟:将军形象的刻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种艰难不在于生活体验与否,而在于你在中国写作,你写一个共和国领袖的私生活,你无法用一般的写实的方法,有很多禁忌在那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历险,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能说他是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你不能说这位开国将军官至哪级,你也不能写他究竟在哪个部门工作,你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将军”,否则你的书就无法面世。我完全有能力把他写得更日常一些,更具体一些,但那将招致非常大的麻烦。除了那些歌颂领袖丰功伟绩的主旋律作品,你见过我们的文学中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私人生活形象的作品吗?所以,在写作时采用的策略实际上是把这个人物寓言化的,让他若隐若现,但又笼罩全篇,他是本书的一个叙事动力,也是本书的一个主宰,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意外的效果,让将军有神秘感,也符合公众对大人物的想象。就风格而言,这是一种写实性和寓言性的结合,我也达成了我想表达的目标。即使像现在这样,在发表、出版时编辑也删节了关于将军的一些细节。本书曾有一则附录,是将军的一个官方年表,也被毫不留情地删去了。
王春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可能只是从杨小翼的“思父”,写到“寻父”、“认父”、“仇父”就够了。因为,一般的小说似乎都是这么构思的。但在事实上,你却在最后一直写到了杨小翼对自己生身父亲的深刻理解。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
艾伟:关于革命的书写,我们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像《青春之歌》这样的,完全是正面的,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写作,人物的行为逻辑完全按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演进。到了新时期,则对革命进行了反面的叙述,用的是解构的方式,像陈忠实和李洱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在《风和日丽》中,“革命”虽然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语,但我感兴趣的是革命之下的人性。我说过,《风和日丽》有一些新的元素,其中之一就是我怀着对人性的信任,所以,在书写过程中,当我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革命的时候,就出现了你说的所谓同情之理解。其实前两个阶段我们对革命的书写都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而我的方法是想脱离这种意识形态,用一种更公正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说起来,谁不被历史所捉弄?即使是历史规则的制定者,也在那种规则里家破人亡。我最后在将军身上发现了人性暖意,我认为这是这部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是的,这部小说里有“和解”。在这部小说里,杨小翼年华已老,她和这个世界采取的是一种平和的姿态。我认为她也只能如此,难道让这样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还和这个世界激烈对抗吗?确实有朋友批评说,这样做似乎把杨小翼一生的苦难一笔勾兑了。那朋友还说,如果杨小翼对抗到底会更有力量。我倒并不这样认为,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方法——他让拉里莎某天在街头失踪,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但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杨小翼人物内心的逻辑就是这样。
王春林:我觉得,伍思岷,是你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你把这一人物某种人性的扭曲变异,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请谈谈你对这一形象的看法。谈谈塑造这一形象的创作心得。
艾伟:长篇小说打动读者的要素之一是要有命运感。命运感说到底就是人物一直在发展,一直在成长。伍思岷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正直、上进,以天下为己任,血液里充满了“革命”因子的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但他命运不济,似乎总是倒霉。他既是“文革”的闯将,又是1989风波登高一呼者,最后死在异国他乡。他在小说里是个有命运感的人,所以容易令人感慨。
王春林:既然是对于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正面强攻”,那很多历史场景与历史人物就是无法回避的。别的更敏感性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只说你对于如同北岛、舒婷、顾城等一代朦胧诗人们的形象所采取的多少有点漫画式的艺术处理方式,恐怕就会引起不少读者的争议。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艾伟: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成了很多人感兴趣的每次我都要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不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就是北岛和顾城他们,你会发现,其中的形象和实际相差还是挺大的。其次,我当时决定把这些时代先知写入小说是为杨小翼服务的,因为杨小翼后来要成为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她的思想必要有来源。再次,在这部小说里,这些人物的加入增加了时代氛围。我们这代人可能对80年代有记忆,其实更年轻一代对当年的历史事件早已淡忘,如果这部书能流传下去,以后的读者更是不会想起曾经的朦胧诗事件,而会把北原和舒畅当成纯粹的小说人物。我不认为这些人物是漫画化的,当你排除“对号入座”的杂念后,这些人物是成立的,有他们自己的行为逻辑。
王春林: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杨小翼既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曾经的丈夫与情人,可以说,你所采取的此种结尾方式,能够让读者联想到《红楼梦》中所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来。请问你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要把杨小翼的一切都剥夺殆尽?但就在这时候你却描写杨小翼周围的自然景致是“风和日丽”。小说标题很显然由此而来,我觉得其中有着鲜明的反讽意味。你是否同意此种说法?请展开谈论一下好么?
艾伟:我倒认为杨小翼并没有被剥夺殆尽,她至少是个成功的学者,她和刘世军绵长一世的情谊也并未失去。以她这样的年纪父母逝去也属正常。最惨痛的是儿子的死。这对她来说确实相当残忍。我同意王侃兄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能带来宁静的。在死亡面前,任何事都是渺小的。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充满了电闪雷鸣,但我用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名字,其中当然有反讽之意,不过,我认为这个词也代表着苦难时光中人性的善。在这部小说里,除了吕维宁,实在找不出一个所谓的“坏人”,但人人在受苦。我认为在苦难世界里就是那一点点人性的暖意支撑着人们,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就是“风和日丽”的时光。
王春林:书写共和国的六十年历史,“革命”无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词,事实上,对于“革命”问题的深入反思,可以说正是你的这部长篇小说最核心的内容所在。不仅如此,近些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许多关于“革命”问题的新说法新思考,请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个人体会与认识。
艾伟:关于革命的想法,我在小说中多有表述,在此不赘。从情感上说,革命曾经是一尊神,笼罩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这尊神倒下后,当然会在我们的精神深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延续,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具体而微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都能找到“革命”这尊神的影响。我也曾遇到过一些充满激情的朋友,至今谈起革命来都会热血沸腾——从人性的意义上来说,革命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风和日丽》是一部关于“父亲”的小说,革命就曾经是我们的父亲,当革命被告别后,我们都成了孤儿。这个时代,中国人没有信仰,大家成了孤魂野鬼,这就是革命的后果,曾经的光耀消失,对未来的承诺落空,广场上的人群撤离,留下一片废墟。
王春林:最后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的主攻方向吗?如果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还会是历史长篇小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