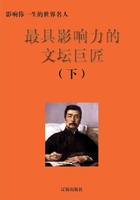在最近十数年内,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中有很多情况使一切形容词和理论思考都将失去分量。人们为对付这些情况作出的努力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每个人对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这取决于构成人的个性的那些难以琢磨的因素。
中欧和东欧千百万人复杂的命运之途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人因其职业观察到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我仅抓住几个典型,试图勾勒出东欧作家的画像。
这个我称之为阿尔法的人,是易北河(Elbe)东岸较为着名的散文作家之一。阿尔法曾经是我的一位挚友,我们曾一起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这些记忆使我们紧密相连。每每想到他,我便难以平静,甚至会扪心自问,我是否有必要这样剖析他。但我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不能因为朋友之情,就妨碍我撰写一篇讲他的着作的文章,有关他的着作我在下文中会多多少少说出我该说的话。
“二战”之前,阿尔法是个高挑瘦削、戴着一副角质眼镜的青年人。他在某个右派周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这份刊物在华沙文学圈子中并不太受欢迎,因为那时组成华沙文学圈子的主要是犹太人和其他一些对该刊物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立场表示不满的人。周刊的编辑虽然是偶然发现阿尔法的,但他有理由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阿尔法的才华在这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不久之后周刊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该长篇小说在一家较大的出版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
阿尔法这本书主要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当时许多年轻作家都受约瑟夫·康拉德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原名JózefTeodorKonradNaczKorzeniowski,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特务》等。小说魅力的影响,阿尔法对康拉德的写作手法尤其着迷,因为他擅长塑造雕像般的和僧侣型的人物。夜晚对阿尔法另有一种魅力。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微不足道却带有强烈情感的人们,在黑夜里活动,黑夜的沉寂和神秘气氛宛如硕大无朋的帷幔笼罩着他们的命运——这就是阿尔法经常描绘的戏剧场面,尽管他从未写过剧本,只写过长篇和短篇小说。他的早期作品描写非人的冷漠世界的庞大、宏伟和沉默,与康拉德的作品有诸多共相。阿尔法的立场曾是形而上的和悲剧性的。使他备受折磨的是纯洁问题——既有道德的纯洁,也有他所写的东西格调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他想让自己的每句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描写,而且要成为乐曲中无法替代的乐句,令人听上去有一种悦耳音响的效果。这种对纯洁性,我想说的是,这种对超凡脱俗的纯洁性的追求曾经是阿尔法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因为,在与别人相处时,他常常显得十分傲慢和不自然地做作。他在写作中追求纯粹,这与他个性中的高傲紧密结合;这是阿尔法本人的精神升华,是他的另一个我,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转移到第二个我上。他越为自己的个人生活不上轨道担心着急,便越是看重对他而言具有补偿意义的写作活动,越是给这种活动赋予庄重仪式的意义。有人评价他时曾说,阿尔法在提笔写作之前,就穿一件术士的拖地长袍,更像是一位身着红色僧袍的主教。这种尊严能满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是红衣主教才具有的。在他看来,举止缓慢,身披飘拂的猩红色绸袍,手戴供别人亲吻的戒指,这就是一种纯洁的风度,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所表达出的更高尚的自我。那些扮演滑稽角色的喜剧演员,一生都梦想着能去扮演某种最庄重、最具尊严的角色;在他身上起作用的便是某些类似的动机。阿尔法在与人们交谈时,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幽默感,而当提笔写作时,他却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他会沉浸在最严肃的悲剧情感之中。他野心勃勃,不仅想做一个因为写了一本好书而成名的作者,同时还希望赢得更大的声望。他想成为作家——成为一个道德权威。
我所提及的长篇小说,就是使他首次获得极大成功的那部作品,那部作品作为天主教小说而受到大肆宣扬,阿尔法本人则由于这本书而赢得最有才华的天主教作家称号。在像波兰那样的天主教国家能得到这一声誉非同小可。其实很难确定他是否真的是个天主教作家,因为在20世纪,天主教作家人数并不多。所谓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令人怀疑的,与那些临时皈依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作家没有什么区别。
同时我也不敢确定阿尔法是否曾是天主教徒。尽管那时我们时常见面,还进行过一些最坦诚的交谈。应该说,他曾是一个与大多数人相类的天主教徒,那是一个大家都对托马斯主义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Aquinas,1225-1274)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发生兴趣的时代,每每在文学讨论中都会援引雅各布·马利丹雅各布·马利丹(JacquesMaritain,1882-1973),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的理论。如果说所有这些“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文学上的一时风气,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能把一个行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捆稻草的绝望手势说成仅仅是一种时髦。可是如果认为这些玩弄托马斯主义术语进行的文学争论,是天主教精神的体现,这样的观点同样不正确;因为他们离完全接受天主教连带所有的后果还相距甚远。即便如此,“天主教知识分子”还是给某些文学圈子增添了自己的色彩。他们在政治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们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劲敌;他们完全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作家和记者,那些人在政治思想上没有摆脱对所谓“健全的制度形式”(如意大利和德国)的崇拜,也没有摆脱对“排犹活动”的赞许。共产主义者带着厌恶情绪看待雅各布·马利丹的影响,将其视为一种退化变质的标志,但是他们对“天主教知识分子”则表现得比较宽容,因为这些人对极右派的思想怀有敌视情绪,故而没有受到他们毁灭性的打击。阿尔法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就经常造访“天主教知识分子”和左派的圈子。由于受到周围人所持观点的影响,加之他一直试图作为一个严肃的道德权威在作家中发挥作用,阿尔法断绝了与右派周刊的来往,并在一封抵制“排犹活动”的集体公开信上签名。
每个人都在天主教中寻找某种不同的东西。对阿尔法来说,由于他对世界的悲剧性感受,他在天主教中寻找的是形式:词语、概念,简言之,就是作品的纹理结构。阿尔法的悲剧感使得他有点像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的“隐身人”《隐身人》(TheInvisibleMan),描写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格里芬发明了一种隐身术,把自己变成了来去无踪的隐形人。这天才的发明并没有给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带来任何欢乐,反使他屡遭灾难,以致他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狂,且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当他想出现在人群中时,他就必须给自己用糨糊粘上一个假鼻子,然后用绷带缠起面部,并给他那双看不见的手戴上手套。天主教提供的语言包括:诸如原罪、圣洁、罚入地狱、灵魂的黑暗和圣宠这类概念,通过这些语言的运用,他能抓住他所描绘的人物的感受,而最为重要的是,天主教的语言能立刻融入昂扬的语调,这种语调是阿尔法所需要的,用以满足他对主教猩红色僧袍的思念。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牧师,无疑,这是受法国天主教小说家的影响,首先是受贝尔纳诺斯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Bernanos,1888-1948),法国小说家、政论作家。生于巴黎一个西班牙血统的天主教徒家庭,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与文学,曾参与保皇派的政治活动,并成为《法兰西行动报》的活跃分子。1913年起主持鲁昂的《先锋》周刊,并撰写社论。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阿尔法急切地想要创造出纯洁而又坚强的人物形象的愿望。故事情节发生在农村;也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了阿尔法的才华弱点。他在着迷于设立道德冲突的同时,却有一双训练不足的眼睛:缺乏对生活细节和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观察;他自幼在城市长大,对农民及其生活知之甚少。因此,他所描绘的村庄往往是没有地域特色的普世化的村庄,把它说成是布列塔尼布列塔尼(Bretagne),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首府是雷恩。或佛兰芒佛兰芒(Fleming),位于比利时东北半弗兰德地区。的村庄,也未尝不可,因此并非现实的村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穿着与其身份并不相符的服装(就像牧歌文学时代的作品中将贵族少爷打扮成牧人一样),他们的谈吐也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因此戏剧是在一种勉强画出轮廓的布景中演出的。但作品情节发展紧凑有力,受到了批评家们的热情欢迎。不仅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而且几次再版销量也很大。阿尔法还因它荣获一项国家奖以及一笔可观的奖金。可能评委们在评奖时,不仅是考虑到阿尔法的作品在艺术上的长处,而且还考虑到给阿尔法授奖会带来某些政治利益。那些年代,政府当局显然是在跟极右派调情;给天主教作家阿尔法颁奖似乎是聪明的一招;右派当然会比较满意,而自由派也不好说什么,左派也没有理由攻击授奖的决定,因为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并据此写作。
尽管阿尔法有了声望和金钱,可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可称为好书。当然,他所赢得的地位允许他继续表现他所喜好的那种傲慢。他被人隆重地宣布为深刻、高尚文学的创作者,而他的同行几乎不可能指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他们的作品只能作为低廉的作品问世。他们的作品或者带有一种炫耀式的自然主义描写,尤其是在对生理范畴的某些现象的描写上,或者是披上长篇小说形式外衣的心理学论文。文学家们生活在自己的咖啡馆那种知识分子孤立封闭的小社会,他们越是与广大群众的生活脱节,他们作品的风格就变得越是离奇,越是难于被人们理解。阿尔法自己感到莫大的困惑:为何他的第一批作品出版后会在他心中遗留下不快的感觉,对此连他自己也无从解释。后来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刻,成了决定他日后生活的转折点。他心中充满了疑虑。如果说他的那些同行也在怀疑他们自己悬在虚空中的作品的价值,那么阿尔法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怀疑更甚。他想达到道德上的纯洁,但是要使这种纯洁是真实的,那它就必须是尘世的,就必须深深植根于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否则就是虚假。阿尔法觉察到自己已经滑落进一种虚假之途,因为他是生活在关于人的理想之中,而不是处在活生生的人中间。他对人的了解,是基于他在自己房间四壁之内的主观体验。他的天主教信仰只不过是他所使用的假面具而已。他是在戏弄天主教,他就像许多20世纪的天主教徒那样,试图用受人尊敬的旧派长袍来替自己遮羞,掩盖自己赤裸的身体。他曾寻找某种途径,以便在读者心中激发他所期望的感情反响。很明显,他的读者,在读到这些他们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字眼——“圣宠”或“罪恶”的时候,自然反应强烈。但是作者在这样运用辞藻和概念时却让人觉得是一种滥用。阿尔法怀疑自己设置的冲突的真实性。他被别人称为天主教作家,但他自己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像一个画家在某一时期从事过立体派绘画,而当他改变画风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人们仍然称他为立体派画家。那些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批评家,将他的写作归为健康的和崇高的文学,与他那些同行的具有颓废派特点的写作对立了起来。但他自己明白,他根本不比那些同行更为健康,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自己可悲的赤裸掩藏起来。
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变成了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从任何经验或文学中所能认知的范畴。我可以断定,那时我们所看到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大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过去熟知的有关大屠杀恐怖的描写,现在只能使我们觉得可笑,就像孩童时代所听到的故事,是那样天真幼稚。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他们对东欧的统治更加残酷无情,因为在东欧生活着不同种族,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这些种族,要么是该彻底灭绝,要么就该被利用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但是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努力去写作。诚然,每过段时间我们当中就有人离开,不是被遣送到集中营就是被枪毙。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这些人就像被困在一块漂浮的正在消融的冰块上,根本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会完全融化。战争公报宣布了我们这个种族最后的死期,我们在和死亡赛跑,但我们仍应坚持写作,因为这是我们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此外,在整个国家到处布满了地下活动网,同时的确存在着“地下国家”,既然如此,那么地下文学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虽不允许以被占领国的语言出版任何杂志或书籍,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地下出版物有油印的,或者是非法出版,形式常常是便于发行传播的杂志、小册子和小开本的书籍。还组织过许多地下演讲和作者见面晚会,甚至还上演过一些地下戏剧。这一切都大大地鼓舞了虽然失败但仍在坚持战斗的民族的士气。民族斗志昂扬,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民族斗志更是激昂,甚至有点儿过分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