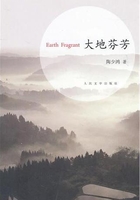十月的某个早晨,我离开巴黎的前几天,正当我在用早餐的时候,有个老头走进了我的家,他一身衣服已磨损得破旧不堪,鞋上沾了不少泥浆,两条罗圈腿,一副罗锅腰,细长的腿支撑着哆哆嗦嗦的身子,就像一只拔光了羽毛的鹭鸶。来者乃毕克休也。是的,巴黎同胞们啊,就是你们的毕克休,那个又尖刻又可爱的毕克休,十五年来,这位疯疯癫癫的讽刺家,用他的漫画与讽刺小品,常把你们逗得乐不可支……哎哟!这可怜的家伙,怎么潦倒成这个样子!要是他进门时没有做怪脸,我敢说怎么也不会认出是他。
他的头歪在肩膀上,嘴里咬着一根手杖,像叼着一支单簧管,这个昔日名扬巴黎、而今悲惨落魄的讽世者,一直走到我房间的中央,碰撞在一张桌子上,惨兮兮地说了声:
“可怜可怜一个倒霉的瞎子吧!……”
我觉得他在假装瞎子,竟装得那样逼真,不禁大笑了起来。但他冷冰冰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在闹着玩,你瞧瞧我的眼睛。”
他转过身来,让我看他两只无光的发白的眼珠:
“我已经瞎了,亲爱的朋友,这一辈子再也看不见东西了……你瞧,这就是用硝酸水写字的后果,我这个好行当硬是把我这双眼睛烧瞎了,一直烧穿了底。”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他的眼皮给我看,那上面早已烧得连一根睫毛的影子都没有了。
我很难过,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我的沉默使他有点不安:
“你在工作吗?”
“不,毕克休,我在吃早饭,你也跟我一道吃点?”
他不作回答,但从他那两扇翕动着的鼻翼,我知道他想吃得要命。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我的旁边。
当给他端早点的时候,这可怜的家伙在桌子上嗅来嗅去,脸上露出微笑,说:
“这些东西好像都很好吃。我要好好饱餐一顿;很久以来,我就从没有正式用过早餐了!我每天早晨老是带着一个铜子一块的面包,在各个衙门里奔走……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老要跑衙门;这成了我唯一的职业。我想找门路开一家公卖烟草店……有什么办法呢?一家老小总得有饭吃。我不能画了,我也不能写了……我口授,叫别人记录?……但口授什么?……我脑子里早就是空空如也;现在也想不出任何东西来。我原来的职业,不过是观察巴黎的种种鬼脸丑态,然后把它们画下来,现在,我没有法子了……于是,我想到去开一家公卖烟草店;当然,不是在繁华热闹的街面上,我可没有资格得到那种优待,因为我既不是走红舞女的妈,又不是高级军官的遗孀。不,我只想弄一个外省的小公卖店,离巴黎远远的,不管在哪里,在伏日山区某个偏僻的角落也行。到那时,我嘴里叼着一个瓷制大烟斗,改名换姓叫汉斯或泽伯兑,就像艾克曼与夏特良①的小说中的人物,我会把同时代作家写的书,拿来当烟叶的包装纸,以此来缓解我自己不能再写作的妒怨。
①艾克曼 (1822—1899) 与夏特良 (1826—1890),法国两个合写小说的搭档作家,有小说作品三十余部,皆以阿尔萨斯省风土人情为题材。
“我全部的小算盘不过如此,要求不过分吧?但要达到这点目的,可难如上青天……说实在的,可以给我帮上忙的人并非没有,我过去曾红极一时,经常应邀到元帅、王公、部长的府上吃饭;这些人常邀请我,是因为我能叫他们开心,或者我叫他们有几分害怕。现今,谁都不怕我了。唉,我的眼睛哟,我可怜的眼睛!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请我去吃饭了。饭桌上有一个双目失明的人,那是多么煞风景的事。请您把面包递给我,谢谢……啊!那些狗强盗,为了这个可怜的烟草公卖店,竟要叫我吃够苦头。这六个月来,我带着我的呈文跑遍了所有的衙门。每天早晨,当工友们生炉子、仆人们在院子里沙地上给部长遛马的时候,我就到了,直到天黑我才离开,那时,大盏大盏的灯都已经点亮,厨房里也飘出一阵阵香味来……
“我的日子就是这么在候见室里装劈柴的箱子上白白地度过的,那些门房也都认识我了!在圈子里他们都称呼我为‘这位好好先生’!而我,为了得到他们的关照,常给他们讲些小笑话,或者,在他们的吸墨纸的一角上,用一笔勾画出各种大胡子形象,逗他们哈哈一笑……这就是我享有赫赫盛名二十年之后的潦倒境地,这就是艺术家的可怜下场!……但是,眼下在法国,却有四万个青年人对我们这个职业行当馋得流口水!在外省,每天都有一个火车头开动起来,给巴黎送来一批批糊涂虫,他们爱好文学,爱好印成白纸黑字的流言蜚语,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唉,天真的外省人啊,但愿我毕克休的潦倒,能成为你们的前车之鉴!”
说到这里,他埋头在自己的盘子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再说话……他那副样子看起来真叫人可怜。每一分钟,他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是找不着面包或叉子,就是用手去摸索酒杯。这个可怜的人,他还没有养成盲人那一套习惯动作。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起话来:
“您知道吗,我还有一件更难受的事,那就是再也不能看报了,不干我这一行的人不可能理解这种痛苦……有时,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总买上一份报纸,只是为了闻闻报纸油墨未干的香味与那上面新鲜消息的气息……多么好闻呀!但没有人把报纸念给我听!我的老婆完全识字,她却不愿意给我念,她说,在社会新闻栏里,总有一些不堪入耳的消息……这些娘们,过去都给人当过姘头情妇,一旦结了婚,再没有比她们更假正经的了。自从我把这个女人扶正为毕克休太太之后,她便自以为应该特别虔诚正经才是,但瞧,虔诚正经到了何等地步!……正是她逼我用沙莱特①那里的所谓圣水擦眼睛!此外,还 有什么神祝福过的面包啦,给教堂捐款啦,读《耶稣降生记》啦,中国小瓷菩萨啦,虔诚的花样繁多,我说也说不全……总而言之,我跟她都埋在虔诚的善行义举之中了……给我念念报纸,这也总该是一种善行义举吧,但不,她偏不肯做这一件。要是我女儿在家,她是会念报给我听的,但是,自从我瞎了以后,为了家里少一口人吃喝,我把她送进艺术圣母修道院了……
①法国山区一小镇,传说圣母马利亚曾在那里显圣,该地的泉水可以治百病。
“我总算还有一个叫我高兴的人,这就是我女儿!她到世上还不到十年,各种各样的病她都得过了……这孩子性格忧郁,又长得很丑,可能比我还要丑……简直就是个丑八怪!有什么办法呢!我从来就只会制造各种各样的丑角……唉,我太老实了,把。我的家底都给你抖出来了,所有这些与你有何相干?……算了,不谈这个,请再给我一点烧酒。我需要再接再厉,从您这里出去,我要到公共教育部去,那里的门房可不容易逗笑,他们过去都是教书先生。”
我给他又斟了些烧酒,他小口小口地品尝起来,脸上流露出感激涕零的神情……忽然,不知他突生何种念头,他站了起来,手举酒杯,那颗像瞎眼蛇的脑袋环顾了周围一会儿,面带着一个即将致辞的绅士所惯常有的微笑,然后,尖起嗓门,就像在一个有二百人的宴会上,开始喊起来:
“为艺术干杯!为文学干杯!为新闻事业干杯!”
接着,他来了一篇十分钟的致酒词,这是一篇狂热的令人赞叹的即席演说,是这位滑稽家从未有过的妙作。
请您想象一下,眼前有一篇标题为 “一八六……年文学概况”的年终述评,上面是这么讲的:在文艺界,自吹自擂的文学集会此起彼伏,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争论吵架从未停歇,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种种怪事成堆,文字粪便不断排出,整个领域黑暗凄惨,像是地狱,但又缺少惊心动魄的气概,在这里,人们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互相坑害,文人才子们讨价还价、争财争利的嗓门,比小市民堆里的更高,尽管存在所有这一切,但文艺界里却到处有人饿死,比其他领域更多;虽然,这个领域里我们这批人都有种种卑劣污浊、软弱无能的毛病,虽然我们之中那位爱买彩票的 T. 男爵老先生,穿着淡蓝色的衣服、手持木钵,跑到了杜伊勒里宫去求乞;而到年终我们当中有成批成批的人死掉时,虽然葬礼有广告大肆加以宣传,致悼词总有一位议员先生出面,悼词中也少不了“亲爱的令人怀念的,可怜的亲爱的”这些陈词老调,但死者的丧葬费却无人肯付!再说,每年还有一些自杀的,一些发疯的……这样一篇年终述评,由一个天才的滑稽大师指手画脚、绘声绘色地宣讲出来,这就构成了毕克休这篇即兴演说。
他致辞完毕,酒杯也喝空了,他问了问时间,拍屁股就走,粗野无礼,连告辞的话都没有说一声……迪吕伊①部长先生的门房那个早晨是怎么接待他的,我不得而知;但我记得很清楚,这可怕的瞎子那天走出我的家门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忧伤与难受。我的墨水瓶叫我恶心,我的笔叫我厌恶,我只想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去看树木花草,去呼吸新鲜空气……老天啊,多么强的仇恨,多 么大的怨气!有什么必要这样辱骂一切!把所有一切都抹得黑黑的!这个混账瞎子……
①迪吕伊 (1811—1894),曾任法国教育大臣。
我怒气冲冲大步在屋里走来走去,毕克休跟我谈论他女儿时那冷嘲热讽的声音,似乎犹在我的耳边。
忽然,在瞎子刚才坐过的那张椅子旁边,我发觉有件东西在我脚下滑动。低头一看,原来是毕克休的文件包,这个包油亮油亮的,四角已被磨破,毕克休从不离身,他曾笑称是他专用来装毒液的。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毕克休这个包与吉拉尔丹②先生的档案夹同样出名,据说,那里面装了好些可以使人名誉扫地的材料……机会难得,我不妨来证实证实。这老掉牙的文件包装得太满,掉在地上时,已经散开了,里面的文件撒满一地;我只得一张一张把它们拾起来……
②吉拉尔丹 (1806—1881),法国当时著名的报人。
其中有一束信件,是用印花纸写的,每封信的开头都是: “我亲爱的爸爸” ,末尾都署着: “瑟丽娜·毕克休,于玛利亚孤儿院。”
文件里还有一些医小儿疾病的旧药方,什么病都有:支气管炎、抽风、猩红热、麻疹……那可怜的小姑娘,任何一种病她都没有躲过!
最后,一个封了口的大信封,从那里面露出两三根鬈曲的黄头发,就像从小女孩的软帽下露出来的一样,信封上歪歪斜斜写着一行大字,一看就是出自瞎眼人之手:
“瑟丽娜的头发,剪于五月十三日,她进那儿去的那天。”
看!这就是毕克休的文件包里装着的东西。
算了吧。巴黎人啊,你们跟毕克休是一个样。对一切都憎恶反感,凡事无不冷嘲热讽,冷笑起来恶毒得很,嬉笑怒骂起来,凌厉刻薄之至,但是到头来,下场也是如此:
“瑟丽娜的头发,剪于五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