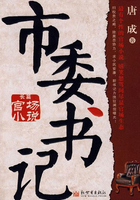这天早晨一打开门,只见我的磨坊周围已铺上了白色霜冻的地毯。小草闪闪发亮,像玻璃那样清脆作响;整个山冈都冻得哆哆嗦嗦的……我亲爱的普罗旺斯竟也变成了一派北国风光; 在挂着流苏般冰凌的松树林中,在开出一束束水晶般花朵的薰衣草丛中,我写出了两首颇有日耳曼情调的散文诗,写诗的时候,冰霜向我闪耀着白色的晶光,天上一片晴空,雁群排成三角形,从海因利希·海涅的故乡飞来,向卡马尔格方向飞去,不断地高叫:“天冷了……天冷了……”
王太子之死
年幼的王太子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王国之内,所有的教堂不分昼夜,都供奉着圣体,烛光通明,祈求着小王子早日康复。古老京城的街道上,凄凄惨惨,冷冷清清,钟声沉寂,车马缓行……在王宫的外面,好奇的老百姓眼光穿过栅栏,盯着那些身披金甲、带着严肃神情在院子里交谈的御前卫士。
整个宫廷都惶惶不安……内侍们、总管们在石阶上跑上跑下……条条走廊上都站满了侍从仆役与身着锦绣衣袍的朝臣,他们来回串堆,低声地探听消息。……在宽大的台阶上,王室贵妇们行着屈膝礼,用漂亮的绣花手绢拭擦眼泪。
在橘橙大厅里,有一大群穿长袍的御医,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他们挥动黑色的长袖,把戴着假发的脑袋,一本正经地凑在听诊器上……王子的太傅与马厩总管在门前踱来踱去,正等待御医的诊断。厨房小厮毫无礼貌地在他们身边来来往往……马厩总管像异教徒似的对神明骂骂咧咧,太傅则念诵贺拉斯的诗句……就在此时,从马厩那边,传来一声凄厉的长嘶,这是王子的栗色御马因为被马夫遗忘了而在空空如也的马槽前悲鸣。
那么国王呢?国王现在在哪里?……国王正把自己单独关在宫殿深处的一个房间里……天下任何一个至尊天子,都不愿意让旁人看见自己哭泣落泪……而王后,那就不同了……她正坐在小王子的枕旁,美丽的脸上泪水纵横,她当着众人的面,号啕大哭,就像一个可怜的纺织姑娘。
躺在带花边的小床上,小王子的脸色比被褥更为苍白,他静卧不动,双目紧闭,旁人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不然,小王子根本就没有睡着……他翻身朝向他的母亲,见她在哭泣,便问道:
——“母后,您为什么哭?是不是您真的认为我要死了?”
王后想作回答,但她泣不成声。
——“您别哭啦,母后。您忘了我是一国的太子,而太子是不会就这么死去的……”
王后哭泣得更厉害了,小太子不由得也害怕起来。
——“哎呀,我可不愿意死神把我抓走,”王子说,“我知道怎么阻止死神到我身边来……立即调来四十名德国雇佣兵,守卫在我的床四周!……再调来一百尊大炮,日夜值勤,炮弹上膛,架设在我的窗下!死神要是胆敢走近我,那就让他粉身碎骨……”
为了叫小王子安心,王后打了个手势。立即,大炮在院子里的滚动声隆隆可闻; 四十名雇佣兵手执长槊迅速布卫在房间的四周,他们都是蓄着灰色胡子的老卫士。小王子一见就鼓掌欢迎,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招呼道:
——“罗朗!罗朗!”
那个卫兵朝床前跨出一步,王子说:
——“我爱你,我的老罗朗……亮出你的大刀来……如果死神来抓我,你就把他砍死,是不是?”
罗朗答道:
——“是的,阁下……”
说着,两行泪珠在他蜡黄的脸颊上滚流而下。
这时,牧师走近小王子,对他低声念念有词了好久,并且把耶稣受难十字架出示给他看。小王子带着十分惊讶的神情听着他,突然把他打断:
——“您讲的这些话,我都很懂,神甫先生;但是,难道我的小朋友具波不能代替我来死吗?我可以给他好多好多的金钱……”
牧师继续对着他低声地讲道,小王子的神情愈来愈惊讶。
牧师讲道完毕,小王子叹了一大口气,回答说:
——“神甫先生,您对我讲的这些话,确实叫人伤心;不过,有一点对我很有安慰,那就是到了那边,到了布满着星星的天堂里,我仍然是王太子……我知道仁慈的上帝是我的表哥,他不会忘记按我的身份来接待我。”
接着,他又转身对他母亲说:
——“叫人把我那些最漂亮的衣服都拿过来,把我的白貂皮上衣、我的天鹅绒鞋子都拿过来,为了显示我的尊贵,我要穿着王太子的服装进入天堂。”
牧师第三次俯身向小王子,又低声对他讲了好久……正当他继续讲道时,小王子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朝他嚷道:
——“照您这么说来,作为一个王太子,就跟平常人那样一钱不值?”
说着,小王太子什么话都不愿意再听,一翻身朝向墙壁,伤心地大哭起来。
县长下乡
县长先生外出巡回视察。车夫开路,仆役后拥,县政府的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他威风凛凛朝仙女谷地区展览会奔去。为了这个很有纪念性的日子,县长先生穿上了他漂亮的绣花礼服,戴上了折叠式高顶大礼帽,着一条镶有银线的紧身裤,佩一把柄上嵌有珍珠的贵重宝剑……他的膝上,放着一个皮面刻有花纹的大公文包,瞧着它,他正在发愁;只要一瞧这公文包,县长大人准要愁眉不展;他在为即将在仙女谷乡民面前发表的演讲词打腹稿:
——“先生们,乡亲们……”
但是,他把心爱礼服上的棕色丝线捻来搓去也无济于事,仍然憋不出下文,老是重复那个开头:
——“先生们,乡亲们……”
下文老憋不出来……马车里又这么闷热!……往车外望去,去仙女谷的大道在烈日暴晒下尘土飞扬……空气像着了火一样灼热,道旁的那些小榆树蒙着白色的尘土,成千上百只知了在树丛中你唱我和……突然,县长大人全身欢喜得打战,在那边,山坡下,有一片绿色的小橡树林在向他招呼。
小橡树林似乎在向他发出邀请:
——“到我这里来吧,县长大人;到我这里来写您的演讲稿,在树荫下又凉快又文思敏捷……”
县长先生大受诱惑;他跳下车来,叫他的随从们候着他,他要到绿色小橡树林里去写演讲稿。
在小小的橡树林里,鸟儿成群,紫罗兰到处盛开,浅草下泉水潺潺……当这些生灵一见到县太爷身着大礼服,手提大皮包,鸟儿就吓得不敢唱歌了,泉水也不敢再发出声响,紫罗兰则躲到草丛里去……这片僻静的小天地哪见过堂堂县太爷?它们纷纷低声打听,这位派头十足、穿着绣花礼服来到这里的大人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
叶丛之下,低声悄语,纷纷询问,此人身穿礼服,究竟乃何等人物……这当儿,县长先生初尝林中的幽静与阴凉,已感到心醉神迷了,他撩起衣裾,把帽子放在草地上,就势坐在一株橡树下的青苔上;接着,他把皮面刻花的大公文包摊在膝上,从中抽出一大张公文用笺。
——“这是个艺术家!”黄莺见此这么说。
——“不是,”灰雀表示异议,“他肯定不是艺术家,既然他穿着绣了银线的裤子,更可能是一个王公贵族。”
——“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王公贵族。”一只年老的夜莺打断上述的胡猜乱蒙,它整整一个春天都在县长公署的花园里歌唱,自有它的发言权,“我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本县的县太爷!”
于是,整个林子都在交头接耳:
——“这是县太爷!这是县太爷!”
——“他的头秃得多厉害!”云雀有所发现地叫了起来,它头上长着漂亮的羽冠。
紫罗兰纷纷在打听:
——“他是个坏蛋吗?”
——“他是个坏蛋吗?”紫罗兰纷纷发问。
那只老夜莺断然予以否定:
——“完全不是!”
听到这个确认,鸟儿又开始歌唱,泉水又奔流起来,紫罗兰又散发芬芳,就像这位不速之客并未来到……对周围这一切动人的热闹情景,县长毫无察觉,他正一门心思在乞灵于专管农事的女神,手里举着铅笔,开始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读,就像在大会典礼上:
——“先生们,乡亲们……”
——“先生们,乡亲们。”县长用在大会典礼上那种声调在朗诵……
一阵大笑把他打断;他转过身来,只见一只啄木鸟站在他的礼帽上,瞧着他在发笑,县长懒得跟它计较,只耸了耸肩膀,他想继续他的演说;但这只啄木鸟还不收场,老远冲着他嚷道:
——“讲这一套有什么用?”
——“怎么!没有用?”县长喝道,他满脸通红;他做了个手势去驱赶那只厚脸皮的畜生,更加起劲地又朗诵起来:
——“先生们,乡亲们……”
——“先生们,乡亲们……”县长朗诵得更起劲。
但正在此时,紫罗兰纷纷把花枝向他伸来,温情脉脉对他说:
——“县长大人,请您闻闻我们的气息香不香?”
这时,泉水也在青苔下为他奏出了美妙的音乐;在他头顶上方的树枝上,一群黄莺为他唱出了最动人的歌;整个小小树林都在发出声响,就为的是把他那篇破演讲词给搅掉。
整个小小树林都在窸窣作响,就为的是把他那篇破演讲词给搅掉……花草的芬芳使人醺醉,林中的音乐令人忘乎所以,县长先生再也无力抗拒花香鸟语的陶醉,他手肘支撑在草地上,脱下他漂亮的礼服,嘴里还结结巴巴嚷了两三遍:
——“先生们,乡亲们……先生们,乡亲们……先生们,乡亲们……”
立即他就把“乡亲们”打发见鬼去了;他请来的农事女神也只得蒙上自己的面纱,悄然而退。
蒙上你的面纱吧,专管农事的女神!……个把钟头以后,县长大人的随从们担心主人的下落,就跑进树林里来,他们眼前的情景把他们吓得后退……县长先生俯卧在草地上,衣冠不整,像个流浪汉,上身脱得精光……嘴里嚼着紫罗兰,正在那里吟哦作诗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