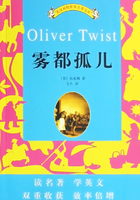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嗯,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有那些重要又机密的文件,然后想起,一直以来你似乎对于他的事情都特别关心,所以我查了一些有关资料。”他不说了……
“嗯,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有那么重要又私密的文件,然后想起,一直以来你似乎对于他的事都特别的关心,所以我查了一些有关资料。”他不说了,我很好奇,他都查到了什么。
“你查到什么了?”我小心的问。
“我看到两份资料和两张保单,保费不低,这么大笔钱一查就能查到,是凌家的,虽然好奇你和凌家的关系,我还是看了另外两份资料,一份药物报告是说用药物改变头发基因,头发会因此富有生命,变得华美,副作用是,它会反吸收人体的营养,表现为衰老症,另一份是他的精神病案,我想你和他是有关系的,我查到你10年前在的城市和工作,所以去那里做了调查,他也在那座城市,这加大了的推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11年前,你做了理发店的收银员,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找上了你,那个人就是凌薇,她要你帮她报仇,她安排你参加了她的葬礼,让你认识了罗迪斯,凌薇知道,罗迪斯看到你的头发一定会接近你,拿你做实验,而你会为你自己报仇,但是,凌薇算错了一点,你的血有抵抗能力,虽然你吃了药,但是反应不大,所以,你没有报仇,只是选择了自保,来到了这里。”
“我的血?”我纳闷,我的血很正常吧。
“半年前,我在暗中清楚了一切,却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没事,所以,我抽了你一点血,拿了那种假发做了个小实验。”陈必发看出了我眼中燃起的怒火,还特意用小手指比了比指尖。
我真不知道我是该狠狠揍他,还是又钻进他怀里哭一场,只是,怔怔的站在那里。
“麦姬,我不是故意要知道你的过去,但我想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我只是想了解你,没有恶意的。”他又把我拥进怀里。
“我……”我想说我并没有怪他的意思,事实上,他让我感动。
“麦姬,答应我,有事我们一起分担,好不好。”他可怜兮兮地说。
“不……”我想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很想找他分担,但是,我害怕晚上要独守空房,可是,他又不让我说话。
“不要说拒绝的话,我是你丈夫,你应该听……”他说,他还说,我恼火了。
我踮起脚,吻住了他那喋喋不休的嘴。
罗迪斯来的时候被记者包围了,记者问的不是衰老症的对抗药,而是问他是不是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我看着电视又看看一旁的他,就见他对我傻傻的笑,我笑着偎进他怀里,心里满上一丝忧愁。
我想罗迪斯会到这里可能是陈必发的动静太大了,把他引过来了,现如今又有记者知道这么私密的事情,他一定更加确定我在这座城市,说不定他还知道陈必发的事,如果他查到陈必发,一定能查到一个在10年前改名字的女人,现在叫凌遗,而以前,叫麦姬,曾经是他的女人。
如果他来找到我,那么死的会是我们一家四口,或许,只有三个人会死,凌罗是他的女儿,不过,凌罗不死也会活的很惨,这种事我不愿看见,但是如果,我主动找到他,那么,死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其实,我早在10年前就要死了的,多活了10年,还是幸福的10年,我心满意足了,陈必发和两个孩子都不会过得太辛苦,因为,凌罗的保险是分红型的,就算陈必发事业也不怕,又有了房子,也不用担心会没有地方住,就算要交遗产税也会因为房子小不用交太多,保险金的冰山一角就能解决。
其实,早在10年前,我就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我做了一桌好菜,写了一张纸条,打了10年钱在渔船上曾经打过的最后一个号码,竟然通了。
“罗迪斯,我们见一面吧,在缘豆咖啡厅。”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出门打车去缘豆了。
“我说麦大小姐,你可真会挑地方啊。”这样尖酸刻薄的话一点也不像是从他那样绅士的嘴里说出来的。
“我知道你那么多秘密,说吧,要怎样才能放过我?”
“哼,原来真的是你?”我突然发现,他怎么还没有陈必发那土包子好看呢?
等等,什么叫“原来”?难道,之前他根本还不能确定是我?那么,我岂不是自投罗网了?是我把他高估了……
“后悔来了吗?”他优雅的喝了口咖啡,好整以暇的看着我。
“还来得及吗?”我反问,我知道,他不过是想看我求他的样子。
“对不起,来不及了。”他恶狠狠的说,“如果不想你一双可爱的儿女有事就跟我来。”他站起身,示意我跟上。
他果然还是动了他们的主意,看来这次就算我不找他,他也会来找我的,拖了那么久的纠缠终于就要了结了吗?
我坐上了他的车,车子越开越偏,开导了以北的死城,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死城,东南西三面都还有人家的,但这里,曾经是厂区,因为一次化工厂爆炸废弃了,一个人也没有,天色又渐渐暗了下来,我害怕,但不能表露出来,我想起陈必发,如果他在就好了,他总让我觉得安心。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接,看了看罗迪斯,见他只是开车,也没阻拦的意思,就掏出了手机。
“是我丈夫。”我说着按下了接听键。
“不准接。”他突然暴怒,伸手打掉了我的手机。
怎么刚刚还好好的,一下就变了?也对,他有双重人格,哼,他这样的男人,以前怎么会迷恋他的呢?
车子在路上停了下来,外面已经全黑了,车灯看得到的范围也瞧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空荡荡无一物的路,路边也不知道有些什么,就听见簌簌的声音,透着几分诡异。
“我问,你答,老实回答。”他阴恻恻地说,车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倒是和周边的景物很搭调。
我点头,没敢多说,眼睛半眯着。
“你在我去研究所之前就拿到手了?”他问。
“不,那天才拿到手。”我老实回答,我可不像一个不小心就惹恼了他,因而让自己早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那之前一个星期。”
“贱人。”他掐住我的脖子,“你速度倒是挺快啊,嗯?”他狰狞扭曲的五官让人胆寒。
但再胆寒也得想办法让他松手,他的手劲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我胸口的那股空气憋在那里,出也出不来,吸又吸不进。
“难道你,不像知道更多吗?”天呐,空气,空气。
“哼。”他一把甩开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咳,咳,凌薇的信。”被他这么一掐,我的声音都不适应的沙哑。他情绪起伏很大,一定在想凌薇信里的内容,我悄悄松开了安全带。
他突然回头瞪着我,我以为他发现了什么,被他吓得往车门上一撞,右边臂膀那叫一个疼啊。
“你带了手套?”他问。
“嗯。”我怔怔的点头。
“那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织布纤维的纹路?”
“我戴的是一次性手套。”
“聪明啊。”他又回转头来瞪着我,“那通电话又是怎么回事?”
“租的船。”我说。
他又瞪我:“看来以前是我小瞧了你。”
我没有回答,没敢回答,也不知道回答什么。
“你眼神不好?”他似是关心地问。
“是有一点。”我依旧半眯着眼。
“看来我们都老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我呵呵地点头。
“不要对我这副嘴脸。”他说着又要伸手掐我。
我一个后仰,整个人都摔出了车去,哪里还管什么痛不痛,还没站稳就向黑暗里跑,如果我推断的没错,我们可以有二十几米的差距。
因为刚刚他扑了个空,还要整理心情,爬起,松安全带,开车门,下车,绕过车头;我穿的又是墨绿色的衣服,黑色裤子,他很难发现我,而且,我的鞋子还是软胶平底鞋,声音减到最低,不像他是皮鞋,这样算来,我在暗,他在明,我占上风。
我跑进一座厂房,厂房很大而且四通八达,出口不止一个,我不怕跑不出去。
我拿着瑞士军刀,躲在离出口最远的角落里,听到他拿什么东西砸在金属管上,嘴里还骂咧咧的叫着“贱人”,他也聪明,知道消停下来,我趁着安静的档口,用刀子在身边金属管上弄出不小的动静,听到他的脚步在往这里来,我拔腿就跑,不回头看身后是什么情况,只要跑出去上了车就好了,我这样觉得。
“贱人,给我站住。”他叫嚣着,就在我已经到出口的时候,我知道,他发现我了,哪里还敢回头,步子反而加大加快了,我觉得我腿软,心跳无力,好像随时要倒下来,又好像,我的动作已经不被大脑控制,完全的处于本能了。
他还在后面叫喊着“贱人”,正好可以让我知道他的位置。
我在车前停下,把手中的瑞士军刀掷了出去,到底有没有扔准都没确定就上车发动,那把刀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
车子发动了,没在意车门,没来得及系安全带,也没想倒车,就顺着来时的路往前开,我知道像这种厂区都是格子式的路。
开到有路灯的地方我才敢停下来,深深的吸了口气,感觉自己还活着,关上车门,系上安全带,这才用正常车速继续往家的方向开。
快到城市的时候,我发现后面竟然有车子一直跟着我,而且,越来越接近我,难道他追上来了?不会吧,他哪里来的车?
虽然这么想着,但是我还是踩了油门,飞驰出去,但是这里车少,路又宽有平坦,阻碍物又少,虽然不考验我的车技,但是,他必定会很快追上来,怎么办?
我开始扔车上的东西,小到车上的纸巾盒子,大到副驾驶座上的座椅套,我恨不得连方向盘都扔出去,该死的,多开几年车就是不一样啊,竟然都被他避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