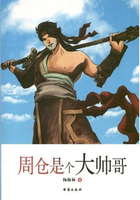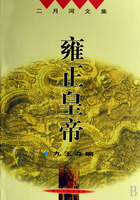不知道为什么在昏睡之中我想到了以前大学中的一个女生,曾经算是喜欢过的一个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不会主动的人,哪怕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一点我与叶小愁妈妈所说的那个总抢别人东西的孩子是大相径庭。在我的世界似乎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属于我的,哪怕它就在我手边,我还是坚持认为它也许并不属于,或许只有被人强迫塞到手中才会接受。但又因为是别人强迫给的所以会经常有这东西并不属于我有一天终究会离开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叶小愁刚刚和我在一起时也会有,我开始也一直以为叶小愁是老天强迫让我接受的女朋友,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真正意识到叶小愁的确是我最想要的人,我也是第一次想保护叶小愁,想抓住叶小愁的手不让她离开我。我突然明白以前自己不会主动,只是还没有等到值得自己主动的人。曾经的我在梦中都不敢去牵自己暗恋人的手,而今天的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欲望想去占有她,只属于我的叶小愁。
所以当她钻进我的被子时,我一下子就抱住了她。
她的身体混着外面空气的冰冷钻到我的怀里,我已经脱掉毛衣她身上的冷穿过我的衬衣直达我的皮肤,让我猛地打了一个冷战,不由得将她抱得更紧。我的手在她身上摸索,她身上的旗袍光滑得留不住手,我的手指顺势向下滑去,直到旗袍的下摆处。与旗袍外的冰冷不同,旗袍下的身体如同火炭般炙热,让我的手无法在一处停留。我的手不停地游走在她的腿上,我第一次发现叶小愁要远比我想象的丰满,她的腿上也比看上去要有肉得多。想到这我用手捏了捏她大腿,这让她像鱼一样在我怀中扭动,我们的身体贴得越来越紧。随着我们身体的挤压我愈发觉得叶小愁的身体与我看到的不同,也与我以往接触过的身体不同,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她却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她的手指在我的嘴唇和牙齿间滑动,我闻到她手腕传来的淡淡香味。她用手掌按着我的肩膀将身体支起,空气拥进被子和我们的身体之间,如同在我们之间又挤进了一个人。当那件旗袍滑落在我脚边,一个温热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时,我突然听见了另一个人的叹息。
那是极其细微的声音,甚至说并不存在的音乐。但我却确定我听到了它,如果我怀抱着一个美丽的胴体一样真实。我有种感觉在这黑暗中有人在注视着我们,就在我的左面,右面,上面,不可能是在床底。她一定在某处看着我们。我知道是她,当然同样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叶小愁的妈妈突然抱住我一样。有害怕但也同样让人兴奋,这是和叶小愁在一起时没有的感觉。和叶小愁在一起时心跳和呼吸永远很平稳,只有叶小愁的妈妈才会让我有无法抑制的冲动,叶小愁的妈妈也在这个房间。
我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可是伏在我身上的她却一直没有停止动作,她解开我的衬衣扣子,鼻尖在我的胸膛上摩擦。我听见了一声更强烈的叹息,我停止了动作捧住了她的脸问她小愁你有没有听到?她依然不回答只是咬着我的手指吃吃地笑,她咬得很用力却让我感觉很舒服。只是我发现在我手中的脸也变得和叶小愁不同,叶小愁虽瘦但脸却是有些婴儿肥,显得头大大的。而在我手中的脸虽然同样富有弹性却略显瘦弱,这样的脸型马上便让我想到了一个人,现在坐在我身上的是叶小愁的妈妈。想到这我的手下意识推出却不想正握住她胸前的温柔部分,随着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更多的是让我开始感觉恐慌。她的胸又大又软一只手根本无法握住,这不可能是叶小愁的身体。如果现在我身上的是叶小愁的妈妈,那叶小愁又在哪里,难道在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是叶小愁?我轻轻叫着叶小愁的名字,没有人回应我,只有她在我身上起俯。我想推开她可是手却顺着她的胸向下滑,当我的手触及她的小腹时,她开始在我的耳边喘息,她的小腹光滑无比,我的手停在那里不知该做如何动作。如果是叶小愁妈妈的身体,那她的腹部必然有着缝合的伤口,可是她没有。我本以为这个长着大胸部的女人必定是叶小愁的妈妈,却不想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还不等我却想身上的女人到底是谁时,她抓起了我的手慢慢往下,手指触及那里的瞬间,我放弃了一切思考,身体只随着欲望慢慢膨胀,直至爆发。
清晨我是被门外的脚步声和说笑声惊醒的,醒来时才发现休息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护士们总是坐第一班通勤车来到医院开始忙碌的一天,而我的一天也要在这慌乱中开始。我四下张望花了几秒时间才确定无论是房间还是床上都只有我一个人,被子将我紧紧地裹起丝毫看不出昨晚有人陪我共枕的痕迹,只是揭开被子发现自己还是赤裸着身体这才让我意识到昨晚并不是梦境,随之而来的暧昧味道更是让我尴尬,我瞬间把内裤扔到自己的衣柜中又连忙穿好衣服,最后小心地查看床上是否还留下了什么痕迹。结果就在床单正中的位置有着一块硬币大的血迹。
那血迹已经干透,呈暗红色。虽然以我的经验并不能确定这个血迹出现的时间,但凭记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血迹是否是在昨天以前出现的了,为此我不得不将床单扯下来揉成一团。开始把它堆在墙角,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妥当就抱在怀里走出休息室准备把它直接扔到送换洗衣服的车上。结果负责送洗衣物的护士正在车边整理衣服,看到我拿着床单走过来十分诧异,因为这些事情平时医生是从不动手的。我随便解释了几句就把床单扔在车里,结果走到办公室时转身发现那年老的护士正把床单拿出来仔细地翻看。
今天又有一例手术,开早会时我才发现竟然是我负责麻醉的。主任昨天把它安排给我,而我昨天竟然忘记了术前检查。这已经算是我的失职,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自己还是一个麻醉师。想想自己竟然有两个月时间都没有怎么工作了,我甚至都不记得在和叶小愁相处的时间里我做过什么手术。主任说话的时候我在拼命思考这几个月都做了什么,可是除了和叶小愁还有她妈妈以外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主任拿着病人的病志问我病人情况怎么样时我胡乱地说了一句没问题,主任抬起头望了我一眼。我想主任肯定已经看穿我的谎话,还好他没有再追问。等到早会结束,我连忙套上白大衣往手术室外跑,主任拦住了我他小声告诉我他昨天帮我看过病人了。我这才察觉主任对我的关心远超出我想象,但我还是坚持要自己去看一眼病人,主任对我的这个决定很满意,点头微笑看着我离开。
同样又是一个子宫切全切除手术,同样是一个中年妇女。竟然也是同样和叶小愁妈妈开始住一个病房。我趿拉着鞋一路小跑,推开病房门的瞬间竟然穿过了哆啦A梦的时空门:叶小愁的妈妈坐在对面的病床上,而叶小愁站在窗前不屑地看着我。等我站稳时看清了窗前站的不过是一个中年男人,而旁边的床上却真的坐着叶小愁的妈妈……
我看着叶小愁的妈妈愣了好一会,她的出现太出乎我的意料,惊异过后便是抑制不住的怒气,我冲着叶小愁的妈妈大喊:你到底要干吗?叶小愁的妈妈一如既往只是微笑,倒是病房里的其它人被我吓了一跳,躺在病床上的另一个女人竟然被我吓哭了,我看床牌才知道她才是我的病人。
马上就要手术,那女人马上就要做术前准备已经紧张得要命,结果被我一吼竟然吓得哭着说不要做手术了。她老公在旁边连连劝她,我也蹲下来说好话,结果那女人不依不饶,另外听说是我麻醉就连她老公也有了疑问,因为昨天是主任查的房,今天又一下子换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我也是开口难辩。倒是叶小愁的妈妈走到患者的床前,坐下来摸着对方的额头帮着她擦去泪水,然后轻声告诉她自己也是由我做的手术,还说我技术好又细心,最后她还撩起自己的衣服,让对方看自己的伤口,说自己伤口恢复得特别好马上就要出院了。我站的角度没办法看到她的伤口的全部,但我看到的部分伤口已呈现出粉红色,是伤口痊愈的颜色。
护士走进病房为患者做术前准备,我连忙退出了病房。走了几步转过头才发现叶小愁的妈妈一直跟在我身后。我停下望着她,她也停住了脚步,站在距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她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刚想再问她,患者已经躺在床上被护士从病房中推出。我连忙不顾叶小愁的妈妈跑回了手术室。
手术室里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我换上无菌服走进手术室时主任都已经帮我准备好了麻醉包,患者被抬到手术床上摆好了体位,我把她的病服撩起来手指刚刚触及患者的腰部,患者便如触电般的抽搐了一下,凉呀。这女人的一声叫喊让我十分尴尬,还好周围的护士和大夫都很不以为然,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最讨厌小题大做的病人,在一旁收拾东西的护士长没好气地说:咱们医院就这条件,暖气空调全开着呢,再冷就没办法了。患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屋子冷,是这大夫手冷。患者说完手术室里大家都笑了起来,护士长也笑了:这个呀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了,这你得问问麻醉主任怎么办。主任听了双手一摊没说话,我自己把两只手握了握丝毫感觉不出冰凉相反因为紧张还有了一些潮湿。我再次小心地把手放在患难者的腰上按了几下,我明显能感觉患者身体的僵硬,结果体位始终摆不好,患者不时还哼哼几声感觉不满。主任走到我身边手按在患者身上然后大声说:来别紧张,我来给你做麻醉,你顺着我的手就好不用紧张。结果患者不再有任何反应很容易就把体位摆好。主任接着消毒盖无菌单都一切照常,就在最后要做麻醉时他偷偷对我使了使眼色,我又戴上手套按部就班地做起麻醉,而主任却站在一边如同唱双簧一般讲解我的每个动作,这让患者觉得是主任在为她做麻醉术一样。硬膜外麻醉针顺着患者的第三、四腰椎间刺入,然后经过外膜时会有明显的落空感,最后插管包好,硬膜外麻醉便完成了。当护士扶患者仰面躺在床上时,患者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还是主任的手法好。大家谁也没有说话,主任笑呵呵地背着手离开,我开始为患者量血压观察麻醉效果。不知为什么只要我的手接触到患者,她都好像有抵触一样不是躲开便是身体僵直,这又让我想起叶小愁的妈妈,让我不由对这个患者没有好感。她的血压、心跳一切正常,麻醉药起效也很快,我挥挥手让医生赶快开始手术,坐在那里便不再理那个患者。
手术进行很顺利,长着肌瘤的子宫很快被医生切除扔在盘子里。到这时手术已经接近尾声,气氛又变得轻松起来,在医生进行关腹缝合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有笑有笑,而我却发现躺在床上的女患者在不声不响地流着眼泪。我拿过一块纱布擦去了她已经流到脸颇的泪水问她怎么了。结果患者小声地问我是不是切除了子宫就不再是女人了。这个女人大概刚刚四十岁,或者更年轻些,只是从发型和装束来看不像太有文化的人。我告诉她只切除子宫是不会影响女性功能的,女性功能是由卵巢来控制的。显然这些她并没有听懂,但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不再哭泣。手术结束我和护士一起把她从手术床上抬到单架车上,我抬着她的肩,她的双手紧紧抓着胳膊,在躺下的时候她抓住了我的衣领嘴贴着我的耳朵说:对不起,我好像误会你了,因为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这个人不好,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才会害怕你。
将病人送回病房后我便马上跑到普外病房,我怒不可遏地推开叶小愁妈妈的病房,进了屋才发现叶小愁的妈妈正在收拾东西,我的到来根本没有打扰到她,她依然慢条斯理地将自己手中的一件上衣仔细地折折叠压平。我冲她大喊:你到底想干吗?她转过头冲我笑笑,医生说我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我马上就要回家了。我走过去一把扯过她的衣服扔在了一边指着她的鼻子说: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和叶小愁在一起,请你别在打扰我的生活,也请你放过叶小愁,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奴隶和小狗。我不知道以前怎么样,那是过去的事情,但如果你现在再伤害她,我一定会报警的。叶小愁的妈妈坐在床边重新拾起那件衣服放在手里抚平衣服上的褶皱。本来都以为自己再也出不了院了,没想到医生今天告诉我伤口已经全长好了,不再裂开,不再流脓,他说我今天就可以回家了,病好了就不再让我在这住了,呵,本来不是说可以把这里当家的呢吗?轻轻的几句话却一下子让我如同进入冰库里一般满身冰冷,因为叶小愁妈妈的最后一句话是昨晚在休息室的,我抱着叶小愁时说的,我告诉叶小愁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只要有我在她身边,这个医院就是她的家。我冲过去抓住她的衣服,你到底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小愁的妈妈看着我不说话,我忍不住把她按倒在床上撩起她的毛衣,她的伤口已经长成细细的一条红线,加上周围对称的针眼就像是一只爬在肚皮的蜈蚣模在她的肚皮上,我伸手摸去除了微微的隆起,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伤口的存在。叶小愁的妈妈轻轻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