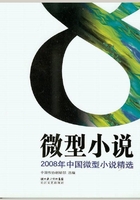凛冽的寒风是锋利的刀子,割着少年黑子的肌肤和心灵。曲柳村的寒冷和饥饿一样可怕。寒冷同样可以使人陷入深渊。
曲柳村最寒冷的冬天,黑子目睹了一头老牛的死亡。
他还目睹了一个老实巴交的老人的死亡。
老牛的泪水让黑子感动。
老人的泪水同样让黑子感动。
入冬之后,生产队的那头老耕牛就明显体力不支了。一般在初冬时节,稻田都要翻犁一遍。那是个有霜的清晨,老人王喜贵早早地起了床,抱了一大捆干稻草到牛栏里去,他是负责饲养这头老耕牛的饲养员,他不能让老牛饿着,虽说昨晚喂过了,可现在他还是要拿着草料来给它吃。老牛慢慢地嚼着干草。老人心里挺担心,牛一老就怕冷,它像人一样,天一冷倒下去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今天就特别冷。
瓦楞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粉白的霜。
老人的牙齿直打哆嗦,上上下下碰得丁当响。他想让牛吃饱一点,因为过一会儿就有人来把牛牵到田里去,犁田手赶着它犁地,那是苦活,要花大力气。
他向生产队长建议过,今年比任何一年都冷,他王喜贵活了六十多年,没碰到过这么冷的冬天,最好不要让这头老牛犁地了,让它好好休养休养,明年春天天暖了再让它下地劳作。
生产队长说:“喜贵叔,生产队就那么几头耕牛,少一头耕牛都不行,地多牛少,地不赶紧翻,冬雨一下就翻不成了,明年的收成也会受影响。”
老人没再说什么。
老牛在嚼着干草,老人在想着心事。
生产队长出早工的哨声响起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了田野。
犁田手李文治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
他边走边说:“霜这么大,也不怕把人冻死,出什么鸟工!犁田这活迟一天早一天也没什么要紧的!”
老人不喜欢李文治,因为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是用手中的竹鞭抽打他的老牛。这不,李文治肩上扛着犁,手中拿着根青青的竹鞭。那根将要打在老牛身上的竹鞭让老人心中冒火。老人一向老实巴交,火也在心里,气也在心里,若不是急了,他是不会轻易朝人发火的。王喜贵是曲柳村最老实的人,他一生很少和人红脸吵架,就是别人欺负他,他也是一声不吭地忍了。这样也没有人会去欺负他,他就像乡野里的野草那样,在乡村的风中默默地从青绿到枯黄。
老人眼睁睁地看着老牛被李文治牵走了。
牛栏空了,老人赶紧把牛栏里被牛尿牛屎浸湿的那部分稻草清理掉,再铺上了干稻草,他伺候这头牛十多年了,这头牛应该是有福的,没有谁像他这样让牛过着舒适的生活。牛栏要是不保持干燥,牛很容易在寒冷的天气中瘫倒。
铺完干稻草,老人的鼻涕流了下来。老人六十多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村里的小孩子都叫他“白须公公”,空闲的时候老人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他年轻时个子也不可能太高太壮,现在老了就更显不出他的个儿,他是个精瘦的老人。
“嗬——”老人呼出了几口白色的热气,“今年怎么会这么冷!”
想到冷,他又不放心老牛了。
他一步一步朝田野走去。
他来到了田边,看李文治一手扶着犁,一手拿着鞭子,赶着牛犁地。老牛喘着粗气,沉重地一步步往前走,犁过处,一块块黝黑的泥土一片片翻开来。李文治嘟嘟囔囔,总有发不完的牢骚,总是嫌老牛走得太慢,走一会儿,他就大声地吆喝一声,抽老牛一鞭子。牛毕竟是老了,任李文治怎么吆喝,怎么使劲抽,它也不可能像从前那么有力气了。
李文治一鞭子一鞭子抽着老牛,那鞭子就像抽在老人的身上。他在地头对李文治说:“文治老弟,你高抬贵手,少抽它几下,它已经老了。”
李文治说:“您放心,抽不死它的。”
他还是继续吆喝着,抽打着老牛。
老人说:“你也会老的。”
李文治没好气地说:“老就老好了,死了拉倒,活着也受鸟罪!”
老人茫然地看着不给他留一点情面的李文治,不知如何是好。
太阳出来了。
田野上冒着气,那是寒霜见到阳光之后融化时冒出的白气。
太阳照在老牛身上,老牛是否感到了温暖,老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感觉不到太阳的热量,天地之间是一个巨大的冰窖。早晨的冽风无遮无拦,从这边扫过来又从那边扫过去,像无数把利刃在空气中狂舞。
老牛渐渐地吃力起来。
它走着走着就喘着粗气不走了,它的四脚打着抖。
李文治气坏了,一阵猛烈的鞭子抽在老牛身上。老牛仰起疲惫的头,长长地哞了一声,嘴巴里鼻孔里喷出长长的白气。
李文治骂道:“死牛,快走,偷什么懒!”
他又一阵猛烈地抽打已经皮包骨头,只剩一副大骨架的老牛。
老人气得全身发抖。
他又听到李文治在呵斥老牛:“死牛,再不走就杀了你吃你的肉!”
这话在老人听来是那么恶毒。
他口里说着:“造孽哟,造孽哟!”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李文治扑过去。
他不顾一切地从李文治手中夺过竹鞭,扔在一旁,他红着眼对李文治说:“你怎么那么狠呢,牛老了,不能动了,你就不能让它休息一会儿吗。人都会老,何况是牛!”
李文治见老人真的生气了,把犁一扔,赌气地走了。
李文治找到了在地头抽烟的生产队长:“队长,这可不能怪我哇,不是我不愿意干,而是王喜贵不让我干!”
生产队长吐了一口烟,问:“怎么回事?”
李文治指了指老人和牛,“你自己看看吧。”
生产队长朝那边望过去,他看到老人给老牛卸下了身上的枷套,然后牵着牛往村里走去。
生产队长没有作声。
他递给李文治一根“经济”烟,说:“抽一根烟吧!”
李文治接过烟,和生产队长对了个火,他吐了口烟雾说:“这可不怪我哇,你可不能扣我的工分。”
生产队长说:“牛也许真的老了。”
李文治看着在阳光中远去的老人和牛,若有所思。
生产队长说:“我看要添一头耕牛了。”
绵绵的阴冷的冬雨让老人心焦。
老人给老牛换了个地方。他把自家放杂物的空房子腾了出来,把老牛牵进了杂物房。在此之前,他把杂物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天花板上看不到一点蜘蛛网。他用油布把窗户严严实实地蒙上,怕冽风会吹进来让老牛挨冻。他在杂物房的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因为牛栏一下雨,水就会流进去打湿了地,老牛说不定一躺下去,第二天早上就站不起来了。
牛老了。
牛在这样舒适的房间里感受到了老人的温暖。
老人坐在躺在干草上的老牛面前,抚摸着老牛的头。牛眼浑浊。老人想起牛年轻时的样子。
那时候的牛是头好牛哇。
它高大壮实,力气很大。村里的黄牛没有一头可以和这头牛匹敌。它要是和别的牛斗起来,胜者肯定是它。那时候它犁地跑得多欢呀,不要说一个铧犁,就是两个铧犁合在一起,它拉起来也风风火火,把犁田手累得吭哧吭哧地跟不上趟,一直叫它慢些走。
牛年轻时神采飞扬。
那神气劲让老人一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幸福感,因为这头牛是他饲养大的。从一头病歪歪的小牛养成一头健壮威风的牛,他花了多少心血哪!
老人的眼中跳跃着火苗。
那时,他还年轻哪,如今,他和牛都老了哇,不堪一击了。
他盼望着天晴,天要晴了,他就会在正午的时候把牛牵到山坡上去放牧,它可以吃一些没冻死的青草,还可以在野地里晒晒太阳,他自己的心情或许也可以得到放牧。
多少年来,他和牛的命运早已经连在了一起。
天终于放晴。
天一晴,太阳出来,就暖和了不少。但要在没有风的日子,天气才会真正暖和,有风吹来的日子还是很冷的。太阳就像是永远煮不开的温吞水,要死不活的,但总比下雨天要好。
有风的日子,老人不会牵牛出去。
碰到没风的日子,老人就把牛牵出去了。在那被阳光晒得微暖的山坡上,牛悠闲地吃着草儿。
老人坐在草地上,目光向很远的山峦眺望。莽莽苍苍的大山让他觉得沉闷,眼皮老抬不起来,进入这个冬天以来,他老是流鼻涕,咳嗽,胸口像堵了块巨石。
他的眼也花了,有眩晕的感觉。
老牛吃饱了,优哉游哉地走到老人面前,躺了下来,头依偎在老人的身上。老人抚摸着牛的头,牛的双眼一眨一眨的,好像在享受着老人的爱抚和温情。
老人会想起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
那是牛还没有成年时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