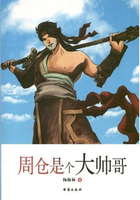李绪源被州府下狱之前,麻烦早已开始。因家大业大,许多地方事务知州大人还要仰仗,故而衙门已经给足李家面子。惜乎此事来头太大,终究捂不住。
根据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置买房产。而大别山里的信阳州,显然并非对外开放城市。教士固然可以建设教堂,但只能作为公共财产,不能当作私人住宅。一句话,房产证上只能署单位名称,不能落个人姓名。不仅如此,李立生他们还算好的,有些后来者是闷声不响地干大事,连契税都不上。
湖广总督、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随即上奏朝廷,要求“以失领土罪有司,转饬鄂豫督抚交涉收回所买土地”。 清朝定例,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省不设总督,巡抚为最高长官。当时河南巡抚是张爱玲的叔父张人骏。他认为信阳两任知州曹毓龄和徐佐尧“于教士购地时,并不详查,遽以税印,又未据实禀明,实属异常疏忽”,决定“奏请一并暂行革职,仍令随同妥慎办理,以观后效”。
偷税漏税的首先倒霉。没盖过官府大印,是为非法,买卖立即撤销。可问题在于,多数交易都没有程序问题。除了双方的协议,州府还发布过官契。官契一式三份,交易双方各执一份,另外一份在府衙照壁的虎头木牌上公告之后,留存官府。在那上面,足足要盖四处官印:地亩数量、四邻疆界、税赋数目,以及官府落款。印信鲜红醒目,岂能随意抹去:有些零星小户卖地的银子已经花光,无钱可退;教士洋商的别墅已经建成,也无地可退。
责任一级级地追查,最终税课司大使周家训的屁股,必须要挨顿板子。
那时的官员多是读书出身,十年寒窗不问世事。精通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但未必掌握法律实务,否则六房师爷也不至于增蘖无度。这次土地买卖真正的关键处其实不在知州,而在于税课司。他们呈报上去,知州怎会留难?如今知州都要暂行革职,周家训岂能幸免。
可拿问周家训,并不解决问题。国人注重实际利益,交易撤销,另行赔偿即可,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两个字:银子;洋人可不行,人家在意虚拟权利,可以无理由拒绝:人权。更何况信阳州府也根本没有另行补偿的态度和能力。
只好先拿小户人家试刀。未缴税的,地亩少的,先进班房。李家势力广大,官府留了面子,没有立即缉拿,但他们毕竟是始作俑者,宽限有期,旨意无情。
此为1905年秋天事。那一年里,孙中山成立同盟会,袁世凯奏请立宪;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革命派担心立宪成功,刺杀阻挠;日本在东北击败沙俄;谭鑫培在北京拍出电影《定军山》;科举停,学校兴。而就时下的廉价观念而言,也是纳尔逊的大庆之年,因其祖国挪威正式独立。然而鸡公山上的李立生,很难感受到这种喜庆。他必须应付那种有理没处说的窘境。
那些日子里,李绪源再也无心竹戏,不停地召集相关房头,商量如何脱身。李玉亭本来已有主意,但刚一开口便遭遇打压,恰如童年故事。李绪源道:“你少打岔!当初你别瞎掺和,也就不会有今天!老祖宗的话没错,你就是个败家子!叔叔大爷都在跟前,轮得到你说话吗?”
李玉亭是代替父亲前来的。他父亲李绪宾迷胡琴爱票戏,两耳不闻窗外事,又抓了次子的公差。在场的都是长辈儿,尽管李玉亭代表着一房,却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从小到大,他一直活在这样的白眼之中,仿佛背上有先天的霉运。而他突然放弃科场,似乎也是个证明。
大伯的无端呵斥,反倒让李玉亭定了心神。从那以后,他不再过问此事,整日里呼朋引类,悠游山林,诗酒唱和。豫南四子均以文名,但个人情形不一,性格迥异。小长辈儿庄重严谨,绰号庄子;刘景向风雅博学,人称才子;胡泰运不苟言笑,所谓呆子;李玉亭机变通达,名曰鬼子。他不仅脑子转得快,舌头也机灵,鬼气十足。鬼到什么程度呢?人们都说,只要他愿意开口,能将屋檐上的麻雀哄入掌心。可巧,他在自家是老二,整个李家大排行是老八,有人叫他八哥。八哥的嘴儿,能不灵巧吗?
大伯入监半月之后,鬼子李玉亭突然找到洋鬼子李立生,要求撤销交易。也不是真正撤销,土地名义上李家收回,但李立生继续使用别墅,无限期使用,以租赁的形式。当然,李家不退还当初的银子,李立生也不必另付租金。
李立生的本能反应是拒绝。正式合同都能反悔,何况君子协定?然而李玉亭巧舌如簧:“李先生,你来中国是传福音的,见死不救,恐怕与你的本意不符吧?土地就在山上,我挪不动,你搬不走,名义归谁,有何区分?别墅你只管住下去,爱住多久就多久。对你无害,与我有益;君子成人之美,此乃善事,你难道忍心拒绝?”
“你们中国人,太不讲信誉。”
“你不明白,不是我们不讲信誉,不过是朝廷要照顾面子。我们当然不想撕毁协议。我向你保证,你如果玉成此事,我一定为你传教提供方便。”
“此话当真?”
“咱们可以另行立约。白纸黑字,永不更改。”
攻下李立生,转头再带着几样酒菜去进攻大伯。
浉河北岸的信阳古城,历史至少也有两千年。城池还是大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旧物,城方九里三十步,高三丈、厚一丈。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城墙再度加固。外面包砖,内芯夯土。本来只有四道门,因南门和西门距离较远,又增设了小南门。这只是外城。正规说法,应该叫郭。从城门进去,里面还有内城;不大,主要是道州衙门、兵营官仓、班房监狱,另外就是官员宅第,一口水井和一座钟楼。
内城门口有兵丁警戒,但无需验照,随意通行。李玉亭目不斜视地进了内城,便直奔州衙。州衙门前照壁高大,贴着布告榜示。大门叫仪门,取成仪临民之意;门口悬着虎头木牌,上面贴着诉讼批示,类似政府公告。当初他们交易的官契,就曾张贴于此。二门叫宜门,取诸事咸宜之意。进门后左边是三班衙役的办公室,所谓“班房”;右边则是监狱,高墙铁窗;大堂位居中间,审讯刑事大案,举办重大典礼。中置公案,刑杖钟鼓布列两侧,左右两厢便是六房师爷。后有屏风门四扇,旁站衙役,俗称门口,非请莫入。里边已是二堂,用于讯问民事,仍有仪仗钟鼓。再进去便为三堂,在此处理衙门内部事务。三堂之后是内眷住所。仓房在最后,但不互通,须从另外的路过去。
大堂后面设东西花厅,用于接待宾客。知州的心腹,刑名钱谷师爷都住在花厅后侧,连同知州办公的签押房。李玉亭首先找到知州大人,向他抛出锦囊妙计:中国收回土地,洋人租用别墅。你得实惠,我保面子,顺坡下台阶。
知州大人闻听,两眼立时放光。他本能地脱口而出道:“好主意!你来给我当刑名师爷如何?”刑名钱谷师爷俗称老夫子,虽然每月只有八两纹银的进项,但在衙门中地位最尊,见官不拜,每逢年节知州还要馈赠礼品。因他并非知州的下属,而是客人,所谓幕宾。
知州大人焦头烂额太久,突见灵光闪现,不免兴奋。可他话虽真诚,却不能当真。师爷可不是随便聘请的。按照惯例,藩台(布政使)衙门挂牌外放你知某州某县后,你谢委时须给藩台的师爷送门包。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县百两以上,小县五十两。同时要请他介绍一两个师爷同时赴任,这样将来上行公文畅通无阻。否则即便是翰林进士正途出身、直接发送各省候补的知县就任,所谓“老虎班”,文书也难保不受刁难。
当然,李玉亭也志不在此。都是聪明人,不必多说,知州大人立即从谏如流:赎回别墅,原户承租。大李小李分家,鸡公山买地的收益以及余下的林地分给小李,责任也交给小李;李绪源出狱,李玉亭名义上代替伯父坐监行孝。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李绪源没有受罪,单独布置的小号,类似干部病房。但小环境再好,终究还是监狱,采光通风都不见佳。此情此景,李绪源除了同意,还能如何?他使劲盯着贤侄道:“你就这么急切地非要分家?好端端一份大家业,分开有啥好?”李玉亭赔笑道:“这只是应付官面的差事。等风波平息再合起来。一切都听大老爷的意思。”李绪源哼了一声:“合起来!砍断的猪腿,还能接上吗?”
信阳州呈报的解决方案,两个多月后终被朝廷采纳。鸡公山随即被划分为四大区域:避暑官地、教会地、湖北森林地与河南森林地。已建成的别墅区域作为避暑官地,另外划出一片教会公地。除此之外的林地,概由鄂豫两省从民间收回,统一出租。小李家分到的山地,多数都被官家回购。价格虽然不比卖给教士洋商,但也肯定不再是普通山地。对于李玉亭而言,这倒是个意外的实惠。
然而他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
班房两月,李玉亭未曾受罪。可尽管如此,尽管已有鬼子的神机妙算,他心里依旧打鼓,夜深人静时尤甚。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决断终究在于遥远的朝廷和太后。就是那种惶惑不安,让他与一个狱友成为知交。此人自称名叫赵明远,直隶清河人士。刚被收监时,虽然隔着好几个号子,李玉亭也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气场。里边的狱卒,全都对他毕恭毕敬。
两个人的交流源于孤独。每当夜晚像巨鸟那样疲倦地降落,用黑色的翅膀罩住整个班房,李玉亭便感觉被孤独与惶恐彻底浸湿,童年的不快记忆慢慢淹没心房。头顶一星油灯如豆,一切全都影影绰绰,他似乎因此而生出第三只眼,也不知是触觉还是嗅觉,总之格外敏锐。而赵明远总在此时练拳,不时嘿哈有声,牵动镣铐发出沉闷的声响。声音并不夸张,但却格外动人。一旦停下,李玉亭便看见有无边的孤独与落寞,像残春的落花那样如雨而下,填满整个空间。
某天此时,正巧家人送来饭菜。李玉亭心里一动,喊来狱卒,要求到那个号子里去,与拳师共享。李玉亭虽在坐监,但不戴刑具,每天都能多次放风。而那人不同,刑具完整。虽然狱卒们对他恭敬有加,却也不敢擅自取下。
李玉亭递给狱卒一两银子:“不要紧。不管出了啥事,我都担着。”狱卒略一犹豫,随即口称谢赏,将他领了过去。闻到酒菜香,那人毫不客气,顺手抄起几片酱牛肉便丢进口中。他抓得多而且快,一片牛肉掉落到铺草上,他本能地伸手去摸索,试图捡起来。李玉亭微笑着斟好酒递过去:“算了吧,有的是。不够咱们再要。”
赵明远自称是炉房师傅,炼化银子的。同时也会拳脚,善剑术。那年月,拳师并不罕见。李家常年招待医生和拳师,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好吃好喝,临走还有红包。招待医生,是给穷人看病,招待拳师,是要训练壮丁。城北四十里的萧曹店,城西五十里的冯家庄,都是出拳师的地方,很多练家子。李家功夫最好的家丁姓雷,就是上次打猎跟李立生暗比刀法的那个,起初也是跟师傅到李家寨训练壮丁而搭上的线。
拳师不稀罕,但炉房师傅还是头一回碰见。因信阳没有炉房。狱中的李玉亭并不知道,当年朝廷已经成立第一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他随口问道:“炉房是干啥的?”话一出口,不必对方回答,他自己便有了答案。开炉房,无非是化铸银子。不是化整为零,就是归零为整。因为当时的硬通货是银两。铜钱与碎银远途携带不便,有时需要换成整锭银子,甚或金锭;等到应付日常生活,成锭的银子又得破开。不过虽然有此需求,但信阳并无炉房,兑换全部仰仗票号钱局。
赵明远轻轻一笑:“信阳果真是小啊。”
“见笑。本地的确没有炉房。”
“所以你们赚不了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