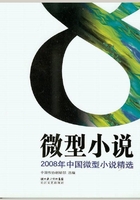“我来并非是找王屋山。”我的语气也变得有些冷硬。因她这番奚落,我的些许怜惜之情也立时化为乌有。我并非浮浪少年,也并非来此寻欢的狎客。
“底死谩生留不住!那你倒是来找谁?”她一把揪下堕马髻上的花朵。
“小生失陪,这便告辞了!”我草草地拱一拱手,就猛然掉头冲外走,刚一拉开房门,就见一个黑影扑倒在地。那人显然是猝不及防,而我也是一时昏头拉错了门。我本是从通向露台的那道门进来,本该是从那道门出去。
驼背的黑影又颤巍巍立起。这是教坊副使李家明。地上有一把摔碎的茶壶。
“你敢在这偷窥!”
“公子着实是误会,小可是要来献茶。”李家明晃动着手里的壶把。
“你这个骗子!楼上有的是茶水!”
“公子光临寒舍,本是李家幸事。”李家明阴恻恻笑道,“小可守在这儿,是恐小妹做出失礼事体来……”
这张笑脸透着狡黠,我顿觉恶心欲吐。我原本对此人也有些好感,身为优伶班首,李家明地位虽远不及朝臣,却也算是宫中近侍。此人谈谐机敏,善为讽谏,每每以滑稽之辞劝喻君上,虽为一己承欢,却也不失纯朴本分。元宗皇帝时,李家明谐戏独出辈流,也曾颇享声望。今上即位后,此人已是老而无宠,再也不得提升。
此刻他是一个偷听者。
“我老李家也算得是体面人家。小妹虽有些使气任性,却是佳人难得,这公子你也看见了。”
李家明正欲拉我一只手,而我已是嫌厌之极。
“我没看见!”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快步逃离这画舫。
木桥通向另一条石径,石径两侧也有茂密的芦苇。小径的尽头有亮光闪动,那是两道穿透暗夜的亮光。
那是一只小猫,一只白色的小猫。双瞳闪闪,毛色雪亮,它轻轻晃动着尾梢,似是在静静地等着我。
当我走过芦苇小径时,小猫就在远处默默望着我。小猫的颈下有一围飘垂的长毛,它静静地蹲踞在路边一片荷叶上,像是一只迷路的幼狮。小猫正对着画舫的灯火,它的双眸闪动着异样的亮光,那是如电如炬的亮光,琥珀色的亮光。
这画舫并无我要找寻的人。我沿着湖边雨花石小路疾走,我要寻找下一处有灯火的楼阁。小猫就在我前头奔跑,仿佛是专来为我引路。暗夜中奔跑的小猫,它在我前方跃动着飞马的身姿。
小路蜿蜒穿过一片桃林。桃枝幽密,这小路忽然没了去向,小猫也不见了踪影。我张皇四顾,就见桃林深处有一道园门,一道宝瓶状的小门。小猫就在那宝瓶门等我。
猫眼反射着异样的亮光,那光源似是来自我身后。我转身回望,就见夜色深处有一团晃动的火苗。
在那芦苇波荡的夜色深处,那座画舫像是在水上游动。在那画舫高处的露台上,一支火把正在奇怪地晃动,那火把先是左旋一圈,接着右旋一圈。我能辨认出那个举火者的身形,那是李家明驼背的身形,像是一个鬼怪在舞蹈。
那火把旋转完毕,又劈空划出一个对勾。我陡然一惊,或许他是在发送某种暗号,这暗号或许是与我有关。
我顿觉毛骨颤栗。那画轴上的诗句或许也是与我有关,可那显然并非新写。
别处并无回应的信号。那暗处定然有窥伺者。
暗处有水鸟啁啾,像是在发出某种信号,而别处并无其同类的回声。
小猫在宝瓶门望着我。
穿过宝瓶门,就见那半坡上有一栋小楼。那青砖小楼藤萝蔓延,檐下挂着绛紫色的纱灯。那或许就是李家妹所说的青楼了。果然,那青楼边的小石桥上有“风月常新”的题刻。我认出那是韩熙载的手迹,我记得有人也将那青楼称作“风月楼”。
那风月桥却是一座断桥。石桥为一道篱墙所隔断,小桥与青楼虽是相望咫尺,外人却难以从这石桥进入那青楼。
此处也不会有我要找的人。小猫从石桥边跑过,一路跑到更远的一棵榉树下。这雨花石路通往两个相反的去向,我站在桥边彷徨无计,不知哪一条路能带我找到那个人。
小猫在榉树下回头望着我,像是要我赶紧跟上。
我正欲跟着小猫前行,忽闻一个男子的吟诗声。“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那吟诵继之以一阵奇怪的声息,像是鸽子交配时的咕咕声。“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我驻足观望,那声息是从风月桥边的小花园传来。那小花园有一个月洞门,洞门内有一个小石桥,石桥通向另一个月洞门。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那吟诵声伴着浪声浪气的呻唤声,那声响伴着桂花香气飘来。“昔为倡家女……”
小花园是一片金桂园,回廊曲折,桂花飘香,园中有一座玲珑假山,山旁又有一棵石榴树,一对男女正在那树下交欢。
“今为荡子妇……”那女子娇声浪叫。
“荡子行不归……”那男子益发用力。
风舞树动,枝柯婀娜招摇,果实沉垂欲坠。他们交颈叠股,似是已入佳境。妇人仰卧在地,两条白生生细腿高高跷起,那小脚纤若钩月。男子俯压在上,起伏间发出粗重的气喘声。
“空床难独守……”妇人接了这末句,假山后忽有咳嗽声传来。那男子愣停片刻,便惊慌起身,匆忙裹起缠曲裙,便悻悻然从那山中隧洞溜走。那妇人也悚然起立,提裙持带向那山后张望。
那妇人纤腰长袖,柔若无骨,一副弱不胜衣之状。她莲步轻移,转身欲走,就有一僧人踅出那月洞门。
“施主缘何如此惶急?”
妇人大惊失色,正欲缚带,那花裙却忽然松脱坠地。慌乱中她弯腰提裙,僧人却已疾手抓过那罗带。那是一个膘肥体壮、五短身材的僧人。
“夫人有所私耶,就不怕我说与舒雅?”
妇人呆望着地上一个石榴,那石榴早已绽裂,就见她举足用力,那弓鞋猛地踹去。那石榴立时被踹烂出水。妇人便不再羞惶,她轻扭腰身,抬手抚一下朝天髻,脸上也有了盈盈笑意。
“只怕你老人家也只是个假和尚。”
僧人略微一怔,便又呷呷笑道:“既是来到这风月楼,咱就不吃素斋吃荤斋了!老衲苦行日久,今日受用这一下,施主方便着些!”
“不是要说与舒雅听么?你倒是去也罢!那不长进的死乌龟,他可是奈何不得我!”
“咄!夫人也是小觑我,出家人不打诳语,我定是要说与大司徒了。”
妇人打个愣怔又道:“我也说与大司徒,单说你非礼。”
僧人又呷呷笑道:“尚未到手你如何说?敦伦一刻,任你说去!”
“和尚好油嘴!无端地拿人开荤,就也不怕犯戒么?”
“在欲行禅,随处自在,佛法也奈何不得!持戒不如布施,施主快快随缘!”
僧人向前扑奔,妇人便掩面而笑,那花裙复又坠地。僧人撩起那缁色袈裟,他挺身向前,忽又抚掌道:“我肏!不想别人唾余污我!”
僧人扳转妇人,使其双臂撑地,马趴在前。
“老贼秃!适间你半道劫食。谁人来得及!”
僧人便又扳转妇人,与其正面相对。妇人咯咯一笑,便两腿分张,弓身后仰。云鬓触地,凤钗半坠,那私处高举相迎,僧人便挺身相就。妇人双手撑地,僧人大力鼓捣。妇人不胜冲撞,便就势沉下身子,僧人便着实地压上去。妇人搂定僧人后背,便柳腰款摆,浪声叫唤起来。一番抽送之后,僧人便揪住她发髻问话。
“怎说我并非真和尚?”
“你是在江上钓鱼么?”
妇人娇喘着应答。僧人僵停片刻,复又大力鼓捣起来。那妇人只顾浪声呻唤,僧人却忽然闷叫一声倒在妇人身上。妇人犹自乱扭,僧人却遽然掐住她脖颈。
妇人伸臂蹬腿,僧人的双手只是兀自用力。那两抹红艳的睡鞋在摇颤。
僧人旋即起身。他轻拍几下僧衣,似是要拂去身上的尘埃。那妇人已是气断力绝,一命归阴。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那僧人望空感叹。
那时我无意中看见了这一幕,我就躲在风月桥边的树丛中。那妇人确实就是王屋山,就是《夜宴图》第二段中的那个扭腰摆臀的舞伎。绿柳蛮腰,娇小而又冶艳,那女子专工软舞,而她最擅长的绿腰舞本也是一款软舞。在那风月桥边,我看见她那高高跷起的细腿,也看见她那紧绷的纤足。那纤足也曾在韩府夜宴中跳一种足尖舞,单腿独立,足尖点地,细腰微颤,身肢便轻盈旋转,那舞姿如鸾飞燕扬,引发一阵阵喝彩声。据说那舞步是由当今国主的宫人尧娘所首创,也有人说那足尖舞或有更早的出处,而我亲眼所见的却是王屋山那细绢缠足的舞步。(而今在我这发白齿摇之年,我所见的女子也都穿起这般瘦小不盈一握的莲瓣鞋,而我居然还依稀记得王屋山那轻若凌波的尖足舞,也记得她在石榴树下偷欢时那纤足紧绷的姿势。)
小猫仍在桥头等待我,它的双眸闪烁着恼怒的电光。当我走回路面时,它忽然冲我弓起身子。它前身伏地,尾部高耸,像是要带我起跑。它奋力地甩动长尾,又似是在严厉地警告我。此时此刻,那蓬松的长尾真像是一条皮鞭,我感到那鞭子正抽在我脸上。我并非来此寻欢的狂且浪子,我在那画舫并无越礼的举止,甚至也无丝毫非分的念想,但我确实也有那番不必要的耽搁,而在这风月桥边,我竟然着实地成了一个窥淫者!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望着石榴树下那两个偷欢者,我却分明是有色情微动的感觉了。——这是怎样的一种羞惭!我甚至不敢正视那小猫的眼睛。
然这羞惭只是片刻的伤感,继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恐惶。这是我平生头一回看见杀人的场景,一个人徒手杀死另一人,而那杀人者就在距我不远处,就与我处在这同一庄园里。那杀手并未看见我,我却并未逃过死者的眼睛。
我收回心神,跟着小猫一路奔跑。我的眼前仍在晃动着那妇人冶荡的形容。就在她与那僧人交欢时,就在她那浪声浪气的呻吟中,她的脖颈架在那僧人的肩头,她的眼睛直望着远处的树丛,而我就躲在那树丛中。淫心如醉,意态妖娆,那一刻她似有万般风情要展露,而我是惟一的观望者。
她的眼睛直望着远处的树丛,而我就躲在那树丛中。我并未逃过死者的眼睛。那一刻她确是在引诱我。这番引诱并非是为肉体之欢。她是将我当作另一种猎物。
城楼有谯鼓声传来,此刻已是初更光景。乌云遮月,夜色更显暗沉。我要找的人不在画舫,不在青楼,我就只能奔向下一个灯火阑珊处。我跟着小猫穿过一座笔架形的小山丘,那山丘上有一片幽暗的桑园。三年前我来韩府游逛时,也曾看见过这片桑园。我断定这去向没错,因我又看到了那片桑园,也望见了那片紫竹林。更鼓声应着我的呼吸,每一声都撞击在我心口,祸及燃眉,我在焦灼中加快了步子。
那是我所熟悉的景色,一片清幽茂密的紫竹林。风动树梢,如麦浪翻涌。竹林深处,有灯光隐隐。灯火处便是名为“兰台”的藏书楼,这是韩府中我能说出名称的一座楼阁。三年前的那场夜宴前,我曾来这藏书楼游逛过一番。那时我从另一个方向乘舟而来,舟至楼前,却发现并无码头。码头设在数丈之外的远处。
青石黛瓦,飞檐斗角,观瞻灵动却又不失沉稳,古雅中亦有几分严峻,这座藏书楼面北临水,原是依据文王八卦方位营造。北方属坎位,坎为水,而水能灭火,书楼北向面水,乃是为防火计。这水池其实是一方荷塘,这荷塘连通更远处的湖泊。这也是三年前我来藏书楼的水路。
与别处建筑迥然不同,这藏书楼并未增建院墙,只是周遭多了一圈竹篱。那楼顶已是荒草丛生,荒草之上是更为阴沉的天色。
苍藓满庭,高梧冷落,有灯光从底楼的花窗透出,那橘红色光芒穿过窗前的笋石和修竹,也照亮那门厅的廊柱。
小猫窜上门阶喵喵叫唤几声,一道侧门便静静地开启。一位美妇人出现在那门口。那妇人体态丰腴,肩头拢着暗红的披帛。我立时便认出她就是我要找的人。三年前我曾在那夜宴现场见过她。她就是那位秦蒻兰。她的姿容依然可见曾经的风韵。此刻她就站在那柱廊的光亮处。那“兰台”二字就嵌在她上方的门楣上。古人以“兰台”指称藏书楼,是因兰草可防古书中的蠹鱼,而读书人总爱将兰草夹在书卷中。我忽然想到兰草其实并非兰花,而眼前这位美妇人却是名叫秦蒻兰。此时此刻,她的周身笼着一片竹影。
涵烟眉,盘桓髻。那姿韵中有色淡意远之致,亦有一种娴雅和温婉。此时此刻,她就静静地立在那片竹影里,那竹影仿佛笼着无可告语的心事。
我并未立刻趋前,只在篱墙边的梧桐树下站定。那小猫急切地冲上前去,像是纳头便拜的样子,它轻轻叫唤几声,就在主人腿脚上摩蹭起来,仿佛沉迷于某种仪式。
“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驿亭一夜眠。”
很多年前,北国使者陶谷曾为秦蒻兰写下一曲《春光好》。那故事也是源自韩熙载的这座藏书楼。周主伐唐,江南败兵称臣。周主派兵部侍郎陶谷使唐。陶谷自恃上国之势,辞色道貌凛然,韩熙载素知此人并非端介之士,便欲杀其傲气。陶谷向韩借书带回驿馆抄录,韩熙载便派秦蒻兰假充驿卒女,旦暮洒扫庭院,那陶谷果然魂不守舍。一宵欢娱,陶谷挥笔题赠美人一曲《春光好》。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
此刻她就站在那柱廊下,含笑望着那撒娇的小猫,又轻轻挪动着脚步。小猫终于找准角度,它耸身上冲,又顺着主人的小腿滑下去,主人便再也无法移动,小猫就顺势躺在她脚上,又用脸颊亲热地摩蹭她的脚面,那小猫的神情已是陶然如醉了。
她似未觉察到我的出现,她只顾低头与小猫细声缠绵。那轻声慢语也是极尽温柔,只是隔着这样的距离,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那一日韩熙载奉国主命为陶谷举宴,席间照例有女乐侑觞。陶谷辞色倨慢矜持如前,国主问他久居使馆是否寂寞,陶谷说他借阅韩书幸免孤寂。国主说江南春色你已采得一枝,何必欺瞒?陶谷勃然作色。韩熙载微笑不语,仍举觥劝饮。陶谷又饮一二杯,忽听歌声幽咽,自那屏后飘出:“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驿亭一夜眠。”陶谷立时心惊目颤,那歌娘袅袅婷婷转过屏风,那正是他曾一夜拥眠的秦蒻兰。
那小猫忽然反转身子,张开虎口轻咬住她的脚踝。似是有主人的默许,小猫的虎牙在试探着用力。秦蒻兰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小猫便立时松了口。她轻轻抽出那只脚,又拉紧那暗红色的披肩。小猫兀自仰躺在地,美美地抻一个懒腰,又张嘴打个哈欠,便微闭双目,仿佛沉入一种冥想。
“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汗水涔涔而下,陶谷无地自容。韩熙载引酒满觥,再度劝饮。陶谷仓惶起座谢宴,连夜辞行回国。北使受辱,韩熙载出了一口恶气,也为江南挽回了一点颜面,而秦蒻兰亦可谓是为国献身。韩熙载将这藏书楼留与秦蒻兰,莫非是为弥补对她的亏欠?
我竭力摆脱往事的纠缠,便向前迈出数步。
秦蒻兰缓缓抬头,或许她早已看见我立在这树下。她神色沉静地望着我。
“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你究竟还是找来了。”
我随秦蒻兰进入这藏书楼,进入这透着橘红色亮光的房间。这是藏书楼的客室。这客室也有一块小小的匾额:芝兰之室。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我记不起这是谁的原话。这客室自有一种清致的格局。一入这客室,我就嗅到一缕淡淡的芳香,这芳香来自书橱边的那株兰花。
她说她已从“王家少妇”那里得知我父亲罹祸。她说“王家少妇”就是王屋山。我说王屋山既已嫁与舒雅,那她应被称作“舒家少妇”才是。她说王屋山岂是舒雅所能驾驭,面上虽与舒雅成亲,但王屋山仍是我行我素,仍愿被人称作“王家少妇”。《王家少妇》本也是王屋山所喜爱的古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