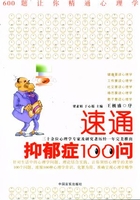我不会!我很想这么大声吼回去,但内心小小的自尊心让我不甘愿就这么任他瞧扁,所以干脆以一记大力发球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还是轻而易举就打了回来。奇怪了,断了一只手的人平衡感不是会差很多,怎么他一点影响都没?
边想我就边追着球去了,哪知道跑得太卖力,左脚绊到了右脚,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了。咚地一声,我和羽毛球同时落地。
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疼,薛城羽就已经跑到我身边,用他那只没受伤的手扶我坐起,嘴上还不忘刻薄几句:“你傻啊?平地上跑都能摔倒!”
才坐好,膝盖上就开始有又麻又辣的疼痛感了,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委屈,鼻子一酸,带着哭腔指控他:“是啊,我就是运动白痴!都说我不打了,你干嘛要跟我组队啊!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去美术教室的,你干嘛要拉我打球!”
我也顾不上疼了,使劲推开他。他一只手就按住了我的腿,拉起其中一个裤管。
“不要!”他这个动作简直触到我神经了,我才不要他这样看我的小腿和伤!
“别动,手拿开!”他凶巴巴地,吓我一跳。
受伤的可是我啊!他眉头怎么皱得比我还厉害,还那么大声!我这伤到底是谁害的啊!可我不敢乱动,只能任他端详。
“破成这样,还流血,去卫生室吧。站得起来吗?”
我用力用手支撑自己站起来,拒绝他搀扶,一瘸一跛地往卫生室去。他跟我在我身后,没有说话。
卫生室的王老师,是个五十来岁的欧巴桑,平时在学校也很闲,总是拿着电话和其他欧巴桑聊八卦。看到我们进去了,连忙对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句“学生来了,先不说了”就挂了电话,笑呵呵跑来看我伤势。
不知道她给我伤口上涂了什么药水,不但疼得我飙泪,伤口上还冒白泡泡。死咬着嘴唇,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几个圈了,坚决不要哭出来,否则臭薛城羽又有笑话我的机会了。
“真不小心啊,不过还好,就一个膝盖流了点血,另一个就是擦破点皮。你有没有别的地方疼啊?”上完药水,王老师帮我在伤口上贴了块超大号的创可贴。
我摇摇头,然后问:“老师,那我能回教室去了吗?”
“小心点。”
说完也不等我们离开,她又伸手去抓电话。薛城羽才不管她怎么说,坚持要我躺在卫生室的病床上无病呻吟。躺着也好,后面一堂是我最讨厌的英语课,而且王老师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们两个是否在旁边,继续聊她的张家长李家短。
薛城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顺手拿了张老师桌上的报纸,边看边说:“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做你的队友真值得同情。”
我听了心里一闷,不禁想起以前的事情。转过身背对着他,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表情。卫生室里只听得到老师在津津有味聊着别人家的事情,隔着一扇布屏风我都能想象她手舞足蹈的样子。薛城羽也没有再说话,我不知道他现在会怎么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偶尔能听到他翻报纸的声音。我内心有小小的挣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和他说心里话,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听。
回想那天在屋顶的气氛,我握了握拳头,小声地说:“我们第一次打篮球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队,各自穿不同颜色的背心来区分。那天我真的有很努力去记自己的队友,但我还是传错了球。我知道没人会来责怪我,最多也只是因为和我一队所以认倒霉。但那之后,像这样的分队活动我都是自动放弃。可能他们心里都在想说不和一个残疾计较,但我不想要这种特殊待遇啊!
要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他人的影响下生活,没有完全的自由啊。我真的好想过平凡的生活,有能谈天的女生朋友,做一个普通的人。”
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最后几句连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理解了多少。是嗤之以鼻,还是会斟酌思量。但我没有勇气回头看他的表情,只好紧紧闭上眼,感觉之前因疼痛憋住的眼泪好像顺着脸颊滑到枕套上。
过了好久,我感觉自己好像睡着了,老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变得朦胧,隐约还觉得有一只手摸了我的头发,很温柔。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最先听到的还是老师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她这电话粥煲得也真是夸张。转过身,看见薛城羽拿了个手机在玩游戏。真不明白他带这个来做什么,我们岛上没有发信台,信号薄弱到可能站到楼顶上都显示不了半格,岛上有手机的都是那些常跑陆上的人,但在岛上都是用座机。有些人家里电话都很少用到,这个地方太小了,串门很方便。
眨着眼睛盯了他好几秒,我突然想起睡着前对他说的话,脸唰一下烫了起来。
他见我醒了就收起手机,不冷不热地说:“回教室了。”说完就站了起来。
我蚊子叫一样地“嗯”了声,爬下床穿鞋。膝盖还是有点疼,但还不至于不能动。依然是我走在前面,他在我身后。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而我忍着疼痛,走得飞快。
已经是最后一堂课的时间了,教室里大家正在奋笔疾书,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纷纷抬头,又好似什么都没看到一样低下头继续写作业。我默默坐回座位拿出课本,心里怪怪的。第一次,他们用那种陌生的眼神看我,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他们平时不会这样的,还是我多心了?
转头看看跟着坐下的薛城羽,完全没有感觉的样子,又像是对这种环境习以为常,把作业本丢给我后又开始玩手机。
放学后,其他同学都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离开教室。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我这个毫无存在感的人吧。收拾好课本,我把薛城羽的作业本连同我自己的一起交给他。这个懒人,我才不要次次都帮他写作业,更何况他又不是不会做。
“不想写,抄至少可以吧?”
他看了我一眼,不打算接下的样子,说:“不要,太麻烦了。”
呵!全世界就他怕麻烦吗?大少爷!
我刚想给他上意义深远的思想教育课,他就站了起来,懒洋洋朝门口走。
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背起书包,我只好拿着两本作业本,跛着腿跟在他身后。
“喂,你体谅下伤员好吗?走那么快!”
“你可以慢慢走啊,又没人催你。”他好整以暇,说得理所当然。不过他还是放慢了脚步,让我终于得以与他并驾齐驱。
“你配合点把作业拿回家抄完,我还用得着追你吗?”我还特地在“抄”字上加重了音调。
“都说不要了,你烦不烦。”他别开头,一脸不想理人的样子。真奇怪,这人怎么变脸比翻书快,一会儿充满关心,一会儿又拒人千里。跟他说话还真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否则我小小的心脏受不了他这多样化的情绪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