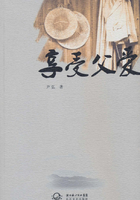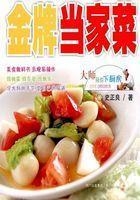张广源摇摇头说:“我不这样认为,崔局长还算是个不错的领导,在机关说话办事比较谨慎,是个有时候真话不敢说,有时候假话也不愿讲的人。他虽然对这个学校的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但也不至于看不出一点问题来,只是不想挑明罢了。咱们俩的意见能够促使他客观地评价学校的会议筹备工作,这就是参谋的作用。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说的话属于人微言轻,但首长一旦听信了你的话,就可以改变他的决心,使你原来的建议变为指示和命令。所以,我们要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不管首长乐意不乐意,宁可说真话挨批评,也不能说假话受表扬。”
“我虽然来机关时间不长,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有些人说了真话有些领导并不待见,有些人不说真话有些领导反而欣赏。”
“是呀,现在有太多的人喜欢听好的话或者说是奉承自己的话。奉承人的话,像是副食商店的‘王致和’,人人都说臭,个个都想吃。特别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听了奉承话心里很舒服,总是不愿意脱掉身上那件‘皇帝的新衣’。奉承,是一种不花钱也能讨好领导的说话艺术,奉承人的人一般都能从被奉承的人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说,所以这种现象总也杜绝不了。”
郑罡听了张广源的话,对眼前这个自己以前也有些成见的老参谋,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真诚地对张广源说:“张参谋,我很佩服你对有些问题的独到见解,您经多识广,机关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对我多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互相学习吧!”张广源说,“既然在机关工作,就要尽快适应机关的环境,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别人都会仰视你,如果你只是一棵小草,有时候就难免会被别人踩在脚下,参谋在机关里就好比是小草。但是小草有小草的作用,小草有小草的尊严。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川剧的变脸似乎已无秘密可言,官场上的很多人都会。我们是在部队机关工作的参谋人员,既要讲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特别注意不能当两种人,一种是唯命是从的人,一种是有命不从的人。”
郑罡颇有感触地说:“我小时候主要是由保姆照顾,她对我有些放纵,造成我生活上不拘小节,说话办事任性。上中学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月回一次家,回家后,母亲为我洗衣服,父亲为我洗脑筋,搞得我心里很烦,家庭的环境养成我叛逆性很强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应当说并不适合在大机关工作。今天听了您的话,我很受教育,可以说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广源笑了笑说:“你太低估我们的教育事业了,也太高看一个人话语的份量了。”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奉承领导的人,讲的是心里话。”郑罡认真地说,“我最讨厌听‘官二代’的说法,尽管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人说高干子弟的仕途通顺,全是绿灯,没有红灯,生活的道路即使曲折,靠老爹的手也能把它抻直了。我到远离父母的地方工作,就是不想在大树底下乘凉,要拥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很难。”
张广源也认真地说:“你能够这样想,并努力按照自己想的去做,我觉得不简单。我原来对高干子弟有偏见,应该说,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有明显的弱点,但也有突出的优点。父母都是为孩子好,当儿女的对父母不能有抵触情绪,也不能有逆反心理。工作上的事咱们以后再说,你已经三十多岁,该成个家了,你的父母对这件事肯定也很着急,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帮不了你多少忙,你要自己抓紧。”
“对于我的婚姻问题,父母肯定着急,不过,他们也知道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尊重我的选择。我现在找女朋友要求条件不高,坚持‘三不’,即不找高学历、不找高身材、不找高干子女,但是,一定要找一个正直善良、通情达理的人。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我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谈了个男朋友,家里人问她小伙子长得什么样,我表妹调皮地说,他个子高高的,身材瘦瘦的,皮肤白白的,帅呆了,酷毙了!我姥姥在一旁连忙说,闺女,咱只要帅的,不要呆的,爱哭鼻子的男人更不能要!”
张广源被郑罡的话逗笑了,他看了看手表说:“咱们俩只顾说话,都快十二点了,抓紧时间睡觉,明天早上你要是七点钟还醒不过来,我就拧你的耳朵。”
晨钟吃过早饭到了办公室,简单地打扫一下卫生,就开始处理文件。
过了一会,电话铃响了,是在外地出差的崔局长要陈文铭听电话。晨钟知道陈文铭前天刚把孩子从城里转到营区附近的学校来,估计是吃过早饭送孩子上学了。他没有对崔局长说陈文铭去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只是讲他出去办点事,一会就回来。
崔局长又问:“他跟随王部长出差的资料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
“他正在认真准备,昨天晚上还加了个班。”晨钟回答。
晨钟刚放下电话,陈文铭就满脸汗水地进了办公室。
陈文铭听晨钟讲了崔局长来电话的事情之后,皱起了眉头。
“小晨,你是个刚到机关来的新同志,有些话我不得不讲,参谋在工作中最忌讳的是‘一问三不知’,但也不可能是‘三年早知道’,对有些事情要多听、多看、多问、多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晨钟看到陈文铭讲话时的表情比较严肃,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陈文铭接着说:“今天是孩子第一天到新学校上学,我去学校送他,昨天就给在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请了假,你没必要在局长那里为我打掩护,我们工作再忙,有些个人的事情也要处理,这一点领导会理解。准备跟王部长出差的材料,昨天下午下班时我就已经送给首长秘书了。另外,昨天晚上我也没有加班,只是回来取走下班时忘在办公室里的自行车钥匙。”
陈文铭的几句话,像一杯冷水,把晨钟脸上原本有几分得意,后来又有几分茫然的表情冲刷得干干净净,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陈参谋,您、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够诚实?”
“不是的!”陈文铭肯定地说,“我知道你是想为我好,但是,有时候你无意间说了一句与实际不相付的话,以后要用很多话去弥补或者解释,甚至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影响相互间的信任。我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有一次,张参谋上班时间去招待所看外地来京的一个战友,我对局长说他到其他局办事去了,局长后来知道真实情况后把我好熊了一顿,张参谋也批评我不能这样为同事打掩护。说话怕穿帮的唯一办法,就是永远不要说谎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实话实说,这是机关参谋必须具备的品质,特别是在领导面前,更应该如此,借助一位名人说的话,即是:‘获得领导信任的技巧就是避免使用任何技巧’。”
晨钟红着脸说:“陈参谋,今天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其实我的父母一直想用高尚的品德为我树起一杆纯洁心灵的标尺,教育我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我原来还比较注意从这些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看到社会上一些口是心非的人比言行一致的人能够获取更多利益时,思想上也有过波动,也有过困惑,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源。”
陈文铭故作轻松地说:“不要把今天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你毕竟还是怕领导对我有不好的印象,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并不是要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其实,老实忠厚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保存至今的宝贵遗产,有些人并不想继承,过去是说假话办不了真事,现在的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是不说假话还真办不了真事。听说话,遍地都是君子,看行动,到处都有小人,社会上见死不救、见错不纠、见难就避、见利忘义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在生活的道路上,正直的人比虚伪的人往往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您讲的话很深刻,在观察和处理问题上,我以后要很好地向您学习请教。”晨钟真诚地说。
“这句话讲得不妥,在咱们小组这个小范围,我们都应当向张参谋学习请教。”陈文铭也真诚地对晨钟说,“他长期在机关工作,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灵活,很多事情处理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他不是钢板,而是铁丝,柔软得可以弯曲,坚硬得无法折断。尽管他脾气不太好,有时候说话太直,但我们依然很敬重他。”
陈文铭看到晨钟在认真地听自己讲话,又看到他面前摆放着的文件,转移了话题问:“今天的文件有急办的吗?”
“没有,没有!”晨钟连忙回答,“只有一份请示件,要等首长有了批示再办,其他的都是阅件。”
“那就好!”陈文铭接着原来的话题往下讲,“张参谋有时候说话不太好听,你和小郑都不要介意,不管是部长、局长,甚至是组长,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有水平、高素质,聪明的领导者懂得,自己的部属都成为英雄,他才能成为统帅,身后一群弱兵,他就不能称为强将。”
晨钟笑笑说:“您的话我非常理解,张参谋有时候是冷面孔、热心肠,他说我是‘大学学历,小学字迹’,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照着他给我的钢笔硬笔字贴练半个小时的字。”
“钢笔字应当练好,因为我们不可能走到哪里都带着打印机,有时候你的文笔虽好,人家一看见满纸鸡爪子印,先减少一半兴趣。在机关里工作,比写字更重要的是文字水平,郑罡刚到局里来的时候,张参谋批评过他几次,也给他找了不少范文让他学习。后来小郑一边学习起草机关文书,一边练习写诗词,诗词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的文字水平这一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提高得比较快。”
“郑参谋写的诗我看过,还有些韵味,我以后练习文字也从这方面入手。”
“那倒不一定!”陈文铭说,“不过,诗词,特别是古诗词,遣词用字非常考究,古人写诗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佳话,像‘三年成一句,一吟双泪流。’‘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语不惊人死不休’等等。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起草机关文书既要主题鲜明,也要文字简练,不能是‘关门闭户掩柴扉,一个孤人独自归。’重复罗嗦,没有重点。你和小郑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生活和学习条件优越,见多识广,思路敏捷,只要努力刻苦,想学习什么本领,肯定比我和张参谋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要快。”
晨钟连忙摆手说:“话不能那样讲,城里的孩子缺少的就是农村孩子吃苦耐劳的这一课,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是风和日丽,你们是雨急雪狂,我们是悠闲漫步,你们是艰难跋涉——”
陈文铭不等晨钟把话讲完就笑着说:“好,看来你以后可以与郑罡一起练习写诗了!”
晨钟比郑罡小不了几岁,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再加上同在一个小组里工作,同在一套房子里住宿,相互之间很快就了解了。郑罡是外向性格,爱说爱笑,办公室里老同志多,他说话不太随便,回到宿舍就云天雾地的与晨钟吹牛聊天。晨钟因为是机关里的新人,公众场合说话办事都还有些拘谨,回到宿舍也喜欢与郑罡谈谈心,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
有一次,晨钟走进郑罡住的大房间,对他说:“你吃过晚饭就一直在这里坐着,该休息一会了,是不是又在练习写诗呀,前几天陈参谋还夸奖你文字水平提高很快,主要是得益于对诗词的研究,你以后写诗不要只是自我欣赏,也不能只有我一个读者,可以给报刊投投稿。”
“我不是没有投过,但投出去的稿子都被退回来了。”
天气有些热,郑罡正在光着脊梁在微机旁上网,手指头没有停止动作,看了晨钟一眼说。
“你投的诗稿都是什么体?”晨钟又问。
“有自由体长短句,也有五律、七律。”
“报刊对五律、七律的稿件可能会退稿,如果你写的是‘一律’的稿子,他们就不再退了,我经常看到报刊的稿约上有‘来稿一律不退’这句话。”晨钟在郑罡的床上坐下来,笑着说。
“你是在取笑我?别人取笑我没有关系,要是连你也取笑我,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干脆跳进洗脸盆把自己淹死算了。”郑罡关掉微机,扯了扯麻木的手指,对晨钟说。
“你千万不能死,要不然,我们以后每年就要过两个端午节了。”
郑罡哈哈大笑,肚子上的脂肪荡起层层涟漪,指着晨钟说:“你在领导和老参谋面前一副正经八摆的样子,在我面前很会耍贫嘴。”
“要是白天晚上都一副正经八摆的样子,还不把人憋死了,白天被压抑的情绪晚上释放出来,生理上才能平衡,你别说我了,自己不也是一样。”
“你讲的有道理!”郑罡抓了件衬衣披在身上,对晨钟说,“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年轻人比较多,晚上还可以一起唱歌下棋打台球,大机关里的干部一下班多数都是各回各的家,就苦了我们这些不快乐的单身汉。”
“当单身汉不能怪别人,您老人家这把年纪早该成家立业了,是自己没抓紧,三十多岁了还屈尊与我一同住在单身宿舍里。”
“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自然条件,谈的女朋友早就论‘打’计算了。你看看我这身材,用有些女孩子的话说‘上身粗,下身短,不是馋,就是懒。’他们以貌取人,与我见一面,就在预选男朋友名单中按了删除键。”郑罡说着,生气地拍了一下面前的微机键盘,“要说我自己没抓紧也对,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战友都进入爱情的坟墓,被判了‘极刑’,只有我是幸存者。不过,我上高中的时候身体还没有发福,与你一样苗条,毕业时就有两个女同学追过我。”
“你们那时候是‘早恋’还是‘早乱’?”
“既不是‘早恋’,也不是‘早乱’,她们俩追我,一个是我看了她一本小说没归还,一个是我借了她的电话卡想赖账。”
“你的话有意思!”晨钟笑着说,“身材只是外部条件,我大姑的儿子各方面的条件与你差不多,他谈女朋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三个月不换就算是‘老夫老妻’了。其实像你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大街上随便走一趟,后边就会跟一大群。”
“苍蝇还是蚊子?”
“是蜜蜂,而且都是没有配偶的雌性。”
郑罡又哈哈地大笑起来,身上的脂肪“花枝乱颤”,他抹了抹眼角笑出的泪水说:“你太不了解现在的女孩子了,她们既想坐宝马,也想骑白马,我上次谈的那个博士,脸蛋长得还可以,五官分布得当,而且一粒雀斑都没有,属于‘美加净’。但身材也不是太好,前胸不鼓后背鼓,腰肥脚大脖子粗,应该说与我还比较班配。她就是因为学历高一些,在我面前由博士变为‘剥士’,说出来的话像刀子,差点剥我一层皮。有些女孩子自信心特别强,总以为自己是公主,你就没想想你老爹是不是皇上。按说一个人生活也挺自在,结婚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咱们楼上原来住着一个退休干部的儿子,去年五一刚结婚,有一段时间两口子总是干架,不但恶语相向,还发生了肢体冲突,这种肢体冲突,在赛场叫拳击,在家里叫打架。我走在楼梯上,有时候还可以看到,男的额头上贴着胶布,女的嘴角上涂着碘酒。有一天,夜很深了,他们还在又吵又骂又摔东西,我实在受不了,就上楼敲门对他们讲:求求你们别闹了好不好,为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多做点贡献。你知道最后怎么着了?两口子被窝还没暖热,今年过罢春节就离了。哎,你看过我去年作的一首诗吗?里边有两句是这样写的:窗外‘沙沙沙——’,那是风和树叶在对话;窗内‘咔咔咔——’,那是夫妻两人在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