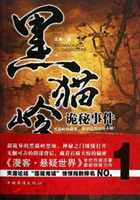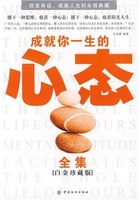别说对不起,别让我伤了心才说不是故意,我却无法怪你
因为先前警察来做笔录,顾映宁让护士将病床的上半部摇到了斜立。所以倚靠在病床上的顾映宁望向轮椅上的盛夏,竟然还是微微居高的。
盛夏看着顾映宁坚毅而紧绷的下颚,微微抿唇一笑,依然有些生疏地将轮椅推到他跟前,歪着头盯向他,问:“肚子饿不饿?”
顾映宁摇头,欲言又止了几番,终于还是开口问道:“许亦晖他……他,他可好?”
他明明想问许亦晖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明明话都到嘴边了,然而转了个弯说出来的却是“他可好”。盛夏怎会不知他的本意,忍不住轻轻笑出了声。
出乎意料的,顾映宁倒也不恼,只不过闭起了双眼仿佛疲倦了一般。
盛夏到底出了声,轻而清晰:“映宁,我们先不聊亦晖的事,你好好把伤养好早日出院,好不好?”
许亦晖始终是横在他和她之间的一道墙,婚礼前他们那场争执是因为许亦晖,婚礼取消也是因为许亦晖。她晓得他们迟早都得面对,但至少不是现在。现在,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言语中不容置喙的顾映宁,他是病人,她也是病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是可以平静沟通的,而她,想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患难时光。
顾映宁睁开眼,苍白的脸色并没有削弱他敏锐冷峻的目光。半晌后,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她帮他订份午饭,盛夏却明白这已是他的默许。
“医院里的饭菜你哪里能吃得惯,”盛夏好笑,“我早就通知江镡,让他给你从滨江饭店带份午餐。”
顾映宁淡淡地“嗯”了一声,面色看不出喜怒。
若是过去,盛夏也许会因为他的反应而黯然,但今时她却很平静,口气也很淡,道:“那我回自己病房了,你好好休息。”
她说着便要转动轮椅,然而还不曾碰到扶柄,手臂却被一张略微冰凉的手掌一把抓住。盛夏一转头,只见顾映宁那只手分明还在打着点滴,就这么一个大幅度的动作让血液都回流了。
她忙急声道:“映宁你快把手放回去!”
然而无论她怎么扯,顾映宁的手劲却大得惊人,不肯放松丝毫。眼看回流的血液越来越多,盛夏无奈只好放弃,问他:“顾映宁,你到底想做什么?”
见她不再扯开他的手,顾映宁终于稍稍松了些劲,顿了片刻后才缓缓启唇:“先前我和谈晶的那番对话你也听到了,无论你和许亦晖究竟在……”
“映宁!我刚刚那些话是白说了吗?”盛夏扬高声音打断他,正欲继续说下去,却听那边响起他低沉而清楚的嗓音。
“对不起。”
他慢慢地松开她的手臂垂下手去,盛夏愣住了,她不敢置信自己听到的这三个字。认识顾映宁这么久,哪怕是从前争吵得再厉害,他也从来不曾如此直白地对自己说过“对不起”这三个字。
仿佛是幻听一般,盛夏抬眼,只见他定定地望着她,于是良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对不起什么?”
“跟你争执,解除婚约,所有的一切。”他的嗓音依旧低沉。
也许是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刻的到来,所以盛夏除了怔忪完全不晓得自己该作何反应。她心里不是没有翻腾的,婚期的前一日他们吵得那样厉害,顾映宁说出的话那样刻薄,她甚至曾经以为自己会挨不过去。但她所有的不解、所受的委屈,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完全抚平的吗?
静默。
偌大的病房里唯有他们彼此的呼吸声,盛夏不知如何作答,而顾映宁,鲜少地同人道歉后却没有得到回应,脸色自然也因而渐次暗了下去。有风吹过来,翩跹了落地窗前质地柔软的窗帘,清新中又带着一丝萧怅。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江镡挎着食盒立在门口。
素来一张冰块脸的江镡挎着有粉红色小猪的食盒,这番场景盛夏怎么看怎么觉得乐呵,不禁抿唇轻笑。
原先凝固的空气因为江镡而又重新流动起来,盛夏转头对顾映宁道:“你先吃午饭吧,我回头再来看你。”
江镡道:“盛小姐,我也帮您准备了午餐。”
盛夏顿了一下,尔后笑笑:“不了,小晶子昨天就嚷嚷着今天给我煮这煮那。你应该还没吃吧,陪映宁一起吧。”身侧的顾映宁双唇紧抿不发一言,她转头冲他浅浅一笑,将他刚才血液回流的那只手轻轻地掖到被子里,说,“晚上跟你一起吃饭。”
直到盛夏离开了许久,顾映宁看着江镡在自己面前布菜,怔怔地依然不说话。抬起另一边的手打算握筷子,他才赫然发现,原来自己的手心早已沁满了汗。
就这么一连过了一个多月,盛夏除了右脚踝还没有完全康复外,其他外伤都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随着顾映宁伤势的不断好转,他早已从VIP重症病房搬到普通病房,而今和盛夏共处一室。
谈晶雷打不动地每天过来,盛夏知道自己已经好了很多,劝她多顾着些店,哪料谈晶双眼一瞪,道是担心顾映宁会欺负她,令盛夏哭笑不得。许亦晖也时常过来探望盛夏,每次都会带一束百合,说是最衬她。打了这么多次照面,许亦晖和顾映宁除了点点头打个招呼之外,似乎从没有过真正的交谈。盛夏能感觉到顾映宁的不悦,但她什么也没有表示,装作不知道。无论如何,许亦晖都是她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这一日,许亦晖傍晚下了班之后便过来了,除了馥郁芬芳的百合之外,他还给盛夏带了一袋子的水蜜桃。一颗颗饱满水灵,红扑扑的,似小孩子的脸蛋。
盛夏看了自然很是欢喜,拿起一颗闻了闻那扑鼻的香气后,睁大双眼惊讶道:“这可是奉化的水蜜桃?”
许亦晖接过来在手上掂了掂,哈哈大笑道:“阿夏你果然是个馋猫!居然凭着香味都能闻出来!”
盛夏扬扬眉:“可不是。”
许亦晖将那一大袋都在床头柜上摆好,转头问她:“现在想吃一个吗?我去给你洗。”
盛夏摇头,微微苦着脸:“小晶子刚才硬塞给我一块蛋糕,胃里还鼓鼓胀胀的。”
许亦晖哈哈笑道:“果然是谈晶这丫头的风格。”
他和她你一言我一语,彼此之间的默契早已浑然天成,连如此稀松平常的对话都能听出温馨来。顾映宁在另一张病床上,这一切自然也入了他的耳。原本,他是在随意地翻看一份财经报纸,听到最后,他却将报纸置于一旁尔后闭目养神起来。
盛夏虽说一直同许亦晖攀谈着,余光却从没有离开过左侧的顾映宁。当顾映宁合起报纸的那一刻,盛夏心知他必定是有些介怀了,只觉得有些好笑。正欲开口说些什么,却听病房的门“吱呀”
轻轻响了一声。她抬头,是辜子棠。
见到自己的顶头上司,盛夏有些局促,挣扎着想要翻身下床。
然而辜子棠怎会让盛夏下床,毕竟里头那张病床上躺着的人可是商业圈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躺着便好,否则你的护花使者可要找我算账了,哈哈!”辜子棠爽朗道。盛夏却是已起身,双脚也已然着地,边穿鞋边笑道:
“辜先生,我可还不想从公司卷铺盖走人。”
顾映宁也早已睁开眼,对辜子棠点了点头算作打招呼。辜子棠同盛夏寒暄了几句,叮嘱她要好好养伤,公司这里不用担心。盛夏道:“其实我也好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便可以回去上班了。”
辜子棠摆手,“唉”了一声道:“急什么!想工作的话以后时间多得是,现在先好好休息。”语罢,他顿了下又继续说道,“警方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吧?”
盛夏淡淡一笑,说:“还能有什么问题,一切都显而易见。裴晋葬身火海,也算是他自己造的孽自己背。”辜子棠叹了口气,道:
“人之大忌唯‘贪’字啊!他也曾是我昔日伙伴,岂料最终竟……”
盛夏见辜子棠言语之中痛惜不已,便好生劝慰了几句,道:“辜先生,人世无常,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也是各自的命运……”辜子棠倒微微笑了:“也罢也罢,逝者已矣,裴晋生前就算说过什么疯言疯语、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应该就此结束。”
盛夏顿了一秒,说:“辜先生想通便好。”
辜子棠起身理了理衣角,弹了弹袖口的褶皱,道:“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公司还有不少事,改天再来看望你们。”他朝顾映宁点点头,“顾先生,再会。”
辜子棠走了之后,方才一直立于墙边的许亦晖也开口道:“阿夏,时候不早了,我也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盛夏披上一件外套,转头看他温婉一笑:“我送送你吧,正好透下气。”
许亦晖余光扫了一眼里头的顾映宁,后者正双唇紧抿双目紧闭。他只觉好笑,自然不会推辞,愉悦地应道:“好,慢慢走,我扶着你。”
待病房的关门声响起只剩顾映宁一人时,他倏然睁开眼,眸中似乎有什么一闪而过,神色竟有些莫测。
夏季的傍晚就是长。F市的天空经常是灰蒙蒙的,而今日的晚霞却格外漂亮。大朵大朵的闲云在空中优哉悠哉地漂浮着,而那玫瑰色的晚霞更是穿透了厚厚的云层,映得整块天幕都粉得鲜嫩。
盛夏抬头望了望布满晚霞的苍穹,不禁被这极为罕见的景色所吸引,赞叹道:“这般美的傍晚,在F市倒是很少见。”
许亦晖和她在花圃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看着鲜艳的晚霞忽然微微一笑,转头问盛夏:“阿夏,你还记得我们一同去离岛的那次吗?”
盛夏张口“啊”了一声,原本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慢慢地回笼,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那个时候,他们在一起刚刚三个月,正是甜蜜中又带着些微磨合的时期。十二月中下旬,天气早已渐次冷下来,路上的行人也越发的寥寥。
圣诞将近,F市的圣诞气息这些年也逐渐浓了起来,满街的小彩灯在树上欢快地闪烁,那些五彩斑斓的颜色一树接着一树,仿佛荡漾成了一条条五光十色的小溪流一般,永不停歇地流淌着。大三的期末,所有学生都很忙,忙着复习考试、忙着打算以后。
许亦晖的功课向来很好,大抵是平时便学得扎实。盛夏经常捧着他的那些经济学书籍翻看,却总是没几秒钟便弃甲投降,直呼看不懂天书。谈晶那会儿总笑话她,说她一个学中文的居然还妄想无师自通地看懂经济学,简直是白日做梦。
终于,圣诞节在心心念念中到了。那天一大早,许亦晖就已经候在了盛夏的宿舍楼下,一连拨打了五个电话催她收拾好自己下来。盛夏纵使心里再埋怨时间太早,却还是十分地期待。这是他们在一起之后第一个盛大的节日,怎么会不期盼。
围好围巾缩着手下来,看到神采奕奕的许亦晖,盛夏一下子就扑进他怀里,许亦晖摇摇头,带着些微心疼道:“又不戴手套?”
盛夏一边往他怀里钻,一边仰脸笑嘻嘻:“有亦晖在,阿夏从来不用自己戴手套。”
许亦晖好笑又好气,屈指敲了敲盛夏的脑门,点点她的鼻头,叹息道:“你啊……”话语中满满的都是无可奈何的疼惜,下一刻竟果真从包里掏出一副手套来。盛夏一把接过来,在许亦晖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口,再度扬起小脸满是得意。
后来盛夏诧异了,原来他竟是打算带她去离岛玩。离岛距离F市区不过三刻钟的行船时间,但旁人都是夏日去的多,凛冽冬日去离岛,不只盛夏,怕是许亦晖也是头一回。
冬天的离岛自然不复夏天时候的郁郁葱葱,却也别有一番肃穆之中的苍然滋味。岛上的房屋甚至也和陆地上的不大相同,颇有些异国的风情。黄漆土墙,低矮的檐头,让盛夏看得不亦乐乎。
最美的,却是傍晚时分的落霞。
冬季的太阳自然落得早,五点多的时候,盛夏和许亦晖并排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望着不远处海平线以上红彤彤的天空。
“亦晖,你说海滩边那石头圈成的爱心究竟是人工摆的还是天然的?”盛夏紧紧地挨着许亦晖,两只手早伸进了他的怀里头,猫似的蹭蹭他的肩。
许亦晖沉吟了片刻,尔后说:“你相信是哪一种,便是哪一种。”
盛夏抬脸白了他一眼,哼声道:“故弄玄虚,哼!”
他温温一笑,正欲说什么,她忽然仰脖兴奋道:“快看快看!
今天的落霞好美!”
确实是极美极绚烂的落霞。最高处的云朵早已被渲染成了极其高贵的玫瑰紫,因着云层的厚薄不同而深浅不一。云朵之外的天空早已是一片深蓝,偶尔夹杂着一丝苍茫。近处的云则大团大团的镶上了金边,黄澄澄的一片。在这些的陪衬之下,一颗不大不小的“鸭蛋黄”被海水柔柔地托在地平线之上。暖洋洋的光洒在海面上,竟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盛夏已然完全被落霞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真切地体会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原来竟是这般的动人心魄。
经许亦晖这么一提,盛夏自然想起了曾经一同惊叹过的那场仿佛盛宴般的落日。她歪着头笑道:“亦晖,说起来你还欠我一次日出呢!”
那次看完落霞盛夏感叹不已,回程的时候一直摇晃着许亦晖的胳膊,也正如现在这般歪着脑袋的模样,带着撒娇的语气一再说:“亦晖,下次我们去看日出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许亦晖起初故意不理她,任由盛夏蹭着自己的肩头笑得谄媚。直到她终于佯怒,瞪大双眼扬高声音:“许亦晖,你从还是不从?”他这才忍俊不禁,终于开口,温和的声音里有着格外明显的揶揄:“嗯,就从了吧。”
只是后来,却没有机会了。
这一段温馨甜蜜的回忆,于许亦晖而言自是清晰得历历在目,甚至连当时盛夏皱起鼻头这样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此刻的他和她并肩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夏季的晚风,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许亦晖接过盛夏的话,眼里含笑,问道:“那阿夏,这次,你从不从了我?”
盛夏的笑容却是慢慢地敛住了,到最后在唇边竟拉成了一个略微苦涩的弧度。
她凝视他,他也不避,好似没看到她的苦涩一般依旧笑得温柔。许久,盛夏倒是先低下了头,盯着地面,她说:“亦晖,我真的很感激上苍,因为你还活着,因为你这些天来的照顾,也因为我们曾经相遇相知……但是,”她还是抬起头,看着许亦晖,“对不起亦晖,从前我对你的感情真的回不来了。”
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终于将这句话一口气说了出来。手指紧紧地扒着长椅的缝隙,盛夏浑身发麻,觉得自己仿佛才是被抛下的那个。
许亦晖不愠不恼,好像这番话根本在他意料之中。他只是兀自勾了勾嘴角,然后轻声道:“阿夏,刚才的那些话我会当做你没说过。”
“亦晖!”盛夏却有些恼了。她知道也许这对他来说一点儿都不公平,可她也不愿再让他还存留幻想、不愿看着他再这么徒劳无功地走下去,“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我爱顾映宁,不管他爱不爱我,我确定我爱他。亦晖,你就当我是个负心人好了……不要再执着于我了,好吗?”
望着她咬唇的脸,许亦晖知道她其实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可他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所以他斩钉截铁:“不好。”
他问她:“阿夏你告诉我,我究竟差了他多少分?我慢慢补回来,一分一分地补回来……你多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能超过他!”
歉疚,无力,苦涩,百种滋味涌上心头,盛夏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枉然。将脸深深地埋入双手,她静默了良久,连叹气都带着沉沉的疲乏。
“亦晖,感情如何用分数来衡量?”她慢慢地站起身,只觉伤痛未愈的双腿格外沉重,“天色晚了,回去吧。”
许亦晖没有说话,却从口袋里缓缓地掏出了一支烟来。他抬眼:“先上去吧阿夏,我想在这儿再坐会儿。”
什么时候起,居然连许亦晖都抽起烟来了,他曾经是那么讨厌烟味的一个人。时间,真的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沟壑。
盛夏点点头,抿唇努力笑了笑,转身一步一顿地离开。
暮色越垂越深重,直到晚霞终于落尽,整片天幕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墨黑。那样的墨黑,就如同他眼眸里浓重的悲哀。他嘴里含着烟,却一直都没有点燃。
到底,他还是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