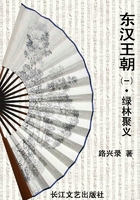伤心证明不了爱有多笨,别怕我报复好还给你公平
回到病房,顾映宁已经换下了医院的病号服,穿着他的丝质睡衣。
这件睡衣其实还是盛夏买的。有一次她去逛街,也不知哪根弦拨动了,心血来潮地买下来之后才暗觉懊恼。且不说顾映宁欢喜与否,单是睡衣这样的礼物,对那时的他们而言并不是那么合适。
幸好顾映宁似乎很喜欢这件睡衣,也一直穿到现今。
盛夏推开门,一跛一跛地挪进来。顾映宁抬头,看到她写满疲惫的脸,却是淡淡的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手边的财经杂志。
最后倒是盛夏自己憋不住了。她从自己的病床上起身下来,慢慢地在顾映宁的床边坐下,抓起他的手把玩起来。当盛夏搬弄起他的第四根手指的时候,顾映宁终于缓缓抬眼,不淡不咸地开口说了句:“你很闲?”
被他这么一堵,盛夏心头原本萦绕的那些沉重竟一下子消退了不少。瞪了顾映宁一眼,盛夏也并没有放开他的手,微微垂首,洁白如瓷的脖颈露了出来,她低低道:“映宁……你说我该拿亦晖怎么办?”
低着头的盛夏没发现,顾映宁的唇线在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刹那收紧,甚至连眸色都瞬间变深。他们回避了许久的话题终于还是要提及了—或者说,是盛夏终于准备好来面对这个横在他们之间的结了。
他只觉喉头一干,张口想说些什么,却到底没发出声来。
盛夏仍旧垂首把玩着他的手指,停顿了片刻后才继续道:“我没法子冷脸赶亦晖走,毕竟他是我曾经那么爱的人……可是现在,当一切已经物是人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面对他的不放弃。”
她抬起头,与他的目光交汇。也许是因为他的眸色太过凌厉,亦或是曾经的那场争执浮上脑海,盛夏苦苦一笑,说:“映宁,不管你相不相信,现在的我已经不爱他了。”
手忽然触碰到他的掌心,感觉到那里的湿冷,盛夏起初一愣,而后嫣然笑了,双眼里瞬间点起的光亮将她先前所有的情绪都一扫而空。她喜笑颜开:“映宁,原来你心里是这么紧张我啊?你看,手心都是冷汗。”
她发现得太快,猝不及防下顾映宁自是极其尴尬。赧然之后他竟有些恼怒了,一把抽出自己的手:“别坐在我床边,两个人挤在一起热不热?”
他的耳边正微微地泛红,盛夏当然不着他的道,仍旧笑得眉眼弯弯。不退反进,盛夏索性掀开顾映宁身上盖着的毛毯,自己双腿一挪也睡了上来。同他靠得这样近,他的呼吸就洒在她的耳畔,痒痒的,暖暖的。
她居然还继续得寸进尺,手指点着顾映宁的鼻尖,轻轻笑道:“映宁,你害羞的样子真不可爱。”
眼看着顾映宁就要怒目,盛夏赶在他前头又开口,“可是我喜欢。”
她的话音落下,他却是怔住了。
将近四年了,这是她头一次如此直白地跟他说,她喜欢。自从裴晋的事情发生以来,尽管她不再浑身是刺针锋相对,但他真的从未想过她竟会这样突如其来地对他说喜欢。曾经他以为,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这天真的到来的时候,顾映宁发现自己竟不知该如何回应了。仿佛喉咙里含着一大口苏打,突然的刺激让他急着想咽下去说话却被激得胸口发聩,反而连一个音都发不出来了。
顾映宁只觉得心口发胀,良久之后竟只是模模糊糊地应了一声:
“嗯。”
虽然他只是含混地说了一个“嗯”字,然而顾映宁亮得惊人的目光和那透出无比悦然的神采让盛夏明白—其实他也是在乎的。曾经她不想说,也不敢说。她怕自己一旦坦诚之后便被他打落地下永世无法翻身。然而因为裴晋的疯狂,她开始后悔,若是那天顾映宁没有来,若是自己和他没有得救,那么这些话是不是就因为她的害怕而永远无法有让他知晓的那一天?她害怕他的答案,但她更害怕自己来不及告白。而现在,他的反应让她明白原来自己并非一头热—但这还不够,她想要的比这要多。
盛夏用肩头轻轻撞了撞他,有些期期艾艾地望着顾映宁,咬唇:
“就是一个‘嗯’字吗?你就没有别的对我说吗?”
顾映宁欲言又止,眸色转了几转,最后略微有些粗声粗气地快语道:“还要说什么?莫非我谁都救吗?”
莫非我谁都救吗?
顾映宁因为有些窘迫而疾声的一句话却让盛夏豁然开朗。倒是她自己作茧自缚了,若是她之于他不重要,他又怎会单枪匹马地来救她?原来早在那天他敲开裴晋的门说“对,今天刚来的”起,他便已经给了她最明显最直白的答案。
他已经将自己的心透明地摆在了她面前,她却在纠缠于为何之外的部分不是透明,真是盲啊。
喜色上了眉梢,晕染了眼眸,盛夏凑近顾映宁,鼻尖距离他的鼻尖只一厘米不到。她笑,说:“映宁,你越看越傻。”说完她闭上眼,不由分说地在他唇上印下一个章。
许亦晖的事就先搁置一旁吧,相守顾映宁的时光,更重要。
顾映宁终于可以出院回家静养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次凉了。第一场秋雨冲刷过后,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薄薄的苍茫之中。
盛夏已经复职大半个月了,从上回到她出院,许亦晖后来只再来过一次。那天他过来的时候谈晶正好也在,一转身看见许亦晖谈晶吓了一大跳:“天哪!许亦晖你是山顶洞野人吗?都不晓得刮胡子!”
听到谈晶的惊呼,盛夏抬头望向门口,却顿时愣住了—这样憔悴而胡子拉碴的人,哪里是她记忆里永远云淡风轻笑容温暖的许亦晖?
顾映宁那日恰好去楼下做B超,谈晶眼珠子转了一转,对许亦晖打了个招呼后便道:“小夏、亦晖你俩慢慢聊,我出去买些今晚要做的菜。”盛夏知道她是特意给自己和许亦晖独处的机会,便也不曾太注意,只是微笑看着许亦晖。
他走近了一些,嘴角扯出一丝淡淡的笑意,说:“最近如何,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盛夏拍了拍自己的腿示意道:“已经好了,医生说过几天便能出院了。”
许亦晖点点头:“那就好。”他在她身侧的那张小椅子上坐下来,大长腿就这么蜷在靠近床边的狭小角落里。
盛夏觉得有什么她不愿再面对的事就要发生,张口刚想率先说些什么,他却已然出了声:“阿夏。”
这样憔悴的许亦晖,满眼的血丝、深陷的眼窝、拉碴的胡子,让她除了静静地屏息听他说完,再无他法。
“阿夏你不用太紧张,我只是想告诉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身边的人。不过,”他深吸一口气,顿了一瞬后继续道,“不过对不起,我做不到放手,就当这是我和顾映宁之间的一场竞争吧。”
他说完之后牵起盛夏的左手,在她手背上轻轻地落下一个吻。
那一刻,盛夏的心很疼—那是对许亦晖的心疼,对所有旧时光沉淀的心疼。直到许亦晖走了良久,她眼眶里的泪虽然不肆意却一直涓涓。
原来,无法回应自己曾经爱人的深情,竟也会这般痛。
经过这一事,盛夏同顾映宁的关系对于辜子棠而言已不再是秘密。
无谓在辜子棠跟前做戏,顾映宁出院后便邀约他共进晚餐以感谢他这些年对盛夏的照顾。但这次的意外多多少少也是因他而起,辜子棠怎肯由顾映宁做东,故而到最后倒变成了盛夏和顾映宁去赴约。
辜子棠在F市惯常去的些酒店不过七八个,最中意的当属徵洲渔港。果不其然,这次去的还是这家店。
渔港吃得多的自然是鱼,河鱼、海鱼,应有尽有。盛夏其实并不喜欢吃鱼,平时都是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可惜这回辜子棠似乎是想来个全鱼宴,虽说是盛情而点了一桌的名贵鱼,盛夏却一点儿胃口都没有。看着满桌的河鱼、海鱼,她草草尝了几口便放下了。
顾映宁倒是还好,同辜子棠一人一盅白酒地互敬着。辜子棠哈哈大笑:“小夏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是好,这么久了我们居然从来不晓得你同顾总的关系。”
盛夏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倒是顾映宁开口,带着一丝宠溺的口气微笑着说道:“她啊,怎么都不肯公开,一直说担心旁人的眼光。”顾映宁几时用过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过这样的话语,盛夏一时间竟怔忪地不知作何反应来。
辜子棠抚掌而笑:“想不到顾总竟也是这般长情之人,来,辜某再敬你一杯!”顾映宁端起酒盅,和辜子棠一碰而饮。放下酒盅后,顾映宁指尖摩挲着杯口,顿了几秒后出声,说:“辜总裁,我想替盛夏请两个礼拜的假,不知……”
他停住了没有说下去,尾音轻轻地拖得很长。然而辜子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在起初的愣怔过去之后复而笑了起来,意味深长道:
“看来,顾总似乎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可以,当然可以!”说着他转向盛夏,笑呵呵地说,“小夏,算起来你在我这里几年了倒也不曾放过大假,这次好好地散散心啊!”
顾映宁并没有同盛夏提及过,因此盛夏也是初闻这件事,这回是比之前更加长久的怔忪和惊诧。她愣愣地抬头看向顾映宁,他也正含笑望着她。她看着顾映宁瞳仁里倒映出来的小小的自己,钝钝地重复了一声:“请假?”
他点点头,依旧言简意赅:“嗯,带你出去转转。”
他的一句话就这么决定了她之后两个礼拜的生活,而她,接受得那么怔忪而欣然。过了很久之后她才彻底反应过来,心底喜悦的泡泡一阵一阵地翻腾,甜得她连夹进嘴里的咸鱼都变得甜蜜无比。
离开徵洲渔港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初秋的F市凉意正浓。
盛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顾映宁原本正在和辜子棠说话,她以为他没有看见,然而他却靠过来一伸胳膊将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
顾映宁和辜子棠喝得都不少,此刻两人皆是满面潮红、满身酒气。
转头看到他极亮的眸子,盛夏心下了然,他醉了。
江镡早就在酒店门口候着了,坐进车,顾映宁解开衬衫上头的两个纽扣,松动了下脖子,对江镡淡淡道:“去何记米粉。”
盛夏惊诧:“喝了这么多酒,你还要再吃东西?”目光落在他刚解开的两枚纽扣上,她微微蹙眉,“天这么凉,要是着凉了我可不管你。”
似乎是从那次意外之后,盛夏在顾映宁跟前变得渐次活泼生动起来,她不再收埋自己的情绪与想法,也再不复从前的淡然。
顾映宁忽然笑了。他嘴角上翘,露出洁白的牙齿,眼底流动的除了满满的笑意还有些别的神采。一把将她拉进怀中,顾映宁凑近盛夏的鼻尖,捏捏她的脸颊:“小管家婆。”
那样近的气息呵在她的周身,盛夏悄悄红了耳根,面上却是一凛,捂着鼻子状似要躲开道:“满身酒味,臭死了!”她这么说着,顾映宁却好像是要同她唱反调似的,故意搂她搂得更紧,整张脸甚至埋进了她的颈间胡乱地蹭着:“居然敢嫌我臭……盛夏你真是越发大胆了……”
他的呼吸是那样灼热,熨烫却又痒得她不由躲得更厉害。盛夏笑得打跌,边竭力地推开他,边喘着气道:“顾映宁……顾映宁你给我停下!”
他终于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将盛夏的胳膊轻轻地环在了自己的腰间,顾映宁俯下身,眼眸里笑意浓浓神采奕奕。似乎在记忆中,盛夏很少见到这样开怀的顾映宁。他的欢喜那么轻易地就感染了她,让她整个腰肢都软了下来。糯糯地倚靠着顾映宁,盛夏不知道此刻的她看在他的眼中,是那么的顾盼生姿。
“盛夏,搬回来,好不好?”他开口,声音不高,然而在这样狭小的车厢里却那么清晰。
她凝视着他,好像意外却又意料之中。他的目光也灼灼地紧紧注视着她,仿佛有种魔力般,盛夏只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融化其中一样。
几乎是下意识的,她点头,应声:“好。”
话音方落,他的唇已经温热地覆了上来。喜色飞上他和她的眉间,这天地间除了彼此的呼吸声,万籁俱寂。
他的舌头在她猝不及防的时候长驱直入,同她的舌激烈地搅缠在一起,那样大的力道让她只觉舌根酸麻一片。仿佛觉察到盛夏的不适,顾映宁终于慢慢地退了出来,牙齿轻咬着她的下唇,一下、一下地厮磨着。盛夏觉得自己是一叶摇摇晃晃的扁舟,而他就是那汪最宽广浩瀚的海洋,她醉心于他的胸怀,哪怕水漫覆舟万劫不复都在所不辞。除了下意识地紧紧攀住他的腰,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该做什么。
待盛夏缓过神来,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车子已经停了下来。懵懵地转头看向窗外,正是何记米粉。她并没有听清顾映宁到底说了句什么,下一秒江镡已经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
这才意识到车厢里其实一直都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想到方才那个绵长的吻,盛夏不由得红了颊。她的眼波原本就有些娇媚,这样一个横目过来竟是那么潋滟。她微怒,嗔道:“都怪你!江镡可一直都在……”
顾映宁笑得气定神闲,道:“又不是头一回了。”
盛夏窘迫而愠:“你还讲!”
他倒是满不在意,大概是酒精的作用让他的情绪鲜少地这般外露。将下巴搁在盛夏的肩头,顾映宁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他的语气中竟透露出一丝脆弱来,带着走遍万水千山后终于寻到港湾的归宿感,他低低道:“盛夏……幸好你还是我的,幸好。”
她的心在那一刹忽然疼了。她又何尝没有庆幸他还是她的呢。
她曾经以为他原来是不爱自己的,以为她和他的缘分就要这么止步了,以为她再不能听到他用淡淡的却又带着亲昵感的语气叫她的名字……她以为她会崩溃,然而命运到底还是好心的。在痛彻心扉之后,幸好他们都还来得及重新开始。
明明她滴酒未沾,然而盛夏觉得自己也已然醉了。借着酒意,她的手抚上他的颊,触摸到他些微刺手的新胡楂。原来,他的眼角早已有了这么多细细密密的纹路,可是看在她的眼里,却是那样亲切动容。
生命原就是静谧的河,他和她是徜徉其中的两条鱼。因为他的温暖,她笑靥如花,熏熏醉意中她第一次将自己透明地坦白在他面前,说:“顾映宁,我爱你。”
下一秒,天和地都旋转了方向,他的味道翻天覆地地笼罩了下来。
比之刚才,这个吻才是真正的深长炽烈,让初秋瞬间变身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