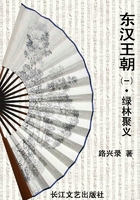她站了起来。
你要走了?桑青有点不相信。
是的,我现在需要睡觉。
你看上去很勇敢,其实不是。他望了望天空,太阳正要从广 场的另一侧落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睡觉,可以跟我睡,我会让你很快乐。
明妙讨厌说好的,答应别人就会不自由,说“不”才是权力,可是这会儿她没办法说“不”,也走不了,这把刀得让路。
明妙舔了舔嘴唇:你叫桑青彭措,对么?
他点点头,彬彬有礼。
我不喜欢你离我这么近,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他咬紧了后面几颗牙,那样子是想打架吗?他也许喝酒了。
明妙转动眼睛,微笑起来:你要欺负我么?
他一下子软下来,晃晃肩膀:男人只能保护女人,别走,我可以为你唱歌。
明妙点点头,迅速离开,她已经为他浪费了很多时间。
结古镇,风马客栈。
客栈地址刊登在一本LP指南上,李明妙住在这里。
客栈有华丽的藏式木雕,大门上挂着蓝色棉布帘,上面绘有宝瓶和双鱼图案,很漂亮。风马旗帜在屋顶翻卷,从客栈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结古镇广场。
客栈走廊狭长,木楼梯红漆剥落,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挂满哈达。楼梯旁摆着热水瓶,一字排开,装满甜奶茶,有五磅的,还有八磅的,从四个方向都能拿到。明妙拎起一壶甜奶茶,上到三楼。她住在独立的小房间,位于这一层的偏僻角落,屋顶很高,有一张靠窗的桌子、一把椅子。明妙坐在桌前,光着脚,开始整理采访笔记。
在经历过几次跳槽之后,李明妙现在居住在上海,为一家旅游杂志工作。
杂志销量稳定,需要长期出差和采访,生活动荡,手艺人式的工作方式,这恰恰是吸引明妙的微光。她专注于工作,消耗极多,也获得薪水和认可。工作是值得依赖的,从不欺瞒,也从不背叛,给了明妙想要的一切,她并不觉得辛苦。
在上海五年之后,明妙依然迷路,孤单,不涉足百货公司,很少参加热闹派对。她不想取悦集体,内心并无归属感,别人认为重要的,她通常漠视。
在编辑部,明妙独立承担一些专题的撰写,每个月花费十五 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外出采访。杂志社时常承接一些有经费赞助的采访项目,安排员工飞往国外,专人接待,待遇优厚。明妙对此并不热心,她喜欢看花豹悄悄接近一群羚羊,迷恋有意思的面孔、有故事的人,但她很难被自然景观感动。有一次她用欣赏的口气描写中央公园的草坪,特别是漂亮的落日,文章的最后,她写道:如果没有和人有关的故事,中央公园实在无聊极了。
在上海,明妙没有亲人,也没有恋情。夏安是唯一与她保持稳定联络的人,他是杂志的主编。
每次明妙出差回来,都会单独和夏安喝杯咖啡。他们常去的咖啡馆很小,柜台上放着奈良美智的梦游娃娃。一个维也纳姑娘站在吧台里,边喝咖啡边煮咖啡,她长着水蓝色的眼睛,开一部哈雷摩托车,每周花一天时间看歌剧,到那一天,咖啡馆不营业。
夏安包容明妙的个性,为她开设专栏。
专栏渐渐有了固定读者,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有些人表达爱慕之意,希望能够与她见面。
有一次,明妙收到一个寄自湖北某小镇的包裹。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椭圆形盒子,金色的,可以打开。明妙找了一根皮绳把小盒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人告诉她:这是藏族的东西,叫做嘎乌盒,用来装最珍贵的东西,贴身供养。她喜欢这礼物,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寄信人没留名字,一个字也没写。
明妙并不想寻找寄信人,她说:写的人和看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
夏安拿起她脖颈上的嘎乌盒看了看,又放下,一声不响。
傍晚来了,这是明妙最喜爱的时刻,结古镇正在改变。
明妙捧着一杯滚烫的奶茶,爬上桌子,背部倚着窗框,外面是熙熙攘攘的集市,可以看见广场上高大的飞马雕像。在荒芜的 暮色中,古镇渐渐显露出残忍的一面,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勤劳、更多的忍耐才能和高原的本性共存。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看见高原上大团大团浓密的白云,会感动得哭出来,以为这片土地充满吉兆和信仰,给人带来安慰,但它可能转瞬成为黑暗之地,变得封闭、冷酷,对穷人和修行者失去耐心。
风马客栈很热闹。二楼提供简餐、咖啡和青稞酒,人们常常聚集在那里,喝酒、唱歌、打牌、抽烟,讲述结古镇的故事。
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明妙就听说了影子活佛。
看,就在那里,二楼靠窗的桌子,他常坐在那儿。
第一次来这儿的人都朝窗边看,桌子空空的。
他在哪儿?
这是一个秘密。
关于一个女人。
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说。
第一次来这里的人接着问:影子活佛是谁?
有人很热心地从头讲起他的传说:影子四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真玛巴。在藏语里,“真玛”的意思是影子,“巴”是对人的尊称。在高原的正午,小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游戏,叫踩影子。玩着玩着,小伙伴们很快发现,谁也没有办法踩到真玛巴的影子,那个跑得最快的男孩,一旦追上真玛巴,抬脚要踩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影子收回身体里了。
藏族人相信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四岁的真玛巴,他可以任意收放影子,他大有来历。
他是个活佛,他总有与众不同之处。
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影子活佛从不笑出声,也不说话,他用手指蘸着青稞酒在桌上写字。那些倨傲的康巴汉子路过这儿,看见 影子活佛,会走过来,捧起他的手,放在额头上,行触头礼。
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他?
这要看命运怎么安排。
“有一天,结古镇来了个汉族女人,她挑开风马客栈的蓝布帘,就这样走进来,两个人目光交会在一起,就这么远,”风马客栈的老板娘伸出手,比画了一下长度,继续讲,“从这儿到那儿,隔着十碗酥油茶那么长。影子活佛一看见这汉族女人,就站起来,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是我的绿度母来了。说完,他就跟着这个汉族女人走了。他就这么不见了,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那汉族女人是谁?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没人知道。
镇上的人整整沉闷了两天。他们到风马客栈来,围着那张桌子。影子活佛不在结古镇了。
你说,他会不会死了?
有些人感到心里难受,空落落的。
他可能发财了,再后来生好多孩子,男的像活佛,女的像绿度母。
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过去,影子活佛没有回来。
结古镇人说:他肯定会回来的,那个汉族女人来到这儿,看了他一眼,是来帮助他完成心愿的,等他实现了心中梦想,就会回来的。
人们举起酒杯祝福他,说“扎西德勒”。
一个少年问:影子活佛会变成什么?
嗨,这很难说。
木头桌子还在,它不会改变,窗户和钉子不会改变,没有命的东西才不会改变。
结古镇人开始打赌,猜想影子活佛会变成什么。赌注是一杯 又一杯青稞酒,酒让他们重新高兴起来。藏族人信奉着古老的法则:难以承受改变的人,由于不敢追随心之方向,更加得不到想要的生活。
在风马客栈的二楼,影子活佛写下最后一句话:
心有疑云,勇气先行。
他一直独来独往地生活,从未说出过心中疑惑。他庄重地坐在那儿,用手指蘸着白色青稞酒,在桌上写字,现在桌上的字迹和他一起消失了。
明妙喜欢这结局,这句话让她感到影子活佛是个诗人。
每个来到风马客栈的人都会再听一遍这故事。
夜渐渐深了,青稞酒闪耀着植物的光芒。有人沉默不语,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心中的愿望。大多数人不能把梦想变成现实,是因为不够勇敢,一旦人真正鼓起勇气,决心完成一件事,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影子活佛说:人和人,是凭勇气分出区别的。
所谓梦想,只是等待发生的现实,它不会永远等下去。
不像结古镇人讲得那样神秘,明妙说:这只是一个男人的故事。
她慢慢喝掉热奶茶,开始给夏安写邮件。
她告诉他已经在当地找到了摄影师,采访还要持续几天,高原反应剧烈,她吃了一点止痛药,手臂和脖子开始蜕皮,失眠,但精神尚好。风马客栈偶尔停电,她买了白色蜡烛,还有一本关于唐卡的图书。书很沉重,在淡淡的烛光中翻看,那些精妙的图案笔触洁净,天真自持,看得久了,眼睛难以承受这样强烈的自由,有泪水木然滴落。
邮件的最后,明妙对夏安说:
没有人能回到过去,让一切重新开始,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创造出一个新的结局。如果影子活佛在这里,我会喜欢他,他是个老老实实的男人,不对自己撒谎,也不逃避问题。
还有,影子活佛用手指挖果酱吃,和你一样。
邮件无法发送。
在这样便捷的时代,一个人想要消失不见是很容易的事情。
明妙独自吃饭,喜欢坐在靠窗的角落里。
结古镇上有很多川菜馆,所有菜都理直气壮,一个大盘子,一大把辣椒,跟一大把盐,还有各种油炸面食。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明妙相信这是真理。起初几天,明妙勇敢地接受了几次嘴唇开裂,她变黑了,也更粗暴,幸运的是她很快找到了热甜茶,也爱上了本地的牦牛酸奶,清爽浓稠,放一大勺白砂糖搅拌均匀,用勺子挖着吃。
头痛的时候,就去门口逛集市。
集市很热闹:卡车的噪音,小贩叫卖、牲畜嘶鸣,音箱里传出诵经声。肉摊上摆着大块切好、风干的牦牛肉。有人兜售兽骨、影碟、珍贵的宝石,还有一些古董,其中一些不那么真。周末的一天,忽然有人搬来几个水箱,展览活的章鱼,鲜红的触手,凸起密集的白波点,它们长得像日本怪婆婆草间弥生。
这混杂在一起的摊位,样样东西,都通往尘世的欢愉。
在户外俱乐部推荐的装备店里,明妙买了把德国产的刀,刀身素净,没有丝毫光华,看起来很可靠。晚上,她把刀放在枕头底下,在黑暗中躺平,做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梦。
梦见独自在月亮下放风筝,一个蓝风筝,是一尾手绘的蓝色鲤鱼,它径直飞入夜空。
记忆就这样在梦境中复活。
那是李明妙的城,一座遥远的北方之城。
道路笔直开阔,路边种植高大的树木——国槐树,威仪如国王。城池中心一座钟楼,一座鼓楼,二者遥遥相对,历经四百多年。黄昏时分,暮鼓沉沉敲响,蝙蝠成群结队在钟楼上空盘旋。
古老城墙毁了又修,保存完整,明妙在这里出生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