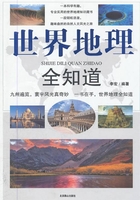土登寺的阳光总是格外透明。
小喇嘛跑来跑去,或三三两两聚拢,神情庄严,眼神澄澈。
他们轻声交谈,温柔中略含一丝忧伤。院子里有很多流浪狗,一些女人坐在白塔下,从大殿里传来香火的味道,诵经声四处回响。
明妙和小嘎玛一起串念珠,他是江阳堪布的助手,在寺庙里学习绘画唐卡。
他串好一个扁扁的、镶着红色小珊瑚珠的手环,系在明妙手腕上,对她笑,牙很白,耳轮像佛祖。
明妙摘下手表,一块圆形手表,背面透明,看得见里面嘀嗒行走的机械零件。这是真年的礼物,在一张照片里,她穿着曳地长礼服,手腕上也戴着这块表——那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她把手表递给小嘎玛,说送给你。
他摇着头,这个不行不行。
我不管。她拽断一根绳子,把手表捆起来,绑在他手臂上。
小嘎玛盯着嘀嗒转动的小齿轮,很着迷,伸出另一只手,飞快地摸一下表盘,又摸一下,羞涩地笑了。他说:我给你画一个佛吧。
风从藏青色山峦的另一侧吹来,在空旷处盘旋。小嘎玛蘸着朱砂,在明妙的锁骨正中央画了一尊佛像。他问:你有什么心愿对菩萨说?
我要找到丢了的东西。
他把毛笔尖放在嘴里舔一舔,嘴唇上出现一抹庄重的红色。
你丢的东西一定有人捡去了,为什么还要找呢?
是啊,为什么还要找呢?她无言以对。
她对江阳堪布说:我嫉妒小嘎玛。
为什么?
他有一种不损的气质,他心里是这样,表面上也一样。而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实际上已经完不成这人生。
江阳堪布放下手中的书本,指着一段话,说你念出来。
她念:无论你怀着多大的善意,仍然会遭遇恶意;无论你抱有多深的真诚,仍然会遭到怀疑;无论你呈献多少柔软,仍然要面对刻薄;无论你多么安静地只做你自己,仍然会有人按他们的期待要求你;无论你多么勇敢地敞开自己,仍然有人宁愿你虚饰出一个他喜欢看到的你。但一定要记住,你的人生是你的,不是任何人的。
念完了。
她苦笑一下,总有人把所有的道理写得一清二楚,可这只不过是书上的字,看似高妙,却长不出粮食,抵挡不了噩运。
江阳堪布,我为什么不快乐?
明妙,一位佛教导师说:我很多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不快乐。
如果要应对它,必须接受你是孤独的,一旦接受,你就没有了不真实的期望,情况就会变得好一些。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爱呢?为什么要彼此倾注这样强烈的感情?
因为这是让人最接近神的感情。
在上海工作一年半之后,明妙前往嘉那玛尼城采访,在结古镇广场上,她与桑青相遇。
从结古镇向东三十二公里,通天河西岸,有一个地方叫勒巴沟。
这是一条八公里长的峡谷,两侧山崖陡峭,岩石呈现古铜色,最高处有三四百米,悬崖向里倾斜,将头顶的天空划开狭长的裂口。山沟里灌木低矮茂密,清流湍急,水中遍布巨石,大的如一幢房子,小的也要两个人双臂环抱。所有石头上都刻着六字真言,据说这是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来的。
在桑青的帮助下,明妙租了一部车前往勒巴沟。司机阿宝是桑青的朋友,一个活泼的藏族人,他很健谈,会谈一些挺严肃的事情,比如正义、责任和死亡之类的,也会说说怎么样让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他睡觉。
每个严寒的冬天,通天河会被厚实的冰面覆盖,聪明的藏族人用细沙在冰上书写巨大的六字真言,太阳照耀的时候,沙子吸收阳光热量,渐渐融掉下面的冰,一层一层坠落河底,冰面上就呈现出一幅壮观的镂空图案。
此刻光亮深长,春天尚未来到高原,在悬崖遮蔽的河面上,镂空的字体间有雪白浪花飞溅而出。阿宝念一声:唵嘛呢呗咪吽。明妙也跟着念:唵嘛呢呗咪吽。她按住心口,泪水扑簌簌掉落。桑青举起相机,拍摄明妙的侧影。在她的轮廓背后,是裸露的悬崖,上面有一幅阴线石刻的礼佛图,三米多高的释迦牟尼佛 偏袒右肩,立于拱形火焰门下,文成公主手捧莲花面朝佛祖,脚下跪着鹿和老虎。
三个人在唐蕃古道上寻找文成公主庙。
风很大,从勒巴沟口一直吹过来,庙门前五色风幡猎猎作响。明妙采摘野生紫云英供奉在大殿里,红衣喇嘛取来清凉的水,滴在她的额头和手心。僧人打开一扇隐蔽小门,请他们进入,一面巨大的岩洞矗立眼前,文成公主就站在那里,她丰满优美,有三米多高。红衣喇嘛讲解着,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经过这里,石头上就自然显现出她的样子。他说:一个女子的身影可以呼唤出石头里的神佛。
明妙将手心贴在额头上,让清凉的水滴在佛前汇合。
佛龛上有青花瓷碗,漂着一白一粉两朵莲花,白莲生白色烟,粉莲生白色鸟。明妙俯身去看,水中映出自己的影子,一轮满月正在眼里,月亮底下有文成公主的模样。僧人们点燃野生柏木,芳香浓烈。
桑青四处拍摄照片,明妙和阿宝坐在庙门口等待,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阿宝递过来一支烟,她摇摇头:我戒掉了。
阿宝呵呵笑着,露出白森森的牙。
明妙,你相信人有灵魂吗?
我相信。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阿宝扔掉烟头,咚咚地原地跳了两下:灵魂嘛,就像唱歌跳舞,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别人都拿不走。
明妙仰头大笑:阿宝,我应该抱抱你,这话讲得真好。
他真的走过来,用力抱了抱她,粗壮的手臂线条漂亮。明妙抓住他的手臂,试着咬了一下,没用力,咬不动。他显然有点不满意:明妙,你要吃得多一些。
她点点头。
明妙,你怎么认识桑青的?
他朝我的窗户扔石头,砸碎了客栈玻璃。
阿宝哦了一声:他是为了不让你睡着。
你真的这么想?
当然,你又不会梦见他,为什么要让你睡?
阿宝替他赔了玻璃钱。
桑青还没有回来,阿宝朝远处看看:明妙,你还没跟桑青睡过?
明妙又点点头。
你不喜欢他?
哦,我只是要等到合适的时间。她跳上一块高大的石头,双脚晃晃荡荡:比如夏天,夏天我会觉得他更迷人。
阿宝咧嘴笑了:这想法很不错,你不用担心,桑青会一直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他在遇见你之前很懒,现在他喜欢干活了,还在变蠢。这说明他喜欢你。
明妙惊奇地绷起脚尖:我可没看出来桑青在变蠢。他很好看,而且很好闻,不是么?
阿宝喷了一下鼻子,像一头真正的野马:明妙,你也变蠢了。我们藏族人说:蠢人可以不用脑子,不用眼睛,跟随你的心和鼻子走吧,看起来很危险,实际上更不容易迷路。
每个男人都不是吃素的,这是真话。
在非洲,男人或许是狮子或者犀牛;在印度,男人是孟加拉虎;藏地的男人更像野马,阿宝是这样,桑青也是这样。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异常强烈,年轻,强壮,充满好奇,因为不理解世俗的规范而对它不屑一顾。
暮色苍茫,一个牧人赶着他的牛羊回家。
桑青从山坡上奔跑而来,摄影包啪啪拍打大腿。他喘着气,一直跑到明妙跟前,对她说:送给你。他伸展手心,里面有一颗东西,像小石子,暗黑色,脏脏的。
这是什么?明妙小心翼翼地拈起来,转动一下。
桑青很兴奋:这是莲籽,一粒古莲籽,有一千年了。在长安城里,富贵人家的公子收集了几十颗,装进瓷瓶,陪着他下葬,后来这个公子的墓被打开了,植物园的人把莲子拿去种,还能开花。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像碗口那么大,是你喜欢的白花朵。
明妙欣喜地屈起手指,把握着古莲籽的拳头放在嘴唇上,亲吻一下,问他哪里来的。
他得意扬扬:师父给的。文成公主家乡来人了,送来三颗古莲籽供奉给自家姑娘,还送了很大的石榴。大石榴师父没给我。
明妙朝手心里看看,还是有点不能相信,这颗黑黑的小东西,竟然藏着一千年前的莲花。
她想了想,从背包里掏出一个黄铜罐,把一条白哈达一层一层垫在罐子里,然后把古莲籽放进去,封好盖子。
你要干什么?
桑青,我要许一个愿。这颗古莲籽等了一千年,你把它送给我,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一直想要的东西,就来带走它,种下它,让它开花。
桑青接过她手中的铜罐,轻轻敲击:你想要什么?
她回答他:勇气。
他不说话了。
你呢,桑青,你想要什么?
他想了想:自由。
她有点惊讶,他看起来一直自由自在。
在唐蕃古道上,他们埋下铜罐。明妙仰头大笑:桑青,我们谁先勇敢,谁先自由,谁就先来勒巴沟,带走这颗古莲籽,我和你,凭此相认。
猎猎风中,他们郑重地勾了勾手指。
他们的相遇很偶然。
桑青从小与众不同,他关心尘世,期望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可是他无法以这种方式对待子梅。子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难以抵达的高山之上,骨瘦如柴的马匹啃噬着高山栎树的叶子,没有电,没有公路,黑暗令一切都倍显神秘。古老史诗《格萨尔王》被一代代人讲述。人们接受贫穷、疾病和死亡,对任何客观的事物都缺乏兴趣,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知道世界,而是知道自己。
童年时代,桑青要在大雨过后上山,在高山栎覆盖的地方寻找松茸,这个弯腰盯着地面的动作,让他充满了挫败感。十九岁,桑青迫切地想要离开赋予他生命的地方,年轻人只想用整个胸膛去拥抱马路和高楼,用手臂紧紧抱住穿西装和裙子的文明。
因为有一个辽阔的未来更值得追逐,他不喜欢寺庙和神的安排。
大学毕业后,桑青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谋生:公务员、小贩、警察、舞蹈老师、临时演员、货车司机、小白脸儿……在结古镇遇到明妙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摄影师。
明妙不太相信,但范猫文说:桑青是最棒的摄影师。
美国老头的评价总是充满感情,让人半信半疑。
范猫文和桑青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天发生了日全食。
地球上发生日全食的延续时间不会超过7分31秒,日环食的最长时间是12分24秒。有一位法国的天文学家,他是个天才,为了延长观测日全食的时间,天才乘坐超音速飞机追赶月亮,他看到的日全食足足有74分钟。
日蚀发生的短短几分钟,地球人都像吸血鬼,望着天空,抬起手臂遮挡阳光。桑青找了一个地铁口,拍摄人们夸张的表情。
在镜头里,他注意到一个美国老头,他举起的手臂上纹着九只猫。
老头走过来,做自我介绍:你好,我是范猫文。这时候,范猫文刚刚娶了第二任妻子,一个爱尔兰女人。夫妻俩一起为自然基金项目服务,保护濒危的猫科动物。桑青会讲汉语、藏语和英语,没有高原反应,还会开车和拍照片,这简直让范猫文欣喜若狂。
美国老头紧紧拥抱桑青:天哪,你是神派来帮助我的。
两人找了个又小又冷的咖啡馆坐下来,交谈了很久,桑青终于听懂了,为了保护一种生活在中国的特殊山猫,最近十年里,这个美国老头多次前往中国的高海拔地区,还取了这个古怪的中文名字:范猫文。他每年都在左臂上纹一只猫形图案,他最着名的演讲里有一句话:我甚至愿意和一头成年母山猫睡觉,哪怕被一头体重超过两百斤的美丽山猫压死,也不能像虫子一样恶心,死于肥胖和一张毫无感情的床上。
范猫文睁大天真的蓝灰色眼睛,卷起衣袖,当众露出他的左臂,皮肤毛孔粗大,被太阳灼伤过,上面纹着九只猫,露出九种青黑色表情。
桑青加入了范猫文的组织,他们一起在中国的大山里流浪,跟踪野生山猫。
工作很辛苦,赚钱并不多,好在时间自由。桑青常常干点古怪的事情,他一直很会赚钱,也一直很穷,这让他快乐。
自然基金组织在上海开会。
桑青展示了一组野生山猫照片,这种狡猾而美丽的动物,生活在中国四川和青海的寒冷高山之上,它们喜欢独居,善于忍耐饥饿。照片的确很棒,给桑青所在的动物保护组织争取到一笔不小的资助。范猫文高兴得像个疯子,他们去上海最高的楼顶酒吧庆祝,跳舞吹口哨,喝了十几种酒。酒醉之后,范猫文变得多愁善感,鼻头红亮,脸上沾满了来自地中海的盐粒。
桑青,我们为你干杯。
一群人哄笑着,桑青站得很高,像个英雄。子梅高山上熊熊燃烧的篝火,篝火边英勇的男子,在他身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明亮的音乐响起,范猫文抱着他的爱尔兰女人跳起大河之舞。
桑青起身去洗手间,推开门,一个女人站在里面。她把鞋子踢到一边,面对着冷冰冰的大镜子,她需要照一照自己。她爱自己这张脸,乌云般浓密的头发,高傲的鼻子,大胆的棕色眼睛,嘴唇很厚很热。她很得意,看看这个美人,那么生动,那么野蛮,她的美乍一看会让人吓一跳。她想要谁就可以得到他,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如果这世上还有比她更厉害的,只可能是闪电。
她晃动腰肢,对镜子里的人说:我多么值得爱啊。
是的,你谁也不必羡慕,你迷人极了。桑青在她背后说。
她霍地转过身,像是要扑过去咬他。他很不错,年轻,俊朗,带着点儿懒洋洋的神情。
你是谁?
我叫桑青,你想和我一起离开小便池吗?外面有很多人在跳舞。
不,我还不想走。
可她已经穿好了鞋子,跟着他走出去。
桑青揽住她的腰,她显然喝了不少,汗津津的,缠绕他,音乐很响。
这么多人,他们跳舞,喝酒,当着我的面恋爱和幸福,这真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故意气我,他们是要谋杀我!她擦了擦脖子里的汗,怒气冲冲地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分,我们十点钟上床,你觉得怎样?
桑青带着有趣的神情看着她。黄凉若——他差一点就没记住她的名字——她有混血特征,看不出年纪,她试图征服他,甚至都不想费点力气试探,她很有魅力。
他们走向一条小路,桑青把凉若揽在怀里,几只流浪猫悄无声息地看着他们,街道转角处有一间小吃店还亮着灯,老板娘坐在桌边打瞌睡。他们又穿过几条小街,就到了旅馆。旅馆外面的小花园静悄悄的,总有一些人醒着,可是在这张床上,除了他和她之外再也没有别人存在,他们至少在床上呆了二十个小时。
凉若让桑青体验到深深的诱惑,他会背叛这个有着奇异美貌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