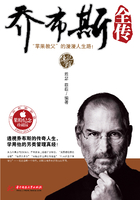接近年末,明妙在海滨城市采访,工作顺利完成,她滞留了两天,和真年约好来这里相见,一起度过平安夜。他们探望当地朋友,去教堂听唱诗,泡在巨大的浴缸里观看满潮,带着一瓶香槟去海边,等待焰火表演——今年担任焰火设计的是一位东京的女设计师,她说,焰火表演是一夜情。漆黑夜空中,火焰盛大开放,又笔直地坠落海面。心里没有爱的人不要看,容易感受到幻灭;心里没有怕的人也不要看,容易受引诱堕落。
从海滩返回,他们手牵手走过点亮银灯的树下,明妙攥着一粒小小的金橘,滋味非常甜蜜。真年,我从来没想到金橘这么甜蜜。
她朝着月亮奔跑,表盘上的指针哒哒倒转,似乎回转到她的十九岁。一个在月亮里放飞蓝鲤鱼风筝的女孩子,几乎是真年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她跟了他五年,什么都没有,不爱哭,不抱怨,不怀疑,在他手指上吃一粒糖果就欢天喜地。真年怔怔地想起来,叫了一声“明妙”,竟然哽住了。
她遥遥转过身,嘴角的小纹路非常甜美:我在这里呢。
他摆摆手,好半天才说:我买枝花给你。
卖花的女孩子很年轻,扁扁的脸,手很小。
明妙喜欢白色香花,真年偏偏挑了最俗艳的红玫瑰送她。她皱着眉毛,轻轻笑,拣出一枝玫瑰花苞,放在他嘴唇上,说你亲它一下,这朵花就是你的,世界上那么多玫瑰,只有这一朵是你的花。
真年果然将嘴唇凑过去,吻了一下玫瑰花。
明妙笑着,手指穿过他的头发。真年合起手掌,将她的指头一根一根摆放好,包在手心里,然后单膝跪下:明妙,我们留在这里吧,不回去了。
她竖起耳朵,有点迷惑,转头看了一眼卖花姑娘。
真年跪着不动:明妙,答应我不回去了,留在这里,只有我和你。
她愣了一会儿,抱着满怀红玫瑰,走到卖花姑娘面前,问她:你喜欢这花么?
扁扁脸的女孩子躲了一下,不作声。
这些花都送给你。
她简直要无法无天,将玫瑰一古脑堆在卖花姑娘脚上,拂落衣襟上的小刺,返回真年身边。
她手里空空的,一无所有,再也没有人能比一个一无所有的姑娘更平静了。
真年,你让我在这里,我就会在这里,我喜欢你啊。
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真年嘴唇翕动,发不出半点儿声音,那些字,被他一个一个吃了下去。
冬天的海灰蒙蒙的,一点儿也不浪漫,它让人走投无路。
可是真年已经鼓足了勇气。第二天早晨,他请当地朋友帮忙,租下一套靠海的公寓。付掉租金,他安装灯具,打扫厨房,和明妙一起去集市上买东西,买了好多食物,雇用几辆三轮车拉回来。明妙坐在一袋米上,惊奇地说:可以吃一百年了。晚上,真年把她抱在怀里,不允许身体间出现一丝一毫的空隙,像一个病人,患上了皮肤饥渴症,病得那么重。
他想起自己年少时的梦想,热爱约翰·列侬,想成为另一个人。
他看过列侬的全部资料。在曼哈顿,达科塔公寓大楼前的人行道上,约翰·列侬被刺杀,他死了。最后一次接受《花花公子》的访问时,列侬说:我已经四十岁了,他们说人生始于四十,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兴奋地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个冬天的海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都不知道。
明妙在他的怀里蜷起手脚,说我感谢这一大袋米,我要和你一起吃它,怎么吃也吃不完。
真年叫着她:明妙,我已经过了四十岁,我差一点就成功地忘掉了约翰·列侬,忘掉了从未实现的心愿。是你叫醒了我,叫醒了一个装睡的人。他更紧地拥抱她:我心里是有愿望的,我要实践它,从前种种一笔勾销,我和你从头来过。
明妙光溜溜地走下床,拿起一只玻璃杯,喝光杯中的水,然后将杯子抛向空中,抛得很高,它无限透明地摔下来,啪的一声,粉身碎骨。
她说,碎碎平安。
勇敢者只需要面对,因为逃避是没有用的。
她知道,他也知道,都忍住不说,是心里有怕。可你怕什么,它就一定会来,你躲麻烦,麻烦就越来越强悍。那些刻意被抛弃的东西不会自动消失,它山呼海啸,正酝酿着惊人的力量。
真年的手机嗡嗡响,他不接。到了半夜,以为明妙睡着了,他躲进厕所里,一条一条看电话记录。他渐渐暴躁,一天一天地无话可说。他们懒得出门,很少吃东西,也感觉不到饿,两个人都精疲力竭,只有身体是存在的,所以尽量做爱,不做爱也尽量抱着,只是身体的接触不再甜美,变得粗糙而暴戾,床单上混合了各种液体的痕迹,皱成一团,他们像是被那张床单生出来的。
她没办法推开他,只觉得痛,要一寸寸地被碾作尘土。
真年低吼一声,喷薄而出,血管一条一条崩裂。明妙从未见过他如此焦虑,仿佛一把刀直接刺进眼睛,他再也看不见她。
明妙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哭泣,大颗透明的泪水迅疾滑落,头发粘做一团。
夜晚过得很快,可它非常难熬。
天气预报说最近会有一场雷雨。真年喝了小半瓶烈酒,昏昏睡去。明妙坐在地板上,用一条绿色的苏格兰披肩裹住自己,脑子里一片混乱。海水在远处涌动,房间窗帘低垂,除了真年的鼻息声,听不到别的。
明妙俯身看着他。这张脸不年轻了,她曾经无数次地看着他,他们总是抱着睡,说话的时候看着彼此的眼睛,她永远美,他也永远只有二十岁。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她觉得自己瞎了,他也是,两个盲目的人,根本看不见一段关系的真相。爱到这一天,她已经没力气了,不知道还爱不爱,心里的柔情还在,可这柔情很坏,让她不再爱自己,也对他很失望,而他,恐怕是早就萌生怨恨了。
她蜷起身体,像一只萎缩的虫子,冰冷的手团团抱着更冰冷的脚。他会松开我的手吗,他会放弃我吗,他在畏缩吗?一想到畏缩,明妙觉得厌恶,这好脏。
真年喝剩下的半瓶白酒丢在地上,她拿起来,灌下一大口,真难喝。又喝一口,肚子里着火一样。她晃晃瓶子,把剩下的酒浇在窗帘上——一层绡白纱帘,还有一层厚的松绿色布帘。明妙找到打火机,啪地按下去,火苗蹿出来,烧着了窗帘。
她歪歪斜斜地笑起来:这是我的领地,我摔碎瓷器,我焚烧一切,你将如何待我?
火苗吱吱尖叫,白纱帘瞬间烧起来,灰烬翻飞,明妙感到吃惊:没有在深夜放过火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她长发竖立,好像要被火焰一根一根吸走,烟雾升腾,她一动不动,呛出满眼泪光,咳嗽着。
火光一冲而起,撞到天花板,又掉头从天花板上烧下来。
真年一下子惊醒,他直挺挺坐起来,瞳孔放大,映照出瞬间炸裂的玻璃,那景象可怕极了:明妙端坐在火焰之中,像个恶魔,玻璃随黑烟飞溅,尖锐地崩裂开。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混乱极了。真年打开了灭火器,用一盆一盆冷水泼向窗帘,泼向明妙,明妙又踢又打,她尖叫、挣扎,被裹在一条湿透的棉被里,五花大绑,像一个恶灵附体的粽子。
房间里到处都是烧焦的气息,冷风强劲地灌进来,他们累坏了,再也难以支撑,分头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明妙被自己的咳嗽弄醒,嗓子里有烟雾颗粒。她披头散发,努力爬到真年身边。手脚捆得太紧,她在地上扭动,像一条蛇,一直爬到床边,努力支起半个身子,把头埋在他的肩膀底下——太冷了。
真年微微颤抖,睁开眼睛,在他的眼睛里,明妙看见了自己。
她轻声叫他:真年。她绽开一个灿烂笑容:我好饿。
他颤抖得越发厉害,用掌心包住她的脸,哽咽难言。
从海边返回北方。
北方的冬天端庄朴素,护城河河水透明,黑色小鱼自由穿梭。
在火车上,他们没有谈起海边的大火,没有谈起初次见面的情形,也没有谈起未来,说了说天气、音乐,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打开公寓的门,真年走了,明妙放下行李,慢慢脱掉袜子,赤着脚,站在地板上不动。房间保持着她离开时的原样:木头桌子,两条铜鱼纸镇,架子上堆满书籍,吃了一半的山楂片,这些东西好像都在沉睡——睡着的东西是失望的,它们活够了,再也不想存活下去。阳光照在明妙的头发上,远处有人吹口琴,但她知道什么是无法挽回的失落。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一切欲望都消失了。
明妙犹犹豫豫走了几步,爱情和亲人距离很远,她渐渐感到睡意蒙眬,一个清醒的人多么不容易活,需要很多力量,很多骄傲,或者很多迟钝,才能相信人的行动是有价值的,相信人生中还有不可摧毁的信心。她躺在床上,直挺挺地,有点儿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
到了下午,真年来了,他两颊凹陷,眼睛混浊。
他们对坐在床沿上,眼望着彼此沉沦。
她心里想:他离我真远啊。
他想的一样:真远啊。
即便是阴阳相隔,两个人也不能离得再远了。
他们束手无策,可他们是恋人,这真让人绝望。
真年,抱我到窗前,我要看一眼太阳落山。
她伸出手臂,缠绕住他的脖子。
这个动作是属于他的。她熟悉他肩膀的线条、头发上的味儿。这些年,她努力按照他的愿望成长,小女孩长大了,朝着他的方向奔跑,一心一意想让他喜欢。现在她只觉得累,累把人变得又干瘪又小,像一具塞满香料的木乃伊。更让人心酸的是,当所有热忱消逝,你曾经热爱的人还在原地。
明妙轻轻贴着他的肩膀,不能再回忆。
我会不断地想你。她闭上眼睛,用尽力气说:我恨你。
他打了个冷战,脸色焦枯——她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明妙,你爱我吧,再试一试,我们还有时间。
她点点头:知道了。
不怨恨也不怜悯。
时间嘀嗒前行,今天改变不了的东西,以后也不会改变了。
这是现实,令人难以接受。
几年前,在一个小酒吧里,真年送她一枚红宝石戒指。戒指有点大,明妙戴在食指上,让它旋转,石头清澈顽固,闪闪发光,在透明中隐藏着难以被征服的性格。明妙拿起一个空啤酒瓶,把戒指丢进去,晃动它,喀拉拉响,那奇妙的声音逗得两人咯咯笑。回家的时候,明妙找不到那个啤酒瓶了。弄丢了戒指,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脸红红的,看起来有点可怜。可他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这让他显得性感无比。
明妙偷偷学习他的口气,直到今天,她终于可以点点头,说一声:知道了。
真年,祝福我们永不再见,因为我这么难以离开你。
她心里这么想,嘴里说的是:知道了。
明妙,再试试吧,会有办法的。
她转动眼睛,忽然微笑起来:真年,我们来玩捉迷藏,你从一数到十,来找我,找到了就答应你。
他有点高兴了,她是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子呀,众目睽睽中,裸露出洁净的身体,径直走出门外,丝毫不感到羞耻,因为反抗的力量那么强。
明妙,你乖啊。
他呼出一口气,轻松地从一数到十。并不背转身,甚至没有闭上眼睛,每念一个数字,他就逼近一步,直到将她顶在一堵墙上。他抱紧她,手伸进她的衣服里,这迷人的身体,隐藏着一捧水,一朵花,一个兔子的秘密。
明妙,我找到你了,你再也不能从我眼前消失。
他进入她,再一次感受到自己肉体的坚实。
他浑身战栗,确信这快感可以令人获得重生。
空中暮云沉浮,花园里的玉兰树影影绰绰。这是一个陌生的冬夜,到处都是芳香,嫉妒之香,离别之香。她小小的声音,为他唱了一整夜歌,真年沉沉睡去,犹如少年,天真并残忍,听不见她的声音。
黎明时分,第一束光线在他脸上跳跃,真年翻个身,慢慢睁开眼睛:明妙,早安。
她冲他微笑,嗓子已经完全嘶哑,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眼中有泪水悄然滴落,淡如朝露。
一周后,明妙不辞而别。
她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告别父母,停掉手机号码,离开这座城。
临走前,她穿上那条紫色裙子,独自在地板上旋转,那动人的颜色,是彩虹最顶端位置的紫,让她看一眼就要掉眼泪。明妙找出一把剪刀,将裙子剪成千万碎片,用大头钉固定好。
当真年最后一次进入这公寓,只看见幕天席地的紫色蝴蝶,他一下子被攫住,呼吸困难。
白床单上,明妙写下一行字:生当如蝶,间或停憩,勿忘蹁跹。
她离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