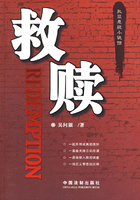他们在一起七年。
深爱过,猜忌过,委屈过,放弃过。
明妙后来说:那时候我对感情一无所知。她在街上捡到一个座钟壳,不知谁丢掉的,黑色,笨头笨脑,没有指针,她当宝贝一样摆在书架正中,座钟既不显示过去,也没有将来,明妙说:这正适合我。
真年毫不掩饰对她的迷恋。他送她各种各样的礼物,告诉她他所知道的一切,出差把她带在身边,会议中途溜回房间,顺路买一支妩媚的口红。她用口红在浴室玻璃上写:原来你也在这里。那就微笑吧,发呆吧,吃粒糖果相爱吧,这样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她蒙上他的眼睛,在他脚心写字,写了左脚,再写右脚,强迫他在床单上用力跳跳跳。他摘下蒙住眼睛的丝巾,床单上一片字迹:左脚及时,右脚行乐,满床及时行乐。
他们一起旅行。她爱破的车、破的路,暗夜里颠沛流离,站在湖水边看了一阵子雨。据说湖心岛上有天鹅,种满梅树和茶花。她凝望远处,什么也看不见,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觉得时间随时会在大雾中失踪。
她握着小小的拳头,举起来。
你看,我的心脏是这么大。她把拳头塞进他手心,轻轻笑,说,真年,我要和你相依为命。
他常常在清晨去找她。明妙还没睡醒,蜷缩成一团,手脚慵懒地散在床上。他把手伸进去,抚摩她的背,喜欢她熟睡的样子,像躺在草丛中的赤裸小兽。
她呼吸微乱,仍然赖皮装睡,真年拿起一支毛笔,蘸着清水,在她背上写字。
她忍不住,在枕上支起脑袋,问他:写的是什么?
真年不慌不忙地说:有一篇小说《大淖记事》,讲乱世里,一对相爱的男女被迫害,男的被打得昏迷,有人透露个偏方,说灌尿碱汤能苏醒。小说里最好的一句情话,我还记得,给你写在背上。
明妙只觉得他写了一片,凉飕飕的,好痒痒,忍不住要笑:
是什么情话?
真年缓缓念给她听: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一碗尿碱汤?明妙小声叫了一下,跟着他再念一遍: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她不笑了,一行眼泪直直地掉下来,真年愣了一下,眼眶也红了。
明妙,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听话。
好的,我听你的话。你让我有多好就有多好,你让我有多远就有多远。要是你再也不来,我也绝不找你。要是你又回来找我,我得想一想,然后继续答应和你好。
真年紧紧抱着她。
明妙,你向我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你的世界,你一直在那儿,可它不属于我,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想要另一个世界,现在我闯进来,再也回不去了。
那你就待在这儿,哪儿也别去,我要你。
明妙,我想敞开心给你看,这样你会更明白我。如果放弃了你,我再也不会有重新来过的决心,更糟糕的是,我设想过放弃你,一想到你要跟别的什么小伙子走了,你会爱上他,不管那爱有多少,我都难以接受。
明妙,我不允许你离开我。
明妙指指自己的心口,哽住了。不是因为难过,她拿自己没办法,也拿他没办法。
关于他们的消息渐渐传了出去。
真年倒也泰然自若,他处事谨慎,性格中有圆滑的部分,总希望别人来促成他做决定,那样就可以不必负责。可是一旦无法回头,他也决不肯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愿。感情是需要寄托的,有的人终其一生咬紧牙关,也只是坚持了一个错误,同样的,改正一个错误也要咬紧牙关。
他问她:命运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心说:我要做。理智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最终,心屈服了,这是最悲惨的命运,因为心会牢牢记住一个人的渴望,记到病,记到死,记到化为灰烬。
为自己行动,那几乎是唯一不会做错的事情。
明妙拍着一只氢气球,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并不看他,他在自问自答。
这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她承受着更大的反对。
有人去跟胡老师说:那个李明妙,我早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了,只是没讲过。
行啦行啦,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胡老师毛躁躁地打断这些话,转身就走。
姑娘,你值得吗?
明妙最后一次去电台时,胡老师这样问她。
我没想那么多。她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直在等待有意思的人,然后真年出现了,他一点儿也不像我想的那样,可我爱上他了,后来我下决心不爱他,做不到,感情的力量好大,比决心还大。
胡老师拉长的脸上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她把一个橘子重重地塞给明妙,转身就走。
明妙不敢叫她,也没有追上去。她知道胡老师在赌气,那么粗暴地把橘子塞进她手心——一个非常漂亮的橘子,那芬芳的气息让她掉下了眼泪。
姑娘,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这么笨?
她不发一言。在关于感情的文字中,李明妙成了一个微小的错别字,折磨着所有正常的句子,这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悲凉尖锐的命运。
也许真年有过一点点后悔:明妙,你是一个错误。
我不在乎对错,你也不是负责判断对错的红墨水。
你太年轻,不知道前面有多少困难。
真年,假如我出一场车祸,毫无痛苦地死去,困难就结束了吧。
他倒抽一口冷气,堵住她的嘴,再也不敢放开她的手。
他们之间的对话:明妙,你会忘了我吗?
会的,每天。
我该什么时候来看你?
是的,昨天。
这是不合理的,他们预先设计,患得患失,左右权衡,事情还是发生了。
真年的手指缓慢地、充满感情地抚摸着她的脖颈:明妙。
她转过身,看着他。他们拥抱在一起,亲吻,仿佛这是不能取消的。他分开她的双腿,热切地索取她:明妙,让我回家,我要回家。此时正是黑夜中最漆黑的时刻,他瞳孔放大,汗水滴落,激越之声不可遏制;她长发飞舞,承受他放肆的力量,不留一丝一毫余地。
他沉重叹息:明妙,你是阿修罗种下的黑色花朵,罪孽深重。
我们一同前往的,也许正是阿修罗之城,那里花从树落,城从天降,城池次第毁灭,激情却无法磨灭。
毕业后,明妙顺利进入一家报社工作,负责人物采访,租住在报社附近的老式公寓里。
她天性里有警觉的部分,与人面对面的时候,相比他们说出来的,她更擅长捕捉他们未曾说出的东西。别人扭头不看的,她坚定凝视;别人一笔带过的,她抽丝剥茧。与其说这是专业训练的结果,不如说是某种天赋。
她偏爱生活的复杂性,采访的对象很广泛:哗众取宠的演员,酒徒,过气的功夫之王,捡垃圾者,获得巨大荣誉的商人,科学家,易装癖女郎。她写大多数人活在偏见里而不自觉,写一个人是多么不情愿地在作恶,写人们所迷恋事物的不可靠。在她笔下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唯一的真理,每个人都值得同情。
她热爱这工作,唯一令人疲倦之处,就是必须与某种恶劈面相逢。她睡眠不好,无法抵抗感冒,害怕闪电,长时间站在浴室里,让热水从消瘦的身体上哗哗淌过,头脑中的累,在脸上显现。
真年劝她放弃一部分压力:明妙,我可以照顾你,你不需要和尘世的欢愉对立。你那么美,没有人舍得对你不好。
她走去给榕树浇水,背对他站立:真年,这世上无人舍得对我不好,可我偏偏得不到我要的好。
她微微仰着头,如同皇冠顶部的明珠。她此刻的表情让真年无法了解。
难道她那内在的高贵不正是我调教出来的?她十九岁,衣袜整洁,在我怀里做梦,黑暗中寻找我的手,冰凉的脸颊贴着我的手心。她越长大,越有光芒,可她整个人哪一样不是我的杰作?她什么时候悄悄开始了改变?她越长大,越是让我意想不到。
明妙,你要什么?
我要你爱我。
那你已经做到了,你可以再要点别的。
她转过身,阳光透过细碎叶片洒在她脸上,金子般闪耀。
真年,我要的谁也给不了。一个中国画家要画一只老虎,他穷尽一生,最后,老虎从画布上走下来,吃掉了画家——这是我听过的最完美的故事。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要有谁也拿不走的东西,即便被它吃掉,也是我甘愿的。
他捉住她的手腕,吻她,威胁她:明妙,你的嘴唇这样甜美,不可以杀气腾腾。
她喘不过气,身体一点一点软了,他却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很快地,由于角度独特,言之有物,明妙所采写的稿件获得了一些好评,收入增加,时间也更加自由,每周固定参加部门会议,自行安排采访,按时交稿。除此之外,她并不与人亲近,所有的人都觉得明妙骄傲,实际上她十分孤独,所以才不合群。她没有圈子,没有安全感,经常独自坐在靠窗的角落里,看着大楼前三棵美丽的雪松,鸽子从空中掠过,她似乎并不在这里。
去美术馆看画展,明妙被弗里达迷住。
一个墨西哥女画家,生命中有过两次大的灾难,一次是车祸,另一次是遇上她的丈夫。因为车祸,她接受过两百次手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她喜欢喝龙舌兰酒,喜欢举办狂欢宴会,在宴会上,她说脏话,唱黄色歌曲,使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深感震惊。她所到之处,人们都被她的美貌征服。她勾引她看上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她的丈夫里维拉也是如此,他们深爱对方,却彼此不忠,过着互相伤害的生活。她不停地画着自己,永远有一种挑衅的表情,自画像里的女人眉毛凶狠,在眉心里连结成“一”字。她不在乎死亡,她说:但愿沉睡不醒,但愿永不再来。
照镜子的时候,明妙不再喜欢自己的脸。
真年,我宁愿长出一对弗里达那样的眉毛,难道我不是这样么?
他像往常一样哄她:明妙乖,你是我的宝贝。
她拿起一根棒球棍,慢慢举起来,猛然砸向镜子,玻璃哗啦碎了一地。
她盯着他:真年,我恨不得挖出这颗心给你看看。它坚毅,敢于受苦,它不是小乖,做个乞丐或者疯婆子都绰绰有余,它连一丝一毫的甜蜜都没有。
他们不欢而散。
真年察觉到危险,他明白这样持续下去,不仅对明妙不公平,也会影响到自己。他无法割舍感情,又在内心深处拼命找借口逃避,他甚至想过:反正总有一天会闹起来,索性和她一起私奔吧,最后又随波逐流,决定让时间来裁定一切。
白天,在一个破酒吧,他们喝了一杯很烈的伏特加。
真年教明妙跳探戈。在阿根廷,生活再艰难,穷人们也会喝着酒跳探戈,人生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欢乐。她眼神清澈,跟随他的脚步,如同他的影子。
他把她抱在怀里,让她坐在腿上,甜蜜地亲吻自己。这样就足够了,她坐在他腿上,像一支鹅毛笔,一个这么轻的女人,需要一只手的把握,才能写出字迹。的确不用担忧什么,他可以主宰她,这样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事儿了。
他完全没想到,明妙会忽然推开他。
她不允许他靠近,贴着墙壁,从手指到脚尖都在发抖,就那么抖了一会儿,她忽然抓住墙纸的贴缝,用力撕开它,力气那么大,一条伤口从天花板裂到地面,惨不忍睹,裸露出里面不一样的内容。
真年,我要你尊重我。你看清楚这里面,我不是你的影子,不是你的小乖。
他被她强烈的反抗所震动,说不出话来。
她二十四岁,他四十六岁,有过一次私奔。
回想起来是非常偶然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