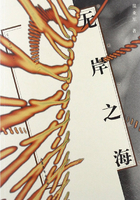杰姆逊的问话开始了:“瑞秋小姐,只有你和女仆在家的那个晚上,你怎么看待东厢房那边出现的人影?”
“那是女人。”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的女佣却一口咬定那是个男人。”
“她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她吓得不敢睁眼,这是她的一贯做派。”我解释道。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第二次闯进屋子的人可能也是个女的,而且她跟在走廊上出现的人影是同一个人。”
“我认为那一次是个男人。”我正在回答问题时,忽然想起那颗珍珠袖扣。
“好了,我们总算抓住问题的实质了。你有什么理由吗?”他咧嘴一笑,问道。
见我面露犹豫之色,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需要声明一点,假如你有证据能证明第一次的午夜造访者是小阿姆斯特朗先生,次日夜晚他又第二次擅自闯入的话,请务必如实相告。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想象去判断案情。想想看,如果把铁棒弄到地上,还在楼梯里留上划痕的人是个女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到,第二天她还会再来,并且在螺旋楼梯那边看到了小阿姆斯特朗先生,由于受到惊吓,或者是别的什么状况,就开枪射击了。”
“闯入者是个男人。”我又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实在说不出有力的证词,我不得不将珍珠袖扣的事情跟他讲了。显然,他对此很有兴趣。
我的话音刚落,他迫切地问:“能把袖扣交给我吗?哪怕是给我看一眼也好。或者这颗扣子能给我们提供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
“这样吧,我仔细地跟你描述。”
“最好能让我亲眼看一下。”他说着,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看着我。
“哎,说起来就惹你见笑了。我原本把它放在梳妆台的盒子里,谁知,再去找的时候,居然不见了。”我尽可能用平稳的语气说道。
对于我的这番说辞,他未作任何评价。不过,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存在疑问。我按照他的要求,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袖扣的样子。就在我进行叙述的时候,他顺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明细单,并匆匆地扫了一眼。
“这上面只有一组压花袖扣、一组钻石袖扣、一组平面晚宴袖扣,上面镶有小珍珠,还有一组造型独特的袖扣,是用翡翠镶成女人头型的,唯独没有你描述的这种类型。不过,假如你的说法属实,那天晚上,小阿姆斯特朗先生很有可能一只袖子上用的是一种扣子,而另一只上面使用的是不配对的袖扣。”
我没有想过他口中所讲的可能性。假如闯入屋里的并不是死者,那前一夜进屋的人又是谁呢?
杰姆逊继续自己的谈话:“这个案件牵扯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情。那天葛奇尔德小姐说,案发当晚,她听到有人把钥匙插在锁孔里,并打开了门。与此同时,枪声也随之响起。可这正是蹊跷所在。根据我们的了解,当晚小阿姆斯特朗先生身上没带钥匙,我们在房门和地板上也没有找到钥匙。也就是说,小阿姆斯特朗先生之所以能够进屋,很有可能是屋内有人接应。”
听到这话,我忍不住插话进去:“怎么可能?杰姆逊先生,这种推测可不能随便说。现在你的矛头明显指向了葛奇尔德,你认为是这个孩子让那个先生进入屋子的。”
他微微一笑,语气友善地说:“瑞秋小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不是她做的。可是,你们两个人在讲述事实的时候,都有所保留,不肯将事实的真相和盘托出。你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说明在郁金香花床上捡到了什么;葛奇尔德小姐也不肯告诉我,她去桌球室到底拿什么东西。现在,我又得知你发现了可疑的袖扣,还企图故意隐瞒不说。事已至此,我索性直说吧。我认为,深夜造访的小阿姆斯特朗并没有被那个弄掉的高尔夫球杆吓到,他能够进屋一定是屋子里有内应。只是我还不清楚那个人是谁,会是丽蒂吗?”
我用力地搅动杯内的茶,愤愤地说:“人们常说,快乐的年轻男子充其量只能作为主事者的助手。由此可见,一个男人的幽默感与他所处的职业地位是反比例关系。”
他毫不隐讳地回答:“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有时候这种幽默感是残酷的,也是野蛮的。而对于女性,这种幽默就像被熊紧紧地拥抱过一样,身上会被抓伤,留下疼痛不已的伤痕。这两者之间,哪一个会更悲惨一些,我也说不上来。”
说着,他突然抬起头叫道:“托马斯!你怎么了,进来吧!”
满脸忧郁的托马斯站在门口,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看到他这副样子,我立马想起了那个放在小木屋里的猪皮旅行袋。他抬脚踏进屋内,站在房门旁边,他的一双眼睛盯着杰姆逊,浓密灰色的眉毛几乎快把眼睛遮住了。
“别紧张,托马斯,”杰姆逊和气地说,“叫你过来,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小阿姆斯特朗先生死去的前一天,你在俱乐部里跟山姆都聊了什么?让我想想,星期五晚上你和瑞秋小姐见的面,星期六一早,你才正式来这里工作,我没说错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托马斯突然变得轻松起来。
“先生,一点没错。老阿姆斯特朗先生带着一家人去西部度假了,就留下我跟华生太太在这里看守屋子。华生太太胆子可真不小,可能是在主屋时间久了,她一直睡在主屋。这里一直怪事连连。这些事情,我跟瑞秋小姐提过。我没胆量在主屋住,就在小木屋休息。有一天,华生太太也撑不住了,她找到我说,她自己也被那栋房子弄得神经错乱,没法在主屋待下去了,要求跟我换换。想想看,她都不敢继续住下去了,我更是不敢。最后,华生太太晚上就待在小木屋里,而我去了俱乐部,在那里另找了一份工作。”
“是什么事把华生太太吓成这样的?”
“她没有提起这个,先生。她只说自己特别害怕。不过,来见瑞秋小姐的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从俱乐部穿过山谷来到这里时,险些在谷底的小河边撞到一个男人。他背对小路站着,手里还在摆弄一个小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小电灯,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个怪东西应该是坏了,亮了一下,马上又熄灭了。我从他旁边经过时,瞥见了他的上衣和领带,尽管没有看到他的长相,可我敢肯定那个人不是阿诺·阿姆斯特朗先生,他身材比小阿姆斯特朗先生高大。另外,我从这里返回俱乐部时,看见小阿姆斯特朗先生正兴致勃勃地玩着纸牌游戏呢,他一玩起来这个,就很难停手。”
“第二天一早,你是从同一条路来这里的吗?”杰姆逊追问道,他一向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的,先生。我第二天原路返回。在前一晚上看到那个男人的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托马斯拿出那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杰姆逊手中。这位刑警将东西摊在手掌上,移动到我的视线之下。那是另一颗珍珠袖扣,跟我丢掉的正好能配成一对!
然而,杰姆逊对托马斯的问话还没有结束。
“于是,你把扣子拿给俱乐部的山姆看,询问他是否知道扣子的主人。山姆就把答案告诉了你,现在,你可以把答案说出来吗?”
“当然。山姆说,他曾在贝利先生的衬衫上看到过这种袖扣。”
“托马斯,我需要这个袖扣。好了,今天的谈话让我收获不小,时间不早了,祝你晚安!”
“你瞧,瑞秋小姐,”等托马斯缓慢地离开后,杰姆逊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说,“贝利先生的处境可不容乐观,他注定脱不了干系。假如上星期五贝利先生想见阿诺·阿姆斯特朗,而没有见着的话,当然,我这也是一种假设。第二天晚上,他看到小阿姆斯特朗擅自闯入房间,会不会执行了原来的计划,将小阿姆斯特朗杀死呢?”
“但是,杀人动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我激动地说,说话的时候几乎在发喘。
“这个动机并不难找。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贝利先生在商人银行担任出纳,他曾经险些被小阿姆斯特朗害得坐牢,从此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僵。还有一点,这两个人都在追求你的侄女。此外,贝利现在不知所踪。”
“那么,在你看来,哈尔斯帮助他逃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