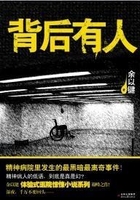向南天又把特务描述的情景前前后后想了一遍,他心里暗骂道:妈的!如果说调查科出了内奸,难道这个内奸不止一个人?
向南天挥手示意特务下去,他想了想抓起电话:“喂?科长吗?我是向南天,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
徐恩曾对上海的事怎能不知道?他前几天看了那张报纸,上面无比醒目的大标题像投枪一样扎进他的眼睛。他本想打电话给向南天的,可想了想自己与向南天对白成的死早有准备,只是没想到会提早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对向南天说道:白成死了,下面的戏就看你怎么演了。
此时徐恩曾好像对向南天的电话早有预料,于是说道:“什么事?”
“我们终究没有保住白成,但是却发现一些极不正常的事。”
“哦?”徐恩曾听罢来了兴趣:“那你说说?”
“是这样的……”向南天把自陈善生和白成的死因的怀疑说了一遍,讲了自己对钱潮和罗秋萍的怀疑,然后等着徐恩曾的回话。
“胡说八道!”徐恩曾静静地听完感到有些恼火:“二七年调查科建立伊始钱潮就来了,他是我的同乡,是被我带进来的,平时办事一丝不苟,小心谨慎,怎么可能是共党的间谍?”
“但是……”向南天想反驳,却被徐恩曾打断了。
“但是什么?但是两件事都好像有他的影子是不是?”徐恩曾说道:“照你的意思是说,陈善生能去逛窑子,他就不能去。人家上班时间外出是办公,他外出就是去向共党告密?那我问你,你看见他向共党告密了吗?”
“没有……”向南天一时有些搪塞:“不过……”
徐恩曾嘴上虽然这样为钱潮开脱,但是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刚才向南天的汇报。自己是调查科的科长,自己身边的人如果真的是共党的间谍,那么自己是责无旁贷的,更别说如果那个间谍是钱潮这个自己的机要秘书了。他知道自己此刻有些不愿意相信或者说去怀疑钱潮是间谍,因为如果钱潮是间谍这就好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委员长知道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毕竟怀疑一个人是要有证据的,而且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罢,既然自己不愿意怀疑,那就让向南天去怀疑吧!倘若查得出来还好,要是查不出来就当是给他一个教训。于是徐恩曾对向南天缓缓说道:“不过怀疑一个人是要有证据的,更何况这个人是我的机要秘书,耀宗啊!你的证据呢?”
“请科长放心,我目前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一定会找出证据给你看的!”向南天也是个善于揣摩徐恩曾心思的人,不用徐恩曾明说,他就已经明白徐恩曾这样说的意思了。
“嗯!还有,那个叫刘月茹的倒是可以仔细调查一下。因为她的职务比较低,我对这个人了解不深,当初是钱潮帮她把她的简历投给我的。”徐恩曾顿了顿又说:“现在咱们的‘绞杀计划’出了岔子,委员长又开始偏宠复兴社了,你一定要给咱们露个脸。该查就查,只要查的出来我就绝不姑息!”
“好的,我明白!”向南天听了顿时信心大增。
月4日,晚,20:45分,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
李隐峰下地走了走,觉得自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于是穿上王庸带来的衣服向马龙神父告辞:“神父,真是谢谢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一直觉得你与我们的信仰不同,真是错怪了你。”
“不不,我的孩子,你并没有错怪我。”马龙摇摇头说道:“咱们的信仰是不相同,但是咱们都有一颗仁爱的心。以前我对你们所做的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我现在知道你们是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比如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和生命,可我亲眼见到你们对一切无所畏惧。虽然我是一个法国人,但我把自己当成了你们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过份!”
“谢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李隐峰紧紧地握着马龙神父的手,望着这个满头银发的法国老头,真挚地感谢道。
李隐峰趁夜色回到了家,整个屋子里一片漆黑,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于是拔出了枪,慢慢地朝里屋走去。
鲁特正在独自抽着烟,烟头忽明忽暗地在屋子里闪着。忽听有人开门,于是赶紧踩灭烟头也拔出枪向门口走去。
“不许动!”两人靠着一面墙的两边慢慢地摸到了门口,忽然猛地闪出来拿枪对准了对方的脑门!
“天雷!”鲁特说道。
“地火!”李隐峰回答道。
两人见是虚惊一场,都不由地松了口气。鲁特见李隐峰回来就一把把他拉了进来紧张地问道:“没有人跟踪你?”
“没有啊!”李隐峰疑惑道:“怎么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又有同志被跟踪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被捕的情况,组织上提醒咱们要格外小心,提高警惕。”鲁特说罢轻轻揭开窗帘的一角,透过窗户向楼下看了看。
这里不是闹市区,此刻街道上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街灯和静静的树在路的两旁伫立着。他观察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异常就放下了窗帘。
“怎么会有人跟踪?”李隐峰问道:“白成不是被处决了吗?难道他们那边还有叛徒?”
“不一定是他们那边有叛徒,可能是咱们内部还有内奸。”鲁特在黑暗中向李隐峰说道,李隐峰虽然看不见他的神色,但听他的声音就知道此刻他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总觉得自从你来了以后就有些地方开始不对劲了。”鲁特接着说道。
“你不会是怀疑我吧?”李隐峰赶紧问道。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咱们一起出生入死,你救过我,我也救过你,如果这是苦肉计,那这样的代价也太沉重了,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李隐峰经他这么一说也开始回想自己来上海以后经历的种种。其实一个间谍被人跟踪是很不正常的,因为那再明显不过了,说明是有人怀疑你或掌握了你的身份、活动时间、甚至是你的上下线。他们抓捕你的早晚取决于对他们知道这些情报的多少。
如果对方并不急于抓你或者至你于死地,则说明他们想摸清楚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再动手。就像大家都知道的“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一样,敌我双方都很清楚这样做的好处。间谍们都受过特殊训练,一个意志坚强和信仰坚定的间谍即便被抓进去,敌人对他施以最残酷的刑罚也不会改变他的意志和信仰,就像霞姨和廖敏,所以抓与不抓就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了。
想起自己在江面上被人跟踪,在第一次与老肖接头的时候被人跟踪,而后王庸的住址之一被敌人搜查,霞姨和穆广贤被敌人抓捕……这些事件前前后后好像一根线。如果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么这根线真是放的很长很长,长的以致于大家差一点就失去了警惕性,以为处死一个白成就挽救了整个组织。
李隐峰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冷战,真是太可怕了。看样子敌人好像正在摸查组织上这些同志的活动规律和联络地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企图将整个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
但是他们对霞姨和穆广贤的那次抓捕好像不太符合这个的逻辑,因为他们并没有抓到王庸,那次抓捕好像是由于敌人太急功近利了。更幸运的是抓捕的时候王庸居然不在那里,由此惊险地躲过了一劫。倘若那次王庸被他们抓住,那后果真是……太可怕了!王庸是我党上海地下机关的二号人物,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数百条同志的联络线,这些联络线就像这些同志的生命一样。若是断了就会使大家找不到党组织。
李隐峰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向鲁特要了支烟,静静地点了起来。屋子内的气氛诡秘而宁静。两人都沉默不语,他们知道彼此的心里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个内奸到底是谁?
月6日,晚,19:45分,上海虹口公园。
李隐峰知道必须得加快策反黄宛莺的步骤了,就算策反不成,也要从她嘴里套出点有用的东西来。于是就打电话约黄宛莺晚上八点在虹口公园见面。
黄宛莺知道向南天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夸张一点地说,被他怀疑上的人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否则就是死,向南天也还是会开棺验尸来证明自己的判断。
然而自己是复兴社间谍的身份是不能暴露的,尽管同样属于国民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内部却派系林立。军阀、嫡系、黄埔圈、保定帮、调查科、复兴社、力行社……就连国民党被捕也划分出了什么“CC派”、“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这一切都是因为蒋介石对这些组织有偏有向,他信任一个组织是有限度的,并且会让另外一些组织与它互相监视,以此来保持这些组织间的平衡。这对蒋介石来讲叫做“权术”,但是下面的人就倒了霉了,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共党杀的还是被国民政府的其它派系的人杀的。
黄宛莺从大世界的后门出来,然后打了个黄包车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确定没被人跟踪后就在远处下车,走进了虹口花园。
已经立春,上海的夜晚变得不是那么冷了,李隐峰一直在上次唱歌的那个地方等她,见黄宛莺来就上前向她后面看了看问道:“这次没被人跟踪吗?”
“这些天一直有人跟踪我,但是今天被我甩掉了。”黄宛莺说道。
“到底是谁派人跟踪你?搞清楚了没有?要是有人想绑票可就麻烦了。”李隐峰故意想把黄宛莺的话套出来,尽管他知道国民党里派系争斗复杂,但他并不知道黄宛莺是复兴社的,所以他对黄宛莺被跟踪觉得有些想不通。
“暂时还没搞清楚,可能是那些帮派。”黄宛莺说完故意岔开了话题:“这两天我正好想找你陪我出来走走,没想到咱们还挺心有灵犀的,呵呵!”
“我才来上海不久,做一些木材生意,认识的朋友大都是生意场上的,所以称不上什么朋友。但是第一眼见你却觉得你挺值得交往,不为别的,就冲上次你借我看圣经。”李隐峰说道。
黄宛莺知道这个叫李枭的男子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她相信凭自己的姿色,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的,但是眼前这个人却不同。他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正气,尽管这种正气目前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的眼神和一举一动告诉自己他确实是个懂得维护别人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