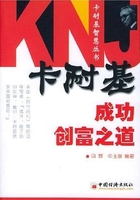这栋外有花园,内有佳人的楼的主人就是向南天,向南天的哥哥向如海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十八罗汉”之一。当年向如海在这十里洋场开办了自己的赌场和妓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此买下了这栋楼。但是他哥哥早死,所以这栋楼和他哥哥的遗产就顺理成章地归了他。
向南天与徐恩曾私交甚笃,今天的会议内容特别而且机密,所以就临时选定在他的公馆里举行。
今天到会的人级别都很高,负责会议记录的是钱潮。桌子正中放着陈善生昨晚那顶帽子,帽子上的那个弹孔显得格外显眼。
“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议程,我将这段时间的工作汇报递了上去,委座很不满意,他要是怪罪下来,大家说怎么办?都吃不了兜着走!”徐恩曾怒气冲冲地冲在座的人说道:“盯梢盯了好几天,煮熟的鸭子却让它飞了!对了,陈组长,你可真是命大啊!”
见徐恩曾和大家的目光都落在那顶帽子上,陈善生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了。
“我倒有一个建议!”向南天站起来,一边走说道:“咱们以往的工作不见成效,就是因为咱们缺乏一些投诚的共党。就像两个人猜谜语,平时他们猜咱们,咱们猜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谜底。但是如果有了一些知道谜底的人,那时咱们就用不着跟他们兜圈子了!”
“哦?耀宗的意思是?”徐恩曾见有向南天一番高论入木三分,立即投来赞赏的目光询问道。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以共治共’,将一些投诚的共党组织起来,成立专门针对共党机密的小组。并且利用比如‘青帮’、‘洪帮’、‘斧头帮’等可利用的一切外围组织,为咱们提供可疑情报,因为他们的耳目无处不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当咱们的‘先遣队’。如果能够组织一些投诚的共党的话,再加上这些外围组织,我想把他们的地下机关一网打尽是不成问题的。”向南天环视着大家说道。
“耀宗果然高见,但是……”“耀宗”是向南天的“字”,徐恩曾话到嘴边突然犹犹豫豫地,说了前半句,就将后半句咽了下去。
“但是什么?”
“但是共党惩办叛徒的手段厉害的很哪!前几次好不容易有几个投诚的,可结果怎么样?唉!还没怎么着呢,就被共党的‘红队’给暗杀了,这些无孔不入的家伙!可惜啊!”徐恩曾先是恨的咬牙切齿,然后面露难色地说道。
“科长忘了?咱们手上不是还有张‘王牌’吗?”向南天得意地想徐恩曾提醒道。
“王牌?”徐恩曾想了想,忽然恍然大悟:“对啊!你看我这脑子,这两天都给我气糊涂了。可谁来负责这个计划呢?”徐恩曾装作有难处的样子喃喃道。
“科长若不嫌弃,耀宗愿为党国效忠!”向南天挺起胸膛大声回答道。
“好!耀宗肯助我一臂之力,不愁大事不成!你明天就拟定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拜托耀宗你来负责了。”徐恩曾闻罢喜形于色地拍着向南天的肩膀称赞道。
然后他缓缓地走到窗前,突然将窗台上一盆花连根拔了出来,恶狠狠地说道:“这些无孔不入的家伙,这次我要将你们连根拔起!”
月2日,午,12:20分,上海鼎吉里6号楼内。
今天还是与往常一样,明媚的阳光通过窗户上的薄纱洒进屋子里,刚刚吃完午饭的大家都有了一些倦意,但休息了一会儿就又开始上课了。
王庸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政治保卫要点,伍豪有事所以暂时没来。屋子里的沙发和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同志,听王庸讲到重要之处时,大家都拿笔在本子上记着,生怕漏掉一个重点。
“同志们,大家用心学习是好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一群做特殊工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证据越少越好,最好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蒸发了,不复存在了,这样就能有效地隐蔽自己,监视敌人。所以我们避免留下证据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些东西装进脑子里,而不是记在本子上,大家明白了没有?”王庸见大家都在动笔,就严肃地说道。
“明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李隐峰在“契卡”接受过用大脑速记的特殊训练,所以用脑子记这些要点根本不是问题。
只要是开会或集结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人给大家把风的,这次也不例外。负责把风的人是情报员张浩,因为他年龄小,但有一身飞毛腿的功夫,上海的里弄没有他不熟悉的,据说他闭上眼睛都能在上海滩走个来回,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耗子”。
张浩站在窗前,用手轻轻撩起白色的窗帘一角向楼下监视着。外面的天气很好,路面上的人三三两两地过来过去,谁也没有注意站在路对面看报纸的那个男人,但张浩却对他特别地留意。
这个家伙看似在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一张报纸,其实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一直留意着路对面这个房子的动静,并且还时不时地用余光扫着路的那一头。这一切别人没有看到,但张浩却看了个清楚。
过了一会儿只见路的那一头来了一辆车,车子路过路边那个看报纸的男子的时候,男子在报纸下伸出五个手指头,大拇指向上挑了挑,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径自走了。
张浩大吃一惊,他虽然不明白这手势的意思,但他确定这肯定是敌人联络的暗号。伸出五个手指头表示“人全在里面,一个也不少”,大拇指向上挑是在告诉同伴“还有条大鱼在里面”。
“不好!老板,有情况!”张浩扭头就朝正在讲课的王庸喊道。
王庸脸上并没有特别吃惊的样子,相反他一言不发,很镇定地走到窗前向下望了望。楼下那车的前门开了,里面出来两个戴着鸭舌帽的黑衣人。后面的车门也跟着出来两个人,一个瘦高的洋人,一个矮胖的中国人。
“情况有变,大家跟我从后门出去!”王庸向楼下看了一眼朝大家说道。
“老板,我看了,后门也有人!”一个同志从后门跑来对王庸说道。
李隐峰见鲁特脑子一热想摸枪,按住他的手,朝王庸说道:“老板,上阁楼吧!”
想在白天从大街上突围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做无疑有极大的风险性,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就离这儿不远,要是他们倾巢出动可就麻烦了。
“好!”王庸想了想说道:“我留下来应付,你们先上去。”
“这怎么行?!”李隐峰和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吓了一跳。
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此时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
“不要慌,这个巡捕我认识,我自有办法!”王庸冷静地命令道:“小李你快带大家上去!没我的命令不许下来!没有时间了,快!”
李隐峰此时与大家一样,既然是“老板”的命令,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几个人一咬牙鱼贯上了阁楼。
王庸等大家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顶,自己整了整衣襟,不慌不忙地上前将门打开。
门外的人早已等不及了,门刚打开了一条缝就推门闯了进来。
“你们有什么事吗?”王庸平静地站在门口问道。
“少废话!让开!”两个黑衣人一把推开王庸径自闯了进去。
“王老板,你好!”后面那个高高瘦瘦的洋鬼子叫“白兰德”,是法租界在这一带的巡捕房探长。法语名字叫Bayard,白兰德是他的中国名字。王庸与他打过几次交道,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不错,所以他一见王庸就先用带着洋腔的中国话打起了招呼。旁边跟着的那个满脸谄笑的矮胖子是白兰德的“包打听”,此人叫赖有为,受过王庸不少好处。
“包打听”是旧上海特有的一种职业称谓,指的是巡捕房探长手下的那些收集各种消息的“密探”。与特务不同的是,这些探子的身份是半公开的。他们出入于上海的茶馆、酒楼、舞厅、妓院等地方,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并从信息里挑出一些有价值的进行上报。平时熟人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消息,比如政府政策、市场动向等等,都会去问或者托人去问“包打听”。
“呦,原来是白兰德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王庸回头看了一眼在屋子里乱翻的那两个黑衣人,向白兰德问道。
“哦!你不要误会,他们不是我带来的人。他们拿着搜查令给我们巡捕房,说你这里有人在搞秘密活动,要求我们帮助搜查。王老板我很抱歉,我也只是奉命行事。”白兰德说完耸了耸肩膀,眉毛向上抬了抬,嘴角向下撇了撇表示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平时做一些小生意养家糊口,都是正经的小本买卖,这些你们是知道的,是不是啊?赖探长?”王庸说罢掏出一包“哈德门”牌香烟递给那个“包打听,又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给白兰德,然后问道。
“是的是的!王老板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不是?”赖探长拿了一支香烟满脸堆笑地回答道。
楼下的房间很快搜查完了,两个黑衣人走向通往二楼的楼梯要上去搜查,王庸看了一眼,并没有阻拦。
大家在阁楼上俯身听着楼下的动静,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枪。当听到特务开始在与大家一板之隔的二楼翻箱倒柜的时候,鲁特和几个同志不由地将枪掏了出来。李隐峰见大家这个样子忙回头将手摆了摆,示意大家不要冲动。
特务将两层楼翻了个遍,但却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脸怒气地走下来,恶狠狠地向王庸问道:“那些人都哪去了?”
“什么人?二位说的话我很不明白,侬这是搞什么啊?”王庸一副不解的样子,用流利的上海话向特务们问道。
“少他妈跟我们装糊涂!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特务们骂完就抓着王庸的领子就要往外拽。
见此情景,白兰德与赖有为赶忙上去拦住,几个人一时扭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门外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声音低沉而具有威慑的力量,特务们松了手回头望去。
只见一个脸色低沉、一身正气的中年人站在门口,用锐利的目光望着大家,两个保镖似的人站在他的身后。
“呦!大老板来了,呵呵,他是我的大老板。”王庸见机说道。
“大老板?哼!你是谁?敢来管我们的事!”一个特务轻蔑地上下打量着中年人问道。
“管你们的事?你们算老几?就连警备司令部的事我们老板也照样管!”中年人还未发话,他身后的一个保镖冲着那个特务厉声喝道,然后左右开弓啪啪两下,在特务脸上连扇两记响亮的耳光!
那特务被扇得眼冒金星,一时懵了,摸着火辣辣的脸,身子向后倾着一脸疑惑地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叫“大老板”的人:“敢,敢打老子?你,你叫什么名字?!”
“问你们委员长去!娘希匹!连老子都不认识还敢在上海滩混!”中年人盯着那两个特务骂道。
两个特务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脑中不停地搜索着上海滩每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的名字:三大亨、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十八罗汉、四大家族……且不说是国外势力了,单单这些人里面的任何一个也是他们都惹不起的。再看看眼前的这个中年人,想想他刚才说的一句与委员长相似的“溪口话”,再想想他理直气壮伸手就打人的派头,真是不知道他是哪路神仙了。
“好!你……等我回去告诉我的老板!”两个特务摸着脸边回头说边蹿上了车。
“王老板,这里既然已经没有事了,我们也要走了。非常抱歉,祝你生意兴隆!”白兰德也不是傻不啦叽的法国佬,虽然不知道这个“大老板”是谁,但见状不对就带着“包打听”上了车走了。
见他们都走了,王庸才将那“大老板”请进了屋子里。这个“大老板”不是别人,正是化妆后的伍豪。
伍豪见屋子前后的敌人确实已经离去,就马上将同志们叫了出来,命令大家从后门赶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