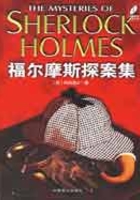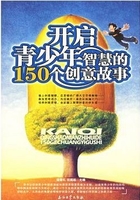老钟头将我们送到了吴教授那里,只见他们已经要整装待发了,见我们来就催促我们上车。老钟头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挥别,虽说才认识这么两天,但是我却觉得他这个人,身上固然是有十足的奸商气,心地却是极为善良的,不由地眼睛有些湿润,回头看看胖子和向茹,也跟我差不多。
上了车,吴教授挨个儿将他的几个学生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一个留着文静的剪发头的戴着眼镜的女孩叫宋碧君,那个同样戴着眼镜的文绉绉的奶油小生叫郝卫国,一听就知道是文革时期改的名字,另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瘦小的小子叫周大伟,听宋碧君他们都形象地戏称他为“小胡子”,却让我想起了《水浒传》里的‘鼓上蚤’时迁。
我看了看吴教授他们的装备,虽不多,但齐全的令我们惊讶。洛阳铲、探针、德国手铲、苏联指南针、从大到小应有尽有,大都是舶来品,我以为我和胖子去新买的“头带式”头灯就够撑头的了,最起码也要比上次那个笨重的矿工帽要好的多,没想到他们的头灯却比我们的还要小,还要精致,真货比货得扔啊,我和胖子互相吐了吐舌头。
我们先坐汽车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途中那个叫郝卫国的小子不停地跟向茹说着话,向茹却有些爱答不理的样子。
那个外号叫“跳蚤”的周大伟,两个眼睛滴溜溜乱转,一直坐在吴教授的身边,不停地拍着马屁,说的老爷子一个劲儿地乐。
宋碧君话不多,一直在看一些考古方面的书,说是准备写博士论文答辩,时不时透过火车窗子看看外面雄奇的西域景色。
列车路过嘉峪关的时候,我们都被这万里长城的最后一个关隘所吸引,几乎全列车的人都挤在窗户跟前看着。
无垠戈壁,漫漫黄沙,一座由朱元璋下令修造的雄关屹立在这夕阳西下的河西走廊上。这座雄关在这里一守就是四百多年,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沧海桑田的剧变,谁也说不清楚。我不禁想起那楼兰古国,在亘古不变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辉煌了三千八百多年,现在又该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
吴教授在一旁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我不想打搅他,就叫上胖子去两节车厢中间抽根烟。
我和胖子刚站定,旁边先来的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男子就笑着递了两只烟过来,说道:“来新疆旅游的吧?”
“呵呵,是啊!”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接过烟笑道。
“我看不像啊!”男子诡异地笑笑,浓眉下的两只眼睛朝我们盯着。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我和胖子都有些警觉。
“你看你们几个人,大包小包的,谁旅游带这么多东西,又不是搬家,哈哈!”男子朝车厢里我们的行李那边努努嘴,笑了。
好眼力!我心里暗叫道,接着问:“你有什么事吗?”见胖子在一旁对他怒目相视,我赶紧将胖子挡在了身后,生怕他乱了大谋。
“其实我没什么恶意,你们要是探险队,我倒可以帮上你们的忙。”男子也对胖子的表情有所察觉,赶紧笑着说。
“哦?你能帮我们什么忙呢?”
“不是我帮,我有工作,是搞石油勘探的。我侄子倒是能帮你们的忙,这两年刚改革开放,大大小小的探险队,考古队,都往新疆沙漠里跑,他们村里离沙漠不远,村里的人都搞起了第二职业当导游捞点外块,我侄子精通维、汉两种语言,还会点英语,接待了不少外国客人。你们要是去那里探险,就按我写的这个地址找他,说是我推荐你们去的,他肯定给你们优惠!”说罢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看了看上面的地址,确实离罗布泊很近,就装在了兜里。
但是听见他说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科考队,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那么多的人都去了,我们还去个屁啊?!我和胖子互相望了望,胖子朝我耸了耸肩,一起回到了卧铺车厢。
我将那男子说的事给吴教授说了一遍,他想了想,觉得很有必要请个向导,于是就答应了,但是答应的条件居然是从给我们的酬劳里扣这笔向导费。这老家伙说好事成之后回来就给我们每人五千块,现在居然开始抠门起来,实在令我和胖子恼火不已,但是想想他一个搞学问的老头子,又不是什么大老板,能有多少钱?再说向导费估计也没几个钱,加上向茹在旁边宽慰我俩,我和胖子心一软也就同意了,只是在暗地里骂这老家伙周扒皮一样地抠门。
到了乌鲁木齐下了火车的时候,那男子在站台上跟我们告别,走了两步又朝我们大喊:“别忘了!我叫霍耀汉,我侄子叫霍小宁,去了找他就对了!”见我们笑着点了点头,这才放心地走了。
由于那时没有从乌鲁木齐直达那里的火车,我们就从乌鲁木齐包了一辆中巴,崎岖颠簸了一天多,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总算到了若羌县的“喀尔达依”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
据司机讲这里离楼兰已经很近了,再往那边深入就是罗布泊腹地了,以前过往的商旅都对它绕道而行,连听都不想听见“罗布泊”这个名字,更别说走进去看看。
我们疲惫不堪地下了车,在当地一个村子里住了下来。
这里房子多是用古老的技术修盖的,将草木灰和上些黄土,倒上些水这么一搅和,就砌成了眼前这一栋栋低矮的黄灰色的民宅。
从张骞出使西域那时起直到,这条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古国就已经是维、汉、以及一些其它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了。
现在依旧是这样,街上三三两两的维、汉生意人还在做着日落前的最后一笔生意,卖沙瓤大西瓜的,卖吐鲁番葡萄的,卖香喷喷的烤羊肉串儿的,还在奋力地吆喝着。我被一个维吾尔老人摊上的英吉沙小刀吸引,上前挑了一把。
据说这刀子极其锋利,而且削铁如泥,老人见我将信将疑,顺手抄起旁边一截已经砍的全是豁口的生铁,拿起我这小刀就砍了上去,顿时火星四溅,每砍一下生铁上就出现一条深深的口子,我这才心满意足地交了钱,将这把刀身细而长,刀把镶嵌着各种人造宝石的刀子插进了皮套,别在了腰上。
我都不用去找胖子,就知道他在一旁的烤肉摊子上狼吞虎咽,我和向茹坐下来吃了一些,味道确实异常香辣,叫吴教授他们过来一起吃一些,却发现他们已经回到旅馆里去了。考虑到明天就深入罗布泊,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就赶紧买了一些当地维吾尔族的“馕”,就是像烤饼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放几千年都坏不了,新疆各地都出土过两千多年前的“馕”,依旧完整如初。
胖子又叫了几瓶哈萨克烈酒,准备跟我来个不醉不归,我想起明天就要向罗布泊腹地出发,喝大发了还怎么去?于是赶紧拦住了胖子,给他多要了二十串烤肉,这才算堵住了他的嘴。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按着那男子给的地址,去前面的村子找到了他的侄子霍小宁。
小男孩才十四五岁的年纪,可是说起话来就香喝了香油一样,溜须拍马,哄的大家一阵阵地大笑,看的出来,吴老爷子也非常喜欢他。
吴教授觉得东西太多,问霍小宁能不能租几匹便宜点的骆驼来?霍小宁说他没有骆驼,但可以找和他一起的老搭档才行,价钱可以帮我们讲讲,我们就同意了,在原地等着他。
我们在村口望着远处那一片苍凉的荒漠不住地赞叹,忽然我感觉背后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一个沙哑而颤抖的声音说道:“去不得啊,去不得啊!”
我和众人都吓了一跳,回头只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佝偻着背,拄着胡杨木做的拐杖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用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冲着我们。她那干瘪的脸庞,皱皱巴巴的嘴唇,银白的长长的散发,和那双布满血丝的犀利的双眼让我们觉得无比诡异。
“您刚才说什么?”吴教授先开口问道。
“去不得啊!”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就说我们去不得?”郝卫国问道。
“嘿嘿!嘿嘿!我知道,你们要去送死!”老人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这话不仅使我们莫名其妙,更怀疑她是个疯子。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郝卫国平时文绉绉的,头发梳的锃亮,现在却大概想在两个女孩儿面前想显示一下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突然上前对这老太太喊道。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见状赶忙和吴教授将他拦住,对这老太太问道:“你再说清楚一些好吗?”
“嘿嘿!它们饿了好久啦!正在咬着太阳等着你们哪!晚上可要吃个饱啊!嘿嘿……”老人语无伦次的话更让我们觉得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他却迎着炎热的漠风颤巍巍地走向了村子里。
不一会儿,霍小宁就领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维吾尔大叔来了,后面还牵了四匹高大的骆驼。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大叔叫买买提,他曾经带两个考古队深入过罗布泊,见过他们在那里搞考古工作,不过这个大叔就是汉语讲的不太好,所以才总和霍小宁做搭档的。
买买提跟我们说道:“你们跟着我走,我说去哪里就去哪里,要不然嘛我就不干了。”
我们心想我们对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不跟着你们走跟谁走?于是就没有反对。
大家一路上向他们打听着那里的情况,当我问道刚才那个村口的诡异的老人是谁的时候,霍小宁皱了皱眉头,用维语跟买买提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们:“那老太太就住在村子里,她的儿子几年前带着一个日本的科考队,一共十几个人,去了罗布泊的深处寻找楼兰古国,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以后她就变的疯疯癫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