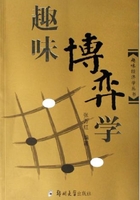从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来看,问题的实质显然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所谓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那些中国经济问题“受欧美经济影响”的说法,不过是在转嫁责任。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如此被动
达尔文说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如此被动呢?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出口,其中最有市场的是“外部环境”论。这种观点认为,欧美经济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相对而言却是健康的。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增速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欧美失火殃及了中国这尾池鱼而已。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恶化。
这种观点有其道理。外部条件对事物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一粒种子要想发芽成长,需要适合其发展的条件外因,譬如适度的温度、湿度、土壤。干旱、高温等恶劣的条件无助于种子的生根发芽。在经济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一观点无疑正确,但却不充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里阐明,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生活条件即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缺一不可。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外因更为重要,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这也解释了,在相同的条件外因下,为什么有的类人猿进化成了可以直立行走、独立思考、有思想、会劳动的人类,而有的却仍然只是半直立行走及臂行的大猩猩。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生物界,在现实的经济范畴里亦是如此。
《广场协议》为何只拖垮了日本
对于日本的衰退,日本国内主流的看法认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是美国胁迫着日元升值,美国想通过牺牲日本来解决自身的双赤问题。《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这令日本在此后近20年,经济一蹶不振。其实这种观点在中国亦大有市场,2010年9月27日《中国证券报》的一篇题为《〈广场协议〉埋祸根,日本深陷“失去的十年”》的新闻综述就很具有代表性。报道援引复旦大学冯昭奎教授的话说:“尽管日本政府阻止美元过度贬值也是为了使已有的对美投资不贬值,然而这种措施的结果是继续推动对美投资并容忍美元资产进一步贬值,这意味着日本已经陷入一种极为被动的、受制于美元的圈套。”而身居日本的中国籍作家俞天任,则更是直白地认为,日本的大泡沫和以后的大灾难,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
然而被人们刻意忽视的是,《广场协议》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国英镑也赫然在列。在这四国中,德国和日本最具有可比性,因为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很快,并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广场协议》明确规定,不仅日元,德国马克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日元兑美元到1987年底时已接近升值100%,但是并非仅有日元升值,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元升值得还更多,达到101.27%。到1988年,德国马克的升值率相比较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与《广场协议》签订时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达到70.5%。
德国马克、日元兑美元走势图(1985.01.31~1991.10.3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策略部
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还有联邦德国,其贬值幅度也非常相近。为何德国在之后的20年,不仅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倒退,反而在2008年以来的欧债危机中,成长为欧元乃至欧盟的拯救者?而真正“失落”的唯有日本一国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1985-1990年这一时期,日本的货币政策出了极大的失误。对此,时任日本政府官员的大野健一、黑田东彦在事后回忆时,都为当时的错误选择而痛苦万分。
《广岛协议》后,为了摆脱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困境,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以此来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1987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减税1万亿日元,同时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同年7月又补增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与此同时,从1986年1月起,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1987年的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却步入了高涨阶段,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机行为。日本政府在这时点上采取的政策,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方面是出现大量的剩余资金,一方面日元升值萧条,实体经济不景气,投资需求下降,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这些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一股脑地流向了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繁荣景象,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美、英、法、联邦德国等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提高了利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预备加息。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美国发生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大股灾。虽然在政府降息等手段的干预下,市场重新恢复了上涨,但美国政府却认为日本在这个时点上不应加息。欧美政府担心,市场还很脆弱,如果日本在这个时点上加息,必然会导致那些套息资金,不仅不会流回欧美,反倒会再次从欧美流入日本,从而再次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
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不愿意加息。他们所担心的是,一旦加息,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进而推高日元,减少其商品的出口,再次因日元升值而引发1986年式的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想将经济体由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变为内需型。而在当时日本财经官员甚至学界看来,要想扩大内需,其关键就在于以低利率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而正是这种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日经指数衡量的股价,从1986年1月的约13,000日元上涨到1989年末的约39,000日元,上涨了大约3倍;同期的地价也上涨了约3倍。
而反观德国,在货币升值以后,它的关注不是像日本那样朝外,而是向内。中央银行秉承了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WilhelmErhard)的思想,坚持以稳定物价为己任,没有实行超低利率和超量货币发行的政策。它排除欧洲和美国的要求,坚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没有大量进入股市和不动产。1985年德国存款利率为4.44%,1987年下降为3.20%,同期,贷款利率从9.53%下降到8.33%,下降幅度远低于日本。更重要的是,随后于1988年和1989年,德国将存款利率分别上调至3.29%和5.50%,贷款利率更是提高至9.94%。
诸如此类的反比,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对通货膨胀,那些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们经常给予的解释是,通货膨胀是由国外输入的。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曾批评的:
如果世界货币体系尚处于金本位时代,那么因为各国货币都是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某一国货币量的增长的确会造成其他国家的波动。历史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量掠夺黄金而造成整个欧洲的价格上涨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随着金本位的破产,这一解释也就站不住脚了。在阴谋论者或故意推卸责任者来看,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是符合他们的逻辑的。因为自美国取代英国之后,它就彻底变成了“邪恶帝国”——当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如此看,一些自认为弱小的国家事实上也是这样看的。随着日本陷入失落,这一观点在日本更是大有市场。
但这是事实吗?当时,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都高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却只在10%左右。当时的货币体系一直是由美国主导,《布雷顿森林协议》是美国主导建立的,而它的废除也是美国主导的,这高涨的通货膨胀与美国有必然关系。可问题在于,虽然当时英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0%,而同时期的联邦德国通货膨胀率还不到5%。难道,美国想利用手中的货币政策对付英国和日本,就没想过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当时的联邦德国?
在1975年石油危机后的五年时间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该数值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每年30%以上下降到不到5%,而联邦德国则一直维持在5%左右。倒是美国,其通货膨胀率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一年里达到了顶峰,约为12%,到1976年降低到5%,但好景不长,随着第二轮石油危机和伊朗事件的爆发,其通货膨胀率再次上扬,到1979年上升到13%以上。从这点来看,阴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外部环境的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
对决定事物发展的因素,达尔文最后的结论是:“外因条件与生物本身内因相比,仅居次要地位。”由此,我们可见,一国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何尝不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呢?!真正令日本为之失落20年的,主要还不在于由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而在于其自身错误的应对。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全力支持出口的那些政策
有趣的“出口主导型”之争
除外部因素论之外,主流经济学界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亦认同问题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上,只是他们认为不是出口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投资过度了。
2009年初,瑞银证券公司(UBS)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在他撰写的一份报告里就认为,中国不应被看作“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必过于夸大,中国并不必对世界需求下降过于恐惧。
他说,出口占GDP的比这一指标具有误导作用,它甚至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统计指标。与外界常有的印象不同,中国的出口部门虽然规模可观,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仍然只扮演一个比较“中庸”的角色,比亚洲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弱。尽管出口额在飞速增加,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缓慢,他认为时间序列的比较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他进而分析被广泛援引作为证据的中国出口占GDP比率这一数值。这个许多人会脱口道出的简单、流行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海关数据除以中国的GDP。人们能够看到出口占GDP的比例在过去急剧上升。
由此推导出的一般结论将是:一,出口已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1/3;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高。如果这两点成立的话,很显然,当出口竞争力减弱、全球对中国产品需求趋降时,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急剧萎缩的风险。
但是,以上结论是误导性的。2006年,马来西亚的出口占GDP达到104%。显然,不能将此理解为该国的出口部门比整个经济都大。对于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来说,情形就更“糟”了,这个比例超过200%。对于不知情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显得不可理解,一个国家(地区)的出口为何会“超过”其GDP呢?安德森指出,这个指标是拿两个不具可比性的数据来做比较:出口被定义为总的“流水”,而GDP是从增值的意义上而言的。如果拿一个公司来打比方,出口类似于销售额,而GDP则类似于利润。
瑞银证券公司的估算表明,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价值含量为45%。也就是说,出口总价值的55%代表了进口原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出口行业本来就以劳动密集为优势,以组装为特色,国内含量仅占GDP的14%~16%。安德森总结,“这是我们对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佳测算”。
有趣的是,40多年前,同样的争论发生在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学界曾就日本是不是一个出口主导型的国家争论不休。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凯维斯(RichardCaves)在他的论文《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和新经济史》里指出,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出口为主导的话,那么就必须有能带来经济利益及使实际收入增加的外部因素,并且还必须能把它和由于增加人力及物力的投资而出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以明确地区别。
根据凯维斯的说法,区别内外部作用因素的简单试验就是看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如果成正比,那么作用因素就在外部;如果成反比,作用因素就在于国内供给的变化。罗林斯“库劳茨把凯维斯的实验用于日本,发现1961年出口价格指数为92,而1968年尽管出口量大幅度地增长,达到了232%,但是出口价格指数却仍然维持在92.9,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根据这一结果,罗林斯“库劳茨认定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不是以出口为主导的。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事实上安德森的分析工具和模型,与罗林斯“库劳茨一样,完全是套用了凯维斯的理论模型。
但正如日本着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博士对罗林斯“库劳茨所做的批评一样:“凯维斯提出的‘如作用因素主要由海外需求所产生,那么出口量的变化就成正比例’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或许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所表现的理论模型本质上却是静态的。某种特定的工业部门由于利用了双重价格机制而发展成为出口工业,接着为了充分利用大量生产的好处又扩大生产的规模,其结果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形成反比,这种情况即使抽象地加以考虑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对日本在最近20年的出口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工业加以详细分析,便可得知,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是由于扩大出口的成功才得以成为现实。”
日本的另一位着名经济学家建元正弘,1974年6月1日提交给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召开的“公共经济学国际讨论会”的论文《日本的稳定政策及其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的关系》中也指出:“扩大工厂及设备的投资,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是不能和出口分裂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