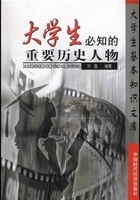魏顺妃因受了惊吓,又有伤在身,所以那句话本身声音并不大,却生生在平地激起一阵炸雷,震得祐珉手中长剑脱手掉落地上,同时震得屋外的祐骋双臂发软,险些从檐上坠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冯伯义这天夜里让他知晓的,居然是这皇宫里最不为人知的天大隐秘!
祐珉半晌才从震惊中回转,似是自言自语喃喃道:“乔振直……是我爹……不可能,不可能!”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魏顺妃凄然道,“二十年前,我才刚进宫不久,皇上登基伊始,整日埋头朝政,对我难得闻问,教我终日郁郁寡欢,若非振直对我百般呵护,我早已积郁成疾而死。兴许苍天护佑,让他的男儿身竟得保全……这才有了你,否则,你如何能成为皇长子而享尽荣华富贵?我入宫之前不离闺门,温婉谦顺,如今却变成宫内人见人怕的戾女泼妇,却是为谁?振直隐忍二十年,日日卑躬屈膝忍辱负重,却又是为谁?我们苦心积虑,平生夙愿便是你能登上皇位,从此呼风唤雨,风光一世,真能有这么一天,我与他便是立刻死了,也死得甘心!”魏顺妃说到这里,忍不住轻轻低泣,停了片刻,哽咽道:“这等苦心,娘是不要求你能体会,振直与我也从未想过将真相告诉你,若不是今日你突然到此……”
“别说了!”祐珉大喊一声,“这不是真的!娘,你在骗我是不是?我是皇子!我是皇子!不是假太监的儿子——”
“你娘没有骗你,你根本不是皇子!”乔仲正一反常态,言语冷冷打断他道,“这一旦为皇上知晓,可是诛灭九族之罪,谁人敢开这样的玩笑?”祐珉的喊叫顷刻停止,乔仲正又道:“事到如今,你根本无可选择,惟有继续我们的计划,使你顺利即位,才能保全你跟你娘的性命。否则,腰斩和陵迟,你且随意选一样罢!”
祐珉默不做声,但听得到他上下牙齿微微磕碰的声音,又听得乔仲正低沉的声音继续道:“你不肯认我这个爹,我也不勉强你,我乔某人一生从不求人,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只是你即位之后,不可亏待你娘,这样即便你这辈子都不认我,我也绝不怪你。”
屋内又是一片沉寂,许久,祐珉茫然喃喃道:“计划?那计划……还可以继续实行么?”
“当然!”乔仲正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如今太后与皇上那边,好事都已进行得八九不离十,这几天就应见分晓。再者,禁宫四处都有我的手下,举事之日,内外接应,处处滴水不漏,你就等着黄袍加身罢!”
祐珉长叹一声,正要说什么,突然外面一阵喧哗嘈杂,一太监脚步匆匆撞开房门奔进屋内,气喘吁吁道:“殿下!娘娘!公公!太后……薨了!”
“什么——!”屋内三人同时叫道,屋外祐骋也忍不住轻呼一声,所幸场面纷乱,屋内无人发觉。冯伯义见祐骋两臂抖如筛糠,再也难以攀牢檐梁,知道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叫他实在不堪承受,便探臂托住他的下腋,轻轻纵身一跳,跃上屋顶,架着祐骋,猫腰踏着屋脊飞奔。离开德秀宫后院时,不忘飞出数枚石子,解开众守卫的穴道,眨眼之间,便带着祐骋离开了禁宫,向慎王府疾行而去。
一路上,祐骋逐渐回过神来,但仍觉得恍在梦里,听得冯伯义低声道:“太后薨逝,想必已传至你府上,呆会回去,你便得立刻换衣进宫。今夜你所见所闻,万不可对任何人泄露半点!”
祐骋讷讷应了一声,突然问道:“前辈,这一切……可都是你安排好的?”
冯伯义哼了一声,脚步丝毫不见停歇,淡淡回道:“那对狗男女背着你父皇厮混已久,又生下你那冒充的大哥,他们只道瞒天过海,不想却被老夫知晓了去。老夫既已答应助你,便得先教你认清他们的底细,只是口述太累,你也未必肯信,不如索性带你亲自走一遭——今夜乃他们例常幽会之时,且你父皇恰好彻夜在上书房批阅奏折,老夫又顺手在那房间的香炉里撒了一把波斯依兰,数因并起,他俩幽会之时,怎能不苟合一番?老夫在去见你之前,事先将顺妃这贱人的珠簪沾了点马血,用袖箭钉到你那假冒大哥的卧房床头,你那假冒大哥见了,自是以为母亲出了什么意外,所以急匆匆赶了过去,这才有整盘好戏的开场。一切顺理成章,老夫又何须费神安排?”
祐骋蓦地停住脚步,蹲在地下,抱头怆然道:“为什么?仅仅几个时辰,一切便都面目全非!皇祖母……”他猛然站起身,直视冯伯义道:“皇祖母身体一向康健,怎的突然……前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说!”
冯伯义转开头去,眼内有光亮微微一闪,缓缓道:“太后一事,老夫也是刚刚知晓,看来老夫有些低估了那乔仲正。你莫多问,先自回去,后面的事情,老夫自有安排!”
“可是……”祐骋略一迟疑,还想再问什么,冯伯义脸色一沉,喝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若你至今还信不过老夫,从此便另寻高人罢,老夫也懒得趟这道浑水!”
祐骋慌忙道:“前辈千万息怒!我按您吩咐的去做便是!”
冯伯义说得果然不差,祐骋才一回府,便被皇上口谕急急召往宫内。太后寝宫内哭声震天,皇上跪在太后床边兀自垂泪,后面的皇后与众皇子公主直哭得昏天黑地,祐骋赶到时,见祐珉和魏顺妃已跪在那里,哭得几欲昏厥,乔仲正俯在地下,脸上也是老泪纵横,不禁暗忖:“莫非适才一切皆为梦魇?再不就是他们太会装腔作势,如此便可怕得紧了!”再一环顾,只见沾衣跪在皇后侧后方,除了泪水不断在脸上流淌之外,整个人静静得如一尊雕像。已悲痛得难以自制的祐骋看见沾衣,更是觉得鼻子发酸,眼泪蓦然渗出眼角。
皇上微微转过头,见祐骋呆呆立在那里,便哽咽道:“骋儿,你且上前来……你自小在这里长大,最得你皇祖母的疼爱,今日……今日……”话还未说完,就已化为一阵低沉的被极力压抑的啜泣,祐骋脸上早已是泪痕交错,父子俩相拥而恸。
沾衣透过泪眼望着他们的背影,皇上虽已尽力克制自己的悲伤,但肩头仍抽动得厉害,她从未过见皇上这般渲泄情感,即便是对她倾诉衷肠的那夜,虽然激动亢奋,却也不失风度威仪,可这时的皇上,那般悲伤和无助,似乎已不是万民敬畏的君主,而只是一位痛失娘亲的儿子,此情此景,让沾衣想起当初爹娘双双辞世的情形,便对皇上油然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疼惜。
半晌,皇上渐渐收住啜泣,缓缓跪起,望着太后遗容,嘴唇翕动,沾衣微微抬头,也偷眼望向太后,一看便愣住了,一丝疑云在胸中弥漫开来,正待细看,突然听祐骋在一旁惊呼:“父皇!您怎么了?父皇——!太医!快传太医——!”
沾衣慌忙扭头看去,只见皇上抚着胸口歪倒在地,双目紧闭,脸色青紫,不禁大惊,扑过去与祐骋一起将皇上扶起。她摸了摸皇上手腕,只觉得脉息纷乱,想是犯了前些日子积下的的心疾,便用身体挡住手臂,手掌按着皇上后心,暗自输送内力到皇上体内,因不知皇上体力深浅,便不敢送得太快,只稍送辄停,心底盼望皇上能捱得一时半刻,等太医前来诊治。
只一会功夫,太医便匆匆奔来,殿内殿外又是一阵忙乱,少顷,皇上悠悠醒转,微弱吩咐道:“朕有些困乏,今日就在近旁的齐庭轩内歇息罢。”沾衣亲自侍侯皇上安顿下来后,正要退出,听得皇上又道:“其他人可以退下了——沾衣,你留下。”众人岂敢不从,纷纷回避,只除了祐骋和祐珉,前者是略有不舍,神色怆然,后者则眉头紧锁,目光闪烁,但见父皇已下逐客令,盘桓片刻,也只好怀着各自的心思打道回府。
沾衣默默站在那里,凝视着皇上。皇上一脸疲惫,轻轻叹了口气:“沾衣,你坐到朕身边来。”沾衣走过去坐下,皇上翻了个身,捧住沾衣的双手,喃喃道:“这个时候,朕很想有个人陪在身边,不要多,一个就好……太后去了,朕也就只有跟你能说说贴心话,唉,朕这一病,不知何时能好,朕以前也忒托大了些,总以为还是当年那般生龙活虎,可如今……毕竟岁月不饶人哪!”
“陛下何出此言?”沾衣藏住满心忧虑,安慰皇上道,“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陛下只须安心养病,过些时日,便可康复如初。”停了一下,沾衣轻轻补充道:“前些日子的那盘棋……臣妾还等着与陛下下完它呢!”
皇上微微一笑,紧紧握了一下沾衣的手,沉默片刻,道:“朕差小全子去传的左右丞相和兵部尚书,此刻也快到了,沾衣,这次恐怕你得回避一下。”沾衣忙起身告退,但仍是不大放心,一番叮咛后方才离去。
沾衣出门来到院里,见施太医远远躲在廊檐下,见她出现,便迟疑着向她走来,沾衣心里起疑,脸上却仍平静,问道:“施太医,您可有事么?”
施太医停步行礼道:“见过惠妃娘娘……微臣不放心皇上龙体,所以先在这里候着,以备万一。”
沾衣温言道:“您一向忠心耿耿,可昭日月,若满朝文武个个如您这般,皇上定可省心不少。”
施太医被沾衣夸得有些受宠若惊,忙躬身道:“谢娘娘抬爱,微臣为皇上所尽绵薄,乃为人臣者分内之事,何足挂齿?”
沾衣微微一哂,向院外走去,忽而又仿佛想起什么,回身问道:“给皇上的药您可备好了么?”
施太医略微一惊,随即脸上闪过一道喜色,忙道:“药已备好,微臣刚才还想着交给娘娘,一转身便忘记了,若非娘娘提醒,可要误了大事!”说罢从怀中取出两包草药和一个小瓶,道:“草药煎服,瓶内乃皇上常服的苏合香酒……每次一小盅。”
沾衣笑道:“您可真是细致入微,待皇上康复了,我可得在他面前好好为您美言一番。”
“哪里哪里!”施太医如释重负,千恩万谢地走了。
沾衣直到看不见施太医的身影,才将药包拿到眼前仔细端详着,心底自言自语道:“既是给皇上的药,应交给小全子才是,却交给我做甚?”想起适才施太医前后神色,越忖越觉得古怪可疑,可翻来覆去看这草药,却看不出什么异样。
正在这时,小全子匆匆走过来问道:“娘娘,给皇上的药可在您这里?”沾衣点了点头,有些迟疑地将药包递给他,却趁他不备,悄悄拈了一小包药握在手心,转而藏于袖内,待小全子转身走远,也闪身出了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