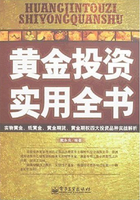源北村地处京城近郊,一夜之间便被屠村一事,次日便惊动朝野,官府只报是山匪所为,皇上震怒,责令官府追查确凿,剿尽匪人,至于沾衣的父母,因遍寻不见尸首,只道是葬身火海,皇上见沾衣悲痛欲绝,也痛心不已,对她极尽劝慰,将她父亲莫三言追封修慈侯,母亲莫柳氏追封一品诰命夫人。沾衣见皇上这般抚慰自己,便按捺悲伤,强作欢颜,想叫皇上宽心,无奈连日心力交瘁,在爹娘过世那夜悲伤过度,又淋了雨,第三日便发起了高烧,卧床不起。皇上心急如焚,召了三名太医连夜为沾衣诊治,给她灌服下几帖精心调配的草药后,天明时分,她的高烧才渐渐褪去。
清晨,沾衣醒来,头脑依旧觉得昏昏沉沉,但精神好了许多,便披衣下床,走到窗前,此时花园里阳光灿烂,鸟声清脆,露珠在草叶上闪着晶莹的光芒,这番景像,让沾衣竟看得痴了,连小富子进来都没有发觉。
小富子见沾衣站在那里,便小心翼翼道:“娘娘身子未痊愈,还是回到床上歇息罢。”
沾衣微微笑道:“略染风寒而已,不碍事,皇上可有来过?”
“禀娘娘,昨日皇上在这里几乎守了一夜,直到娘娘退烧以后才去上早朝。”
“哦?”沾衣转过身,“如此说来,皇上是一宿未眠?”小富子点点头。沾衣扭回身来,望着窗外,心里泛起丝丝感动,可这种柔软的感觉却又让她烦恼不已,自家门惨变之后,此刻的沾衣非比从前,虽然表面一如既往,使外人难以觉察,其内心却陷入日益加剧的沉重,教她不敢奢望一切能令自己愉悦欢乐的东西。
“太后驾到——!”门外一声尖细的通传把沾衣从沉思中唤醒,她慌忙整理一下头发,向已经进门的太后下跪施礼。
“快快免礼!”太后有几分嗔怪,“你这孩子!身子还没好,就下床走动,还不快回去?”沾衣谢过,等太后落座,方才斜靠床沿坐下。坐定以后,才发现立在太后身后伺候的太监竟然是乔仲正,登时一腔的仇恨在心头澎湃,直恨不得立时上去取他性命,但表面依旧平静,神色自若,微笑着与太后娓娓而谈。
乔仲正一直偷眼端详沾衣,从沾衣的举止,根本看不出她几天前经历过灭门之痛,看向他的眼光也丝毫觉察不出异样,然而沾衣越是如此,便越叫他心惊胆战。那天夜里他急于离开源北村,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要去搜寻冯伯义的下落,谁想他和他的手下细细寻遍了方圆数十里,直到天明,也未见冯伯义半个人影,他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回到宫里瞒过皇上太后关于小成子失踪这茬事。冯伯义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果让他好生烦恼,几天下来,每想起此事他便咬牙切齿,这世上只要还有一个知他底细的人活着,他便终日不得安宁,如今不但冯伯义生死不详,莫沾衣也已经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万昭宫那花园密道——可不是更教他如坐针毡?冯伯义受了重伤,一时半会也难以再找他的茬,下落不明倒也罢了,可这莫惠妃就近在眼前,抬头不见低头见,偏偏又集千般宠爱于一身,动不了她半根指头,此刻的乔仲正仿佛饿久的猛虎面对一只刺猬,眼巴巴盘算无数个念头,却丝毫下不得嘴。
这时,小富子推门进来斟茶,太后端起茶闻了一下,笑道:“小富子,这六安瓜片香得很,可是你烹的?”
沾衣呷了一小口,也赞道:“是香呢,小富子,你伺候我这么久,真没看出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小富子被夸得美滋滋的,咧嘴笑道:“太后和娘娘忒抬举了,这茶是德秀宫玉凤姐教奴婢煮的,里面还放了顺妃娘娘秘制的红莲雪蛤膏,又滋补又养颜。”
“你说的玉凤可是顺妃的贴身宫女?”太后随口问道。
“正是!”小富子忙回道。
沾衣眼中掠过一丝喜色,笑吟吟对太后道:“早听说顺妃姐姐擅长茶艺,玉凤也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烹茶高手,如果没有猜错,这道茶应是顺妃姐姐自创的,今日奴婢口福不浅。”
太后放下茶盅叹道:“顺妃资质聪慧,可惜太过争强好胜,有茶兴却无茶心,她若还这般执迷不悟,只怕迟早要闯出祸来。”
沾衣笑了笑,举起茶盅掩面一饮而尽,又从小富子手中拿过茶壶,揭开盖子看了看,道:“太后不必担忧,顺妃姐姐人虽泼辣傲气,却是嘴硬心软,她定是得知奴婢身体不适,所以辗转通过玉凤和小富子熬制这道补茶,您瞧这茶熬得火候正好,用料十足,这一片心意可是假不得的。”
太后赞许地看着沾衣:“哀家知道你为人宽厚,顺妃若能有你一半的胸怀,这后宫就会太平许多。”说完端起茶来,还未等送到唇边,沾衣突然站起,从她手里夺下茶盅,摔在地上,这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太后也惊诧万分:“惠妃!你……?”
只见沾衣面色惨白,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指着茶壶喘息道:“太后……这茶……喝不得!”说完便瘫倒在椅上,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慌得众人搀扶的搀扶,寻太医的寻太医,太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才平静下来的万昭宫,此时又是一阵手忙脚乱。
少顷,太医赶到,刚给沾衣号脉片刻,便紧锁眉头,太后急问:“惠妃到底是何病症?可是这茶里有毒?”
太医嗫嚅道:“禀太后……这茶里的……不是毒,娘娘她……”
“惠妃她怎么了?”太后急得直用龙杖咚咚敲地。
太医吞吞吐吐道:“惠妃娘娘已先兆小产,龙种……怕是难保!”
“什么?”太后脸色大变,身体一晃,若不是乔仲正手脚麻利扶住,险些栽倒在地。太后略微定了定神,问太医道:“那么这茶里到底有什么古怪?”
太医思索片刻,踌躇道:“微臣不敢妄下断言,只是看娘娘的症状,似乎是服用了红花、益母草和山棱之类……”
太后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失声叫道:“这些可都是孕时忌用之药!”转身紧紧盯着小富子,目光犀利:“这茶是你熬给惠妃的,你在里面放过什么?”
小富子吓得面如土色,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奴婢……奴婢什么都没有做过……奴婢不敢……”
“你当然不敢!哀家是问你受何人指使来加害惠妃!”
小富子磕头如捣蒜,一迭声叫道:“奴婢冤枉!这茶是完全按顺妃娘娘的方子熬的,里面除了六安瓜片,也就只有顺妃娘娘的红莲雪蛤膏而已……并无他物啊!”
“哼,惠妃小产,顺妃怕是高兴得很哪!”太后有些咬牙切齿,“哀家只道她心胸狭窄,没想到她竟如此心狠手辣!”
正在此时,听得脚步匆匆,皇上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原来他刚退朝,便听人禀报“惠妃娘娘小产”,急得朝服不换就匆匆赶来万昭宫,不等宫侍反应便冲了进来,却正好将太后逼问小富子这番对话听了个完全,一时间惊怒交集,竟忘记向太后问安,径直走到床前,望着已陷入昏迷的沾衣,问太医道:“惠妃病情怎样?”
“无甚大碍……”
“无碍?”皇上怒道:“她风寒未愈,又逢小产,你敢说无碍?”
太医慌忙跪下:“陛下,惠妃娘娘虽是患病之时小产,但脉像前弱后强,外虚内实,涩而不塞,沉而不淤,想是娘娘身体根基一向扎实,所以此次未能伤及内体,只须悉心调理,十日内便可痊愈。”
皇上脸色依旧阴沉,心底却稍稍放宽,转身走到小富子跟前,厉声问道:“到底谁指使你这么做的?快从实招来,否则朕将你凌迟处死!”
小富子不住磕头,直磕得前额冒血:“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陛下饶命啊!”
“还嘴硬!”皇上气得头上冠冕乱抖,“来人!拉出去廷杖重责,打到他说为止!”
“陛下……息怒!” 此时沾衣已醒,听到皇上最后一句话,不顾病体虚弱,极力从床上撑起半个身子,急切道:“陛下,小富子一直尽心侍侯臣妾,他不会害臣妾的,他实在没有理由要害臣妾……”还未说完,已是喘息连连。
“沾衣……你起来做甚!”皇上心疼,疾步走上前去扶住沾衣肩膀,让她轻轻躺下,回身对架住小富子的内侍们摆摆手,“罢了罢了,放他去罢!”但心里仍是恼怒,背着手踱了几步,从牙缝中恨恨挤出几个字:“摆驾德秀宫!”
一直冷眼旁观的乔仲正身子不由微微一抖,慌忙道:“陛下留步!娘娘小产……未必是因为喝了这茶!”
“嗯?”皇上诧异地盯住乔仲正,“说下去!”
“依常理,即便服用这些活血的草药,也要至少半个时辰后才能见效,可娘娘刚一喝这茶便致小产,兴许是因为之前娘娘所服的药汁汤水中被人下了手脚。”
太后颇为诧异,问沾衣道:“惠妃,哀家来看你以前,你可曾服用过别的汤药?”
“不曾服用……臣妾刚醒不久,太后就来了。”
“这就是了。”皇上淡淡道:“朕直到早朝前才离开此处,惠妃的汤药都经过朕之手,莫非你是以为朕残害自己的亲骨肉么?”
“老奴不敢!”乔仲正冷汗涔涔而下,讷讷道:“老奴适才只是担心无凭无据,不但寻不到真凶,还可能错冤无辜,这样一来,真正下药之人逍遥法外不说,后宫怕也要引起骚乱。”
“此话也不无道理。”皇上思索片刻,问乔仲正道:“依你之见,应该如何?”
乔仲正深施一礼:“老奴不才,略通些药理,若陛下允许老奴对这茶稍做查验,兴许能发现些许线索。”
“那还不快查,愣着做甚?”皇上催道。
全屋人的眼光登时统统集中到乔仲正身上,只见他端起茶壶,先闻了闻,又用指尖蘸了点尝了尝,眯眼沉吟半晌,猛然睁开眼睛,脸上表情甚是怪异:“原来是这样!”
皇上急问:“是怎样?”
“陛下,药的确是下在这茶里,这药里不但有红花、益母草和山棱,而且还加了熏陆香和乌灵脂,难怪见效如此神速!”
沾衣禁不住暗自冷笑,心道:“说得头头是道,为何不告诉皇上这药里还有川芎、莪术、蒲黄和田七呢?是怕皇上见你知道得如此详细而起疑罢?”
又听得乔仲正振振有辞道:“陛下,那乌灵脂平日里宫中用的不多,而且此药功效猛烈,轻微用量即可,所以老奴推测,下药那人手中应还有残余的乌灵脂,若能搜查到,便能抓住此人。”话音甫定,便听得咕咚一声,瑟缩一旁的小富子突然坐倒在地,半天都没能爬起来。